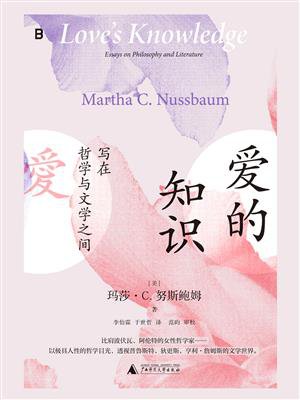1.价值之物的不可通约性
我们在这些小说中发现对质性区分的承诺并不令人惊讶;一个人很难想象没有这种承诺的
文学
艺术。但小说比其他许多形式更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区别的多样性和精细性。小说所体现的洞见表明,一个事物不仅仅与另一事物在数量上不同;不仅没有一个单一的度量标准可以有意义地考虑不同美好事物的主张,而且甚至连一个小的多元的度量标准都没有。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多元质性思维的价值和丰富性,并在读者身上激发一种丰富的质性洞见。小说家的用语甚至比日常生活中那些有时生硬含糊的用语更加丰富多样,在定性上更为精确;这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在打磨(既有定性的)理解方面我们可以追求什么。在小说中所呈现的那种将质化约为量的倾向(在《金钵记》的前半部分的魏维尔父女身上,在狄更斯笔下的葛莱恩先生和麦卓康赛先生身上);在最好的情况下,它被视为道德上的不成熟——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被视为无情和盲目。葛莱恩先生对小说的厌恶有其充分的根据。

1a.依恋与义务冲突的普遍性
对于一个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和其他事情一样”的能动者来说,不存在任何简单的权衡,很多选择都会有一个悲剧性的维度。当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50美元和200美元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十分痛苦:一个人放弃的只是他得到的东西的不同数量。在两种性质不同的行动或承诺之间做出选择,如果处于无法同时追求这两种行动或承诺的情况,那么这种选择是或者可能是悲剧性的——部分原因是,被放弃的事物跟得到的事物并不相同。小说作为一种形式,深深地卷入了对这种冲突的再现,这种冲突直接源于它对不可通约性的描述和对情境的伦理相关性的承诺。当然,人们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些这样的困境,给出一个栩栩如生的书面案例。但在“有瑕疵的水晶”一章中,我认为,只有在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正如这部小说的典型做法——遵循一种选择和承诺的模式,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冲突在人类追求好生活的努力中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