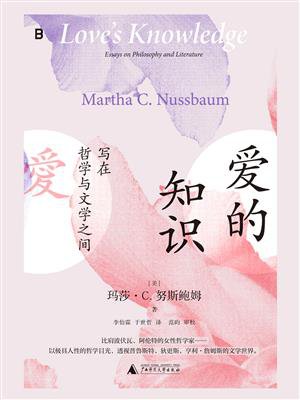Ⅵ.一个空洞的境遇道德?
这种伦理规范将被指责内容空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指控是正确的。由于特殊事物的优先性,我们不能对慎思的优先性做一般性的说明,也不能对好的慎思的技术和过程做一般性说明,这种一般性说明足以在面对案例之前区分好与坏的选择。一般性说明可能会为我们做出好选择提供必要条件;它本身不能给出充分条件。亚里士多德对此说得很清楚:正如能动者自身的决定取决于感知,我们对于他或她是否做出了正确选择所做的判断也同样如此。那种为正确的感知确立穷尽一切的一般标准的要求需要受到抵制(《尼各马可伦理学》1126b2—4)。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里,有实践智慧的人不会背着公告闲逛,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跟随他们。我们也永远无法在生活中完全滴水不漏地保证在特殊境况下正确运用感知。不存在充分条件:我们自己的决定取决于感知。
但是对空洞的指责以一种更强烈、更令人不安的形式出现。希拉里·普特南评论了我之前试图从《金钵记》中引出的一幅亚里士多德式选择图景的尝试。他认为,这种观点面临崩溃的危险,可能会陷入“一种空洞的境遇道德”。在这种情境中,一切都是“权衡的问题”。
 我认为,这项指控是说重视具体选择情况并主要根据情况要求进行判断的能动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伦理连贯性和承诺,缺乏坚定的原则和可靠的关于好生活的一般概念。只要能动者在这一案例的材料中承受足够多的煎熬,她就可以做任何她喜欢的事。
我认为,这项指控是说重视具体选择情况并主要根据情况要求进行判断的能动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乏伦理连贯性和承诺,缺乏坚定的原则和可靠的关于好生活的一般概念。只要能动者在这一案例的材料中承受足够多的煎熬,她就可以做任何她喜欢的事。
我们已经开始对这项指责做出回应,我们坚持认为,在玛吉·魏维尔的慎思过程中,一般性原则起到了指导作用。我们还指出,在亚里士多德式概念对责任冲突的认知中,允许我们持有一种比我们在许多伦理概念中更为深刻的对原则的忠诚。但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回答普特南,因为可以让我们对亚里士多德式选择中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给出一个迄今为止更为丰富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戏剧即兴发挥的隐喻开始,这是詹姆斯主义者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对实践智慧活动最喜爱的比喻。玛吉·魏维尔是一名已经准备好了的和受过训练的女演员,现在她发现自己必须“相当英勇地”“时不时地”即兴表演自己的角色。在学习即兴发挥的过程中,她是否采取了一种没有原则、一切都是临时安排的选择方式?(也许: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这位女演员的形象暗示了这样的推断是多么不准确。根据剧本进行表演与即兴表演的显著区别在于,一个人必须对其他演员和情境给予的东西 更加 敏感,而不是更麻木。死记硬背无济于事,你必须在每一刻都积极地体察和回应,准备好迎接惊奇,这样才不会让他人失望。一个即兴表演的女演员,如果她即兴表演得很好,就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能说。她必须把她的选择与故事的进展相适应,后者有自身的形式和连续性。最重要的是,她必须保持她的角色对其他角色的承诺(作为演员的她对其他演员的承诺)。这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专注的忠诚。
想想交响乐演奏者和爵士音乐家之间类似的对比。对于前者,承诺和连续性是外部的,来自乐谱和指挥家。她的工作就是解读这些信号。爵士乐演奏者,积极地创造连续性,必须以充分的体察并在对这种形式的历史传统负责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在每一刻积极地尊重她对其他音乐家的承诺,她最好尽可能地对作为独特个体的他们有所了解。她将比只会读谱子的人更有责任,而不是更不负责,去展开连续性和结构的工作。(我们也可以说,随着古典乐手的音乐水平不断提高,她不再只是一个死记硬背乐谱的人,而是一个积极思考的诠释者,在每次演奏时都能从中获得新的认识,就专注的特点而言,她也越来越像爵士音乐家。)
因此,这两个案例向我们表明,道德上即兴发挥的感知者负有双重责任:对投身的历史和构成其背景的不断发展的结构负责;尤其要对这些负责——在每一个场景中,在一种她自身的历史与场景的需要之间积极且充满知性的对峙中,她所做出的承诺都是崭新的。
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感知者将一般性概念和承诺的历史以及一系列过去的义务和从属关系(有些是一般的,有些是特殊的)带入新的情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构成她不断发展的好生活的概念。这些承诺有组织地内化,构成了她的性格。她会欣然地将这种境况视作由一般性的事物所组成,她对此的道德描述也会使用(如我们所见)“父亲”和“朋友”等措辞,并承认她在这种情况下所承担的一般和特殊的责任。正如我们所说,即使这样做会带来冲突的痛苦——但这是承认这个具体情况的一部分。
我们或许说,感知是一种规则与具体回应、一般性概念和独特案例之间充满爱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阐明了特殊,反过来又由特殊进一步阐明。特殊是由可重复和不可重复的特征构成的;它是用一般术语的结构勾勒出来的,也包含着我们所爱之人的独特形象。
 如果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中实现的话,一般性是黑暗的、缺乏交流的;但是,一个具体的图像或描述如果不包含一般术语,则是不清晰的,实际上是疯狂的。出于我们所说的原因和方式,特殊性具有优先性;有相关的不可重复的属性,有一些可修改性。归根到底,一般性的作用只有在正确表达具体的时候才能发挥。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特定的人的上下文背景,在其所有要素上都不会是自成一类,也不会脱离充满义务的过去。作为人性的标志,对此的忠诚是感知最为基本的价值之一。
如果不是在一个具体的形象中实现的话,一般性是黑暗的、缺乏交流的;但是,一个具体的图像或描述如果不包含一般术语,则是不清晰的,实际上是疯狂的。出于我们所说的原因和方式,特殊性具有优先性;有相关的不可重复的属性,有一些可修改性。归根到底,一般性的作用只有在正确表达具体的时候才能发挥。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特定的人的上下文背景,在其所有要素上都不会是自成一类,也不会脱离充满义务的过去。作为人性的标志,对此的忠诚是感知最为基本的价值之一。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小说能够在表达亚里士多德式道德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引导我们关注具体的事物;它们在我们面前展示了丰富的细节,将其呈现为与选择相关。然而,它们却在告诉我们:它们要求我们想象我们自己的处境和这些主人公的处境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去认同这些人物和/或处境,从而感知这些相似和不同之处。通过这种方式,小说的结构也表明,许多道德上的相关性是具有普遍性的:了解玛吉·魏维尔的处境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的处境。
还有一点可以补充,亚里士多德式慎思,在我看来,非常深入地涉及一个一般性概念,即人的概念。亚里士多德式探询在伦理学上的起点来自这个问题,“人应该如何生活?”(见导论)。亚里士多德本人对这个问题的一般性回答是:“符合构成完整人生的所有良好功能的形式。”良好的人类功能的概念将这一探询引向更深层次,将注意力集中在情境的某些特征上,而非其他。能动者把她不断发展的好的或完整的人的生活的图景带到了选择的情境中。她会判断在这种情境下,良好的人类功能能否发挥作用。“人”这个概念是她用来界定它的最核心的概念之一,用于思考他人和她自己。她把好的特殊判断看作对人之善这一不断发展的概念的进一步阐述,如果它看起来有缺陷的话,也可以看作对它的修正。没有什么是不可修正的,但是,在她思考情境为各种功能创造了什么样的场合时,暂时性概念的指导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正如“超越”一章中所论证的那样,这个概念不是可选的。任何 对她 来说的好选择,也必须是一种对她 作为人 来说的好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感到亚里士多德式概念并非毫无根据(例如,远不如基于一个人某一时刻偏好的慎思方案那样毫无根据),也有助于我们感到,它确实给了能动者很好的指导,让她知道她的思想可能会走向何方。
这是一个宏大论题;其进一步影响不便在这里讨论,我在别处研究过它们。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提一下:亚里士多德式观点并不意味着主观主义,或者甚至是相对主义。对慎思必须考量到情境特征的坚持,并不意味着慎思的选择只相对于地方性规范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特殊主义完全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感知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事物的本来面目,需要进一步论证来对此处立场的最佳解释做出决定。当然,“人”这个概念的使用将在适应跨文化判断和跨文化辩论的概念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但有一点需要特别提一下:亚里士多德式观点并不意味着主观主义,或者甚至是相对主义。对慎思必须考量到情境特征的坚持,并不意味着慎思的选择只相对于地方性规范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特殊主义完全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感知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是事物的本来面目,需要进一步论证来对此处立场的最佳解释做出决定。当然,“人”这个概念的使用将在适应跨文化判断和跨文化辩论的概念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如果普特南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这几乎是毫无根据的。
因此,如果普特南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是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这几乎是毫无根据的。
在这里,我们应该补充一点,小说再一次证明了它是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合适载体。因为它们具体地描述了在多样的社会背景下的人类境况,并将每个境况中的社会背景视为与选择相关,它们还在自己的结构中构建了一种我们共同的人性。它们对人类讲述关于人类的故事,那种以某种可能性和某种有限性为特征的共同的人类生活形式,是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强有力的连接。这种具体性被视为人类发挥功能的一个场景,读者被邀请来做出相应的评估。尽管要从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直观地评估一部伦理或宗教专著极其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但小说能更有力地跨越这些界限,让读者沉浸在同情和爱的情感中,使读者自己成为所讨论的社会的参与者,并评估它为世界上的人类生活提供了什么物质资料。因此,在小说的结构中包含着不断发展的一般概念和丰富的特殊感知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教会读者如何机智地在这两个层次间穿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