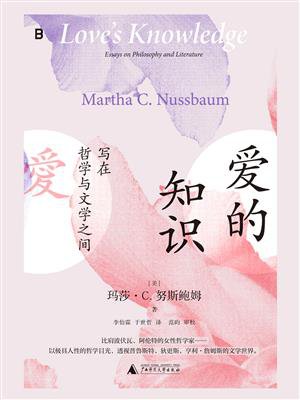2.感知的优先性(特定事物的优先性)
在这些文章和小说里,继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之后,都存在我称之为“感知”的伦理能力。我指的是一种能够敏锐而迅速地辨别出一个人特殊处境的显著特征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式的观念认为,这种能力是实践智慧的核心,它不仅是实现正确行为或陈述的工具,而且本身就是一种有伦理价值的活动。我在詹姆斯那里发现了类似的例子,他一直强调要实现“细微的体察和完全的承担”这个目标。这一承诺看似再一次被纳入作为体裁的小说这种形式当中。
我们需要说明这些具体感知与一般规则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这里,这个观点很容易被误解。在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那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对感知的强调中有一点就是要显示那种建立在一般规则之上的道德的粗糙性,并要求伦理学对具体事物有更敏锐的反应——包括那些前所未见的特性,因此不可能被纳入任何预先建立的规则体系中。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都用即兴发挥这一隐喻来说明这一点。但是规则和一般范畴在感知的道德方面仍然具有巨大的行动指导意义,正如我在“洞察力”和“‘细微的体察’”章节中试图展示的那样。这完全是一个它们被认为有 什么 意义,以及能动者的想象力如何使用它们的问题。 [39]
在这个概念中,特殊的感知优先于固定的规则和原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对他的讨论中,它与
一般性
和
普遍性
形成了对比。
 重要的是要区分这两种观念,并准确地看到“特殊事物的优先权”是如何与每一种观念相对应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对
一般性
(反对一般规则作为正确选择的
充分依据
)的论点指出,在伦理关切和判断中需要那种细腻的
具体性
。他们坚持认为有必要对伦理关切加以重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三样东西是一般原则所忽视的,它们先于具体案例而存在。
重要的是要区分这两种观念,并准确地看到“特殊事物的优先权”是如何与每一种观念相对应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反对
一般性
(反对一般规则作为正确选择的
充分依据
)的论点指出,在伦理关切和判断中需要那种细腻的
具体性
。他们坚持认为有必要对伦理关切加以重视,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有三样东西是一般原则所忽视的,它们先于具体案例而存在。

(a)新的和未预料到的特性。亚里士多德使用了伦理判断与航海家或医生的技巧之间的类比,认为旨在涵盖过去各种情况的一般原则将不足以使人准备好应对新情况。只要我们训练人把伦理判断简单地看作应用这些事先制定的规则(只要我们训练医生认为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在教科书里),就很难让他们为实际的生活流程做好准备,也难以让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意外时有必要的智谋。
(b)相关特征的语境嵌入性。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认为,要恰当地看待一个情境的任何单一特征,通常必须从它与复杂而具体的情景中许多其他特征的关联关系中去看待。这是另一种惊奇进入伦理场景的方式;在这里,一般的公式常常被证明过于粗糙。
注意,这两个特征都不能阻止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观对普遍性和伦理判断的普遍性产生浓厚的兴趣。就这些特征而言,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很可能坚持,而且通常也确实坚持,只要同样的环境、同样的相关语境特征再次出现,那么做出同样的选择也将再次正确。
 的确,这通常是正确选择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将指出,一旦我们像这一观点那样认识到文本、历史和环境的许多特征是相关的,那么由此产生的(高质量的)普遍性就不太可能具有多少行动指导用途。当然,它们不会扮演伦理普遍性在许多哲学观点中所扮演的法典化和简单化角色。但当我们意识到,复杂的詹姆斯式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可普遍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小说所提供的伦理教育及其所激发的伦理想象的方式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即使是高度具体的普遍性也有困难,这与关于特殊感知的第三个亚里士多德式论证相关联。
的确,这通常是正确选择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将指出,一旦我们像这一观点那样认识到文本、历史和环境的许多特征是相关的,那么由此产生的(高质量的)普遍性就不太可能具有多少行动指导用途。当然,它们不会扮演伦理普遍性在许多哲学观点中所扮演的法典化和简单化角色。但当我们意识到,复杂的詹姆斯式判断在很多情况下是可普遍化的时候,我们就会意识到在小说所提供的伦理教育及其所激发的伦理想象的方式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即使是高度具体的普遍性也有困难,这与关于特殊感知的第三个亚里士多德式论证相关联。
(c)特定人物和关系的伦理相关性。在阅读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时,读者可能会含蓄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与角色所处的环境足够相似,那么同样的言语和行为将再次成立。”但这些推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举个例子,如果我们考虑玛吉和她父亲之间的场景,也就是“‘细微的体察’”的主题,我们可能会有一种对这个形式的推论,“如果一个人像玛吉,而他的父亲也跟亚当一模一样,他们的关系和环境也一模一样,那么同样的行为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得出一种对形式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考虑自己与其父母之间关系的特定历史,他们的性格和自己的性格,像玛吉一样,选择对具体事物做出反应。”第一种普遍性虽然在生活中没有多大的帮助,但很重要:因为除非人们看到他们将如何对玛吉所描述的背景特征做出回应,否则他们将无法知晓玛吉的选择是否正确。第二种判断在小说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中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用普鲁斯特的话来说,读者变成了自我的读者。这一判断显然要求读者去超越那些描述的特征,转而去考虑自身情况的特殊性。
假设一个人找到了对自己情况的描述,那么反过来,这是否会产生一个具体的普遍性,将所有与伦理相关的事物都纳入其中呢?小说表明,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玛吉和她父亲的关系说明,这种可描述的、可普遍化的特性并不完全相关。我们从玛吉和亚当身上感受到了爱的深度和品质,我们觉得,这种爱是不能被克隆的,即使是具有同样可描述特征的克隆。她爱
他
,不仅爱他的特性,也爱超越特性和特性背后的部分,无论这听起来有多神秘。
 读者也被邀请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此外,正如小说所表现的那样,人类生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且只有一个走向。所以,想象同样的环境和人的再次出现就是去把没有结构的生活想象成实际上拥有结构。这改变了一切。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样,在实践选择的背景下推荐这样一个思维实验,它给我们的行动赋予了分量,一种让世界变得永恒的分量,但生活的现实偶然中罕有这种分量。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暗示,
某种
特定的强度将会被消减:因为他认为,(例如)一个人的孩子是“他唯一拥有的”这种观念,是他对孩子的爱的重要成分,如果没有这种不可替代的思想,爱的大部分价值和动力将会遭到削弱。他指出,在一个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这种强度的缺失给了我们充分理由拒绝把它作为一种规范。
[40]
玛吉必须意识到这是她的爱的一部分,任何质量上相似的替代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她的人类处境中,同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她只有一个父亲,他只活一次。如此看来,似乎普遍性并不能决定每一个选择的维度;有很多内心中的沉默,在那里它的需求不能、也不应该被听到。(参见“洞察力”章节和“‘细微的体察’”章节的尾注。)
读者也被邀请以同样的方式去爱。此外,正如小说所表现的那样,人类生命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并且只有一个走向。所以,想象同样的环境和人的再次出现就是去把没有结构的生活想象成实际上拥有结构。这改变了一切。正如尼采指出的那样,在实践选择的背景下推荐这样一个思维实验,它给我们的行动赋予了分量,一种让世界变得永恒的分量,但生活的现实偶然中罕有这种分量。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暗示,
某种
特定的强度将会被消减:因为他认为,(例如)一个人的孩子是“他唯一拥有的”这种观念,是他对孩子的爱的重要成分,如果没有这种不可替代的思想,爱的大部分价值和动力将会遭到削弱。他指出,在一个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城邦)中这种强度的缺失给了我们充分理由拒绝把它作为一种规范。
[40]
玛吉必须意识到这是她的爱的一部分,任何质量上相似的替代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她的人类处境中,同样的事情永远不会再发生;她只有一个父亲,他只活一次。如此看来,似乎普遍性并不能决定每一个选择的维度;有很多内心中的沉默,在那里它的需求不能、也不应该被听到。(参见“洞察力”章节和“‘细微的体察’”章节的尾注。)
这些关于爱的反思直接把我们带到了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第三个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