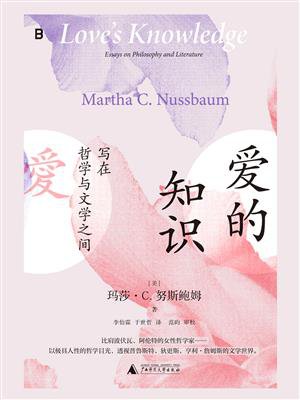4.不受控制事件的伦理相关性
在这场古代争论中,戏剧诗曾受到指责,因其在构建情节的方式中暗示:那些因非自身过错而发生在那些人物身上的事件对于他们的生活质量而言有着极大的重要性,而类似的可能性也会发生在观众的生活中。文学的反对者和捍卫者一致认为,对情节的关注本身就表达了一种伦理观念,这种观念与苏格拉底的主张(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悲剧的抨击中接受了这一主张)——好人不会受到伤害——相矛盾。在我们现代小说的诸多例子中,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作为这种体裁的成员和拓展者,这些小说在其结构中强调了对人类生活来说关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惊奇与逆转的重要性。詹姆斯将自己对偶发事件的兴趣与古代悲剧的兴趣联系起来,关注人物在他们的处境面前所表现出的怜悯和恐惧。(他的读者应该是“热切关注的参与者”,就跟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把发生的事情看得很重要。)普鲁斯特告诉我们,文学艺术的首要目的是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些时刻:在这些时刻,习惯被意想不到的事情所打破,并在读者中引起一种真实的、惊讶的感觉,类似高潮。两位作者的文本能够给读者以深刻的见解,因此他们都依赖这种能力来展示这些不受控制的事件,就好像这些事件对人物很重要一样,并使它们对读者也很重要。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认为,关于人类过好生活的愿望会被不受控的事件所制约这样一种正确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伦理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柏拉图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欺骗。

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包含了一个非常适合支持文学主张的学习观点。在这里,教与学不仅仅是学习规则和原则。学习的很大一部分发生在具体的经验中。反过来,这种经验性学习需要培养感知能力和回应能力:阅读一种情境的能力,挑出与思想和行动相关的内容。这个活动任务不是一种技术,人通过引导而不是公式来学习它。詹姆斯可信地暗示,小说例证并提供了这样的学习:在人物和作者的努力中例证它,通过构建一种类似复杂的活动,它在读者那里得到了激发。

小说还用一种更深层的方式来回应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实践学习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强调,亲密的友谊或爱的纽带(如联系家庭成员或亲密的私人朋友的纽带)在成为一个好的感知者的整个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
 相信朋友的引导,让自己的情感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和选择中去,一个人就能学会看到自己以前错过的世界的各个方面。一个人与朋友分享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望激发了这个过程。(我们在阿辛厄姆夫妇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通过那在同一图景下生活的爱的渴望,他们找到了对其处境共同感知的基础,从而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满足彼此的需要。)詹姆斯强调,不仅小说中所再现的关系,而且整个小说阅读中所涉及的关系本身,都具有这种特征。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某些人物,尤其是整个文本所揭示的生活意义,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热切关注的参与者”。我们相信他们的指引,暂时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即使,像狄更斯笔下的斯蒂尔福斯那样,我们被爱引导着,走出了笔直僵硬的道德判断的界限。
相信朋友的引导,让自己的情感参与到对方的生活和选择中去,一个人就能学会看到自己以前错过的世界的各个方面。一个人与朋友分享一种生活方式的渴望激发了这个过程。(我们在阿辛厄姆夫妇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通过那在同一图景下生活的爱的渴望,他们找到了对其处境共同感知的基础,从而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满足彼此的需要。)詹姆斯强调,不仅小说中所再现的关系,而且整个小说阅读中所涉及的关系本身,都具有这种特征。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某些人物,尤其是整个文本所揭示的生活意义,都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热切关注的参与者”。我们相信他们的指引,暂时通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即使,像狄更斯笔下的斯蒂尔福斯那样,我们被爱引导着,走出了笔直僵硬的道德判断的界限。
如果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也许会感到奇怪——认为爱情所扭曲的东西和它揭示的一样多,甚至更多。但是,这些文章是从一种体验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体验中,爱的启迪能力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现实。在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这点,通过坦率的自传方式——在这一方式中,我对女儿的爱以及我女儿对斯蒂尔福斯的看法使我对爱与道德之间的联系有了一种修正的观念;通过这一方式,借助于友谊(这不是说同意,而是比同意更深的东西),希拉里·普特南观点的转变,阐明了我对于政治生活的看法。同样的,在文本中还有其他的人物和事件,没有名字或者缺席,在文本中成形,并引导文本形成其自身的感知。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可以从我与小说本身关系的故事中看到这一点,它比任何其他的爱情都开始得早,而且是亲密无间的爱情。这些关系演变的故事本身也是思想的展开以及同情心得到塑造的故事。
F.小说、实例和生活
我曾说过,小说是道德想象力的一种特别有用的媒介,是最直接地向我们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艰巨性以及各种利益的文学形式,它最能指导我们认识人类的多样性和矛盾性。
莱昂内尔·特里林《自由主义的想象》
有人可能会承认,如果我们要充分且清晰地研究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主张,就需要一些非抽象论述的文本——这既是因为一篇论文能够或不能够陈述什么,也是因为一篇论文能够或者不能够对其读者做什么。然而,人们可能仍然不太确定小说是不是所需要的文本。于是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是这些小说而不是其他?为什么是小说而不是戏剧、传记、历史、抒情诗呢?为什么不是哲学家的例子?最重要的是,如詹姆斯笔下的斯特瑞塞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不是“可怜的亲爱的老生命”?
在这里,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我们手头上有一连串问题要研究。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甚至是关于如何生活的问题,会在完全相同的文本中得到探询。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想要思考宗教信仰在我们可能过的某些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那么这里所选的小说对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帮助,除了贝克特的作品以外,而且其作品也只是以一种有些局限的方式来探询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思考有关阶级区分,或者有关种族主义,或者有关我们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其他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样,这些特定的小说将是不够的。——尽管正如“洞察力”一章所指出的,大多数小说通过友谊和认同的结构,以某种方式聚焦于我们共同的人性,为这项计划的追求做出了一些贡献。我选择的文本表达了我对特定问题的关注,而不是假装处理所有重要的问题。
 (关于与我的立场相关的一些思想,见“感知与革命”章节尾注。)
(关于与我的立场相关的一些思想,见“感知与革命”章节尾注。)
然后,即便对于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而言,我们也不应该坚持认为所有体裁都不合适,或者只有小说不合适。并非所有的小说都能对应上詹姆斯和普鲁斯特在批评其他小说家时提出的理由。詹姆斯抨击乔治·艾略特小说中叙述者的全知视角,认为这是对人类地位的歪曲。他还指出,如果我们不够小心的话,许多小说对戏剧化兴趣的传统源泉的利用可能会破坏我们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更为单调地追求思想和感情的精确性,而不那么戏剧化地追求公正。
[45]
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对他遇到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持批评态度,认为这些作品对心理深度的关注有所不足。普鲁斯特和詹姆斯的写作方式都注重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因此,我以他们为参照建立的叙述不能自动地扩展到所有其他小说家。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詹姆斯有很好的论据来支持他的观点,那就是,在既有的各种体裁中,小说是他所说的“投射的道德”的最好例证。
 我提出在小说结构和亚里士多德式观念的要素之间存在不少联系,这些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我提出在小说结构和亚里士多德式观念的要素之间存在不少联系,这些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讨论。
不仅小说被证明是恰当的,许多严肃的戏剧(同样,仅就这些特定的问题和这个概念而言)也是恰当的,一些传记和历史文学同样是恰当的——只要它们的写作风格能够注意特殊性和情感,并且让读者参与到相关的探索和感受活动中,特别是让他们自身感受到与那些人物同样的可能性。我发现的一个短篇小说的案例(“爱的知识”一章),对于我正在研究的问题,其结构上的复杂性已经足够。在我看来,抒情诗提出了不同的问题。它们对更大项目的继续很重要,我把它们留给那些比我更有兴趣分析诗歌的人。对于喜剧和讽刺的伦理角色也是同样,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在其他体裁中。
但哲学家可能不会为这些文学类型的问题烦恼,而会被一个先前的问题所困扰,即:为什么是文学作品?为什么我们不能用道德哲学家擅长发明的复杂例子来研究我们想研究的一切呢?作为回答,我们必须坚持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迄今为止无法被有关文学形式与伦理内容之间密切联系的论证所说服。图解式的哲学家的例子几乎总是缺乏优秀小说的那种特殊性、情感吸引力、引人入胜的情节、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他们也缺乏优秀小说所具有的那种让读者成为参与者和朋友的办法。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些结构特征,小说才能够在我们的反思生活中扮演角色。正如詹姆斯所说,“所需要的是暴露和纠缠状态的图景”。 [46] 如果这些例子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它们本身就是文学作品。 [47] 有时,一篇非常简短的小说就足以用来研究我们当时正在研究的东西;有时,像“有瑕疵的水晶”一章中那样(我们的问题是关于一个相对漫长而复杂的生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一部小说的长度和复杂性。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图解式例证都不足以作为替代。(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被完全排除在外,因为它们还有其他用处,尤其是在与其他伦理观念的联系中。)
我们可以补充一些例子,把事情以图解性的方式建立起来,向读者暗示他们应该注意到什么、发现与之相关的东西。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伦理上最显著的描述。这意味着很多伦理工作已经完成,结果“已经确定”。小说则更加开放,向读者展示了怎样探寻合适的描述,以及为什么这种探寻很重要。(然而,它们也并非开放到无法让读者的思维成型。)通过展现“我们现实的冒险”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它们对生活的描绘比缺乏这些特征的例子更为丰富与真实——实际上是更为准确。它们对读者而言是一种更适合生活的伦理作品。
但为什么不是生活本身呢?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生活和反思来探询我们想要研究的事情呢?如果我们愿意去审视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难道不能在没有文学文本、完全没有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用摆在面前的我们自己的生活文本做到这一点吗?在这里必须首先说,我们当然也这样做,远离小说阅读以及(普鲁斯特所强调的)阅读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鲁斯特把文学作品视为“光学仪器”是正确的,通过它,读者可以成为自己内心的读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光学仪器呢?
亚里士多德已经给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我们从未活得足够充分。没有小说,我们的经验便太局限、太狭隘。文学扩展了它,让我们反思和感受那些可能因为太过遥远而无法感受的东西。这对道德和政治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卡萨玛西玛王妃》——在我看来——将小说读者的想象力描述为一种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类型,对广泛的关切有所同情,反对对人性的某些否定。它培育了读者的同情心。
《卡萨玛西玛王妃》——在我看来——将小说读者的想象力描述为一种在政治(和私人)生活中非常有价值的类型,对广泛的关切有所同情,反对对人性的某些否定。它培育了读者的同情心。
在此说明中,我们可以通过强调小说不能像“未经加工的”生活片段那样来起作用,来阐明和扩展这个观点:它们是一种亲近而细致的解释性描写。生活的全部就是在进行解释,所有的行动都需要把世界视 为 某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没有生活是“未经加工的”,而且(正如詹姆斯和普鲁斯特所坚持的那样),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小说的制作者。重要的是,在文学想象的活动中,我们被引导着以更精确的方式去想象和描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每一个词上,更敏锐地感受每一个事件——而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缺乏这种高度的体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并没有完全或彻底地活过。无论是詹姆斯还是普鲁斯特,都不认为日常生活是具有规范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概念也不例外:太多的日常生活是迟钝的、墨守成规的、不完全有感觉的。因此,文学是一种对生活的延伸,这种延伸不仅是水平的,让读者接触到他或她从未遇到过的事件、地点、人物或问题,而且也可以说是垂直的,为读者提供比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更深刻、更敏锐、更精确的体验。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加上另外三种东西,它们跟我们作为读者与文学文本的关系相关,也跟这种关系与生活中所涉及的其他关系之间的区别相关。正如詹姆斯经常强调的那样,小说阅读将我们置于一个既像又不像我们在生活中所处的立场:像的地方在于,我们在情感上投入人物角色,与他们一起行动,并意识到我们的不完整;不像的地方在于,我们摆脱了那些经常阻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进行慎思的扭曲根源。既然这个故事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就不会发现自己陷入个人嫉妒或愤怒的“庸俗的强烈激情”,或有时陷入我们的爱的盲目的暴力。因此,(以伦理作为关切的)美学态度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对此表示赞同,他提出了一个更有力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令人信服的)论断:只有在文学作品而不是在生活中,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种以真正的利他主义为特征的关系,并真正认识到他者所具有的他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对狄更斯的阅读使这一点复杂化,但它并没有将其移除。阅读行为可以成为进行仿效的范例。
此外,另一种让这项阅读事业值得效仿的方式是,它将读者聚集在一起。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强调的,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将读者汇聚,这种方式构建了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想象、思考和感受都被认为具有道德价值。
 亚里士多德式的辩证事业被描述为一项社会或共同体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那些愿意分享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试图就他们能够共同生活的观念达成一致。每个人单独审视他或她的自身经历可能是一种太过私人、无法被分享的行动,以至于无法促进这种具有共性的对话——尤其是如果我们像小说都在做的那样,认真对待个人思想和感受相关的隐私的道德价值。
[48]
于是,我们需要可以一起阅读并且像朋友那样去讨论的文本,那些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用的文本。就詹姆斯后期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声音而言,“我们”的普遍存在和“我”的稀有,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一个共同体是由作者和读者形塑的。在此共同体中人的独立性和质的差异并没有被忽视;每个人的隐私和想象都得到滋养和鼓励。但与此同时需要强调,共同生活是我们伦理利益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式的辩证事业被描述为一项社会或共同体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那些愿意分享一种生活方式的人试图就他们能够共同生活的观念达成一致。每个人单独审视他或她的自身经历可能是一种太过私人、无法被分享的行动,以至于无法促进这种具有共性的对话——尤其是如果我们像小说都在做的那样,认真对待个人思想和感受相关的隐私的道德价值。
[48]
于是,我们需要可以一起阅读并且像朋友那样去讨论的文本,那些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用的文本。就詹姆斯后期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作者声音而言,“我们”的普遍存在和“我”的稀有,具有高度的重要性。一个共同体是由作者和读者形塑的。在此共同体中人的独立性和质的差异并没有被忽视;每个人的隐私和想象都得到滋养和鼓励。但与此同时需要强调,共同生活是我们伦理利益的目标。
到目前为止,我坚持认为在完全书写作品中,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离的。但我也为这些小说辩护,认为它们是整体探索的一部分,而要完成这项研究,显然需要对文学作品的贡献做出明确的描述,并将其呈现的生命感受与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这些文章本身采用了一种对文学作品有所回应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它们的策略;但这也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对解释和明确描述的关切。有几篇文章(尤其是“爱的知识”一章)讨论了哲学的风格是文学同盟这一观点,哲学风格虽与文学作品的风格不同,但却引导读者关注这些作品的显著特征,并在一种与其他文本、其他选择所建立的清晰的联系中提供各种洞见。这在我们对辩证过程的叙述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概念之间的比较必须以一种不完全拘泥于一个概念的风格来组织,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开始这项与文学有关的辩证任务时,我们需要——甚至在我们开始研究另一种概念之前——一种哲学评论,它将明确地指出这些作品对我们关于人类和人类生活问题的追求的贡献,以及它们与我们的直觉和我们的生命感受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小说及其风格是道德哲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但它们是在与一种自身更有解释力、更为亚里士多德式的风格的结合中做出贡献的。为了成为文学的盟友,并引导读者认识而不是远离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亚里士多德式的风格本身将与我们通常遇到的许多哲学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必须是非还原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它将指向经验和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更完整的领域得以被探询。
我们认为,小说及其风格是道德哲学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但它们是在与一种自身更有解释力、更为亚里士多德式的风格的结合中做出贡献的。为了成为文学的盟友,并引导读者认识而不是远离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亚里士多德式的风格本身将与我们通常遇到的许多哲学写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必须是非还原性的,同时也要意识到自身的不完整性,它将指向经验和文学文本,作为一个更完整的领域得以被探询。
 但是,如果要把小说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使之与其他概念的特征形成比照,那么(我们的方式)也需要与小说有所不同。那些对小说进行陈述的文学批评和“哲学批评”都是整个哲学任务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是,如果要把小说的独特性表现出来,使之与其他概念的特征形成比照,那么(我们的方式)也需要与小说有所不同。那些对小说进行陈述的文学批评和“哲学批评”都是整个哲学任务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学丰富性与解释性评论的结合可以有多种形式。有些作家——比如柏拉图和普鲁斯特——把这两种形式结合成一个文学整体。有些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将他们的文学文本与他们自己明确的评论联系起来。其他哲学评论的实践者——从亚里士多德到斯坦利·卡维尔、莱昂内尔·特里林、科拉·戴蒙德和理查德·沃尔海姆这样的当代人物——为他人的艺术作品撰写评论。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存在唯一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家的叙述能力,以及他或她在探询不同伦理概念的整个计划中所投入的类型和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注意到这些评论所发展出来的形式与风格主张,它们不能削弱文学文本的主张。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文学文本可能包含一些形式使读者完全脱离那种辩证的问题;事实上,这可能是它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G.道德关怀的限度
除了你之外,我还能为什么而感受到爱?
我是否将最智者之书压在我身边
日夜隐藏在我内心深处?
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
这部分探究以“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为出发点。我在这里研究的所有书籍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但也有几个是关于爱的;爱,或者说爱的智慧,是这些文章中一个相互联系的主题。这也意味着有必要追问: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主动愿意或者允许自己被道德问题的边界所限制——另一方面,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达并引诱读者进入一种超越道德问题的意识。在这些文章和小说中,有一个(或多个)反复出现的伦理立场的概念,这种立场对于恰当地提出和回答这个包容性的伦理问题是必要的。这种立场常常与作者和读者的立场紧密相连。在不同情况下,我们的问题都必须是:这一立场是小说作为整体所安排的立场吗?或者(更动态地说),文学作品(有时)是否为其读者构建了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侵犯到了这个问题的边界?如果是这样,这与小说的伦理贡献有着怎样的关系?
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作为读者和评论家对这个答案的评价)将依赖并表达一种看法,即伦理观念与人类生活中某些重要因素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尤其是爱、嫉妒、需要以及恐惧——它们似乎位于伦理立场之外,并与之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我这里讨论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各不相同(也可能有所转变)。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导致我在不同的阶段聚焦于或寻求启发于一部小说或一个作者,而非其他小说或作者。为了澄清这些文章所提出的特定问题,我想把这一转变分为三个阶段(尽管其实在时间上它们并不完全是分离的)。我将集中讨论欲望之爱/浪漫之爱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中,我相信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立场是包容一切的,足以包括爱在内的好的人类生活的每个组成要素。如果一个人从狭隘的道德观点转向更具包容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即关于人类好生活的问题,那么我认为,他可以思考和感受任何事物,它们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看似合理的部分,包括激情之爱,追问它如何与其他要素相协调以及如何从所有这些要素中构建一种平衡的生活。(我在这里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著作包括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讲笑话、好客、友谊和爱本身,但这些对于康德和其他许多人而言则不在道德领域之内。所有这些要素都安全地存在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对好的人类生活的探索之中,而且可通过这种探索来得到评估和进一步说明。)
在这一时期,我强调了一个事实,即詹姆斯有关伦理立场的概念似乎具有同样的包容性;他的小说是由一种意识塑造并在读者心中形成的,这种意识总是能体察到关于人生以及如何生活的所有问题——人物的命运、情节的结构、句子的形态。该意识体察到生活中非伦理的,甚至是反伦理的因素——诸如嫉妒、复仇的欲望,以及与之相关的欲望之爱。但它对这些元素的体察自身具有强烈的伦理性。读者总是被敦促去关注它们对那种“投射的道德”的影响,并把它们作为人类好生活的要素(或障碍)加以评估。我个人认为,作为一种对生活中各种元素的态度,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立场是完整的,这是《善的脆弱性》一书的指导思想;在本书“有瑕疵的水晶”“‘细微的体察’”和“洞察力”等章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它们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的思想。
理查德·沃尔海姆在他对“有瑕疵的水晶”的评论中指出,小说对我们自我理解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在特定时间、以特定方式引导读者“脱离道德”,使他们成为道德以外计划的合谋者,尤其是那些基于嫉妒和报复的计划。
 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道德的边界及其在更为原始的态度下的根源,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我们从一篇道德论文中无法看到的关于道德的重要内容。我当时给沃尔海姆的回复是,我认为我们的差异仅仅是语言上的,仅仅是“道德的”和“伦理的”这两个词使用上的差异的结果,他对道德的理解是狭义的康德式的对道德的理解,而我是更广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在前一种意义上伦理或道德之外的东西,在后一种意义上的伦理或道德之内。即使(我说过)如果有人承认《金钵记》有时确实能让读者瞥见这种更广义的伦理立场的边界,向他们展示那种排他性的爱,与细微的体察和完全的承担互不相容,即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将读者带到那种爱的有罪的、有所偏倚的视野中,但爱仍然会以某种方式允许读者总是能在这一视野中对小说人物所失去的东西保持一种敏锐的体察;这样一来,小说始终保持在道德立场之内。
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这部小说向我们展示了道德的边界及其在更为原始的态度下的根源,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我们从一篇道德论文中无法看到的关于道德的重要内容。我当时给沃尔海姆的回复是,我认为我们的差异仅仅是语言上的,仅仅是“道德的”和“伦理的”这两个词使用上的差异的结果,他对道德的理解是狭义的康德式的对道德的理解,而我是更广义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理解。在前一种意义上伦理或道德之外的东西,在后一种意义上的伦理或道德之内。即使(我说过)如果有人承认《金钵记》有时确实能让读者瞥见这种更广义的伦理立场的边界,向他们展示那种排他性的爱,与细微的体察和完全的承担互不相容,即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将读者带到那种爱的有罪的、有所偏倚的视野中,但爱仍然会以某种方式允许读者总是能在这一视野中对小说人物所失去的东西保持一种敏锐的体察;这样一来,小说始终保持在道德立场之内。
在第二阶段中,我对詹姆斯式的读者及其伦理特征的看法或多或少保持不变,但对爱情的态度却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伦理观点有所不同。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更深入地发展了我观点中的部分要素,这些要素在我阅读《金钵记》的结局时就已经提出了,尽管在我给沃尔海姆的回信中没有提到。这里,我坚持认为人类之间的某些重要关系,尤其是欲望之爱,与伦理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而普遍的紧张感,需要得到一种关注,即使这种观点可以被广义的詹姆斯/亚里士多德式的方式所理解。寻求一种排他性和私人的关系的要求被认为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亚里士多德对伦理立场的包容性理解,也强调这种立场与广泛和包容性的关注以及与公共说理相联系。在“感知的平衡”中(以及在“斯蒂尔福斯的手臂”一章关于亚当·斯密和詹姆斯的内容中),跟随詹姆斯和斯特瑞塞的观点,我认为爱和伦理之间,以及每一种所需要的关注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的张力。任何希望包含这两者的生活都不能以平等均衡的状态为目标,而只能在伦理规范和这种非伦理因素之间不安地摇摆。(这一点最初是在“有瑕疵的水晶”一章中关于《金钵记》读本结尾处的一段简短评论中被提出的,这段评论说的是,我们需要随机应变,判断什么时候该把握细微的体察的标准,什么时候该放手。)至于詹姆斯,我的观点是,他把读者置于对道德最有利的观点上,使他们成为斯特瑞塞的盟友,并把斯特瑞塞的观点作为他与文学长期接触的结果。但詹姆斯使读者对斯特瑞塞的依恋变得复杂,足以让读者在小说的边缘感受到爱的寂静世界。因此,他想知道,一种更完整的人类之善是否可能不是“感知的振荡”,而是“感知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本身并不能代表人类的全部美德。
在这个阶段里,我没有坚持认为爱情对伦理理解有任何积极的贡献。我把它看作完整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但在伦理观念本身涉及的部分,它是颠覆性的而非有益的。在这里,我失去了在阅读柏拉图《斐德罗篇》(《善的脆弱性》第七章)时的信心,或者是失去了那时的洞见。在那里,我主张爱的“疯狂”不仅对完整的人生至关重要,而且对理解和追求善也至关重要。本书的“爱与个体”一章中再次记录了这些论点,但带着一些怀疑;女主人公对一个特定个体的面部和形态的明显专注 体现出 这与更广泛的伦理关怀是不相容的,尽管她 谈论 了很多伦理关怀。
当时,另一个论点影响了我,这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强调爱与伦理关注之间的鸿沟。在“有瑕疵的水晶”和“感知的平衡”中,我在提到嫉妒时,简略地提到了这个论点;虽然这是沃尔海姆对“有瑕疵的水晶”的回答中的一个主题,但并没有详细展开。它在塞涅卡悲剧的叙述中被详细地描述出来,这是我正在写的关于希腊化时期伦理学著作的一部分。这个争论关注的是欲望之爱、背叛或失望,如何将自己转化为对客体、对对手,或对双方的愤怒和邪恶的愿望。我认为,欲望之爱不能被亚里士多德式的平衡和谐的生活方式所“驯化”,而始终对亚里士多德式的追求具有潜在的颠覆性,因为这种爱与愤怒和想要伤害他人的愿望相联系。在爱欲中,一个人不仅冒着失去的危险,还冒着罪恶的危险。
第三种观点出现在最新的文章《斯蒂尔福斯的手臂》中。在此,由我对狄更斯的阅读(或者也可能由我对这种可能性的兴趣让我重读狄更斯)所引导,我认为,对最优秀、最人道的伦理立场所特有的细节的非评判性的爱,其本身就包含着对爱的敏感性,这种爱有时会将情人带出伦理立场,进入一个没有伦理判断的世界。狄更斯提出了一种同情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是动态的、浪漫的,是斯特瑞塞所不具有的。斯特瑞塞的“对特殊事物的非评判性的爱”,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非评判性。这个亚里士多德一再提及的问题,关于我面前的这一切如何与人类应该怎样生活的计划相吻合的问题,关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行为和感受的问题,从不会不被听到。狄更斯为其笔下的主人公所定制的传统有着不同的古代根源。它体现在罗马斯多亚学派关于仁慈和对非此即彼的判断的舍弃中,并在基督教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大卫·科波菲尔的爱的观念的一个源头。(另一种起源当然是浪漫主义的,正如我们在大卫偏爱充满生气的向前运动,以及将静止与死亡的联系中看到的那样。)
根据这一概念,爱和伦理关怀并不完全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是相互支持、相互影响;没有彼此,每一个都不会那么好、那么完整。普鲁斯特肯定不会接受这个观点,因为他相信所有的个人之爱都必然是唯我论的,他们对被爱之人的幸福漠不关心。更难以知道的是,对此,詹姆斯是否能接受,又能接受到什么程度。《使节》和《金钵记》的某些部分,太专注于把事情弄对,过于执着于要求细微的体察与完全的承担,以至于无法接纳爱,作为伦理生活中的一种不断滋长的势力,爱具有排他性并让人心绪不宁——即便与此同时,它可能被视为丰富或完整的人类生活的一个中心部分。然而,在海厄森斯·罗宾森与海宁·米利森特的爱中,在海厄森斯·罗宾森和奥罗拉女士对王妃充满仁慈的爱的方式中,在《金钵记》中对阿辛厄姆夫妇的描写中——也许在小说结尾玛吉对评判的温柔拒绝中,我们看到了欲望之爱的依恋和一种新的、更为柔软的道德正确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确实找到了这幅图景中的元素,显示出在柔性的严厉控制中存在着一种优雅,正如玛吉所反思的那样:“坦白的情感显示在不牢靠的艺术中,细腻的同情心也显示在系出名门的粗俗里。”

哲学常常把自己看作一种超越人类的方式,一种赋予人类新的、类神的行动和依恋的方式。我所探索的另一种哲学是把自己看作一种属于人的和言说人性的方式。这只会吸引那些真正想成为人的人们,他们以生活的本来面目看待生活,包括它的惊奇和联系,它的痛苦和突如其来的欢乐,一个值得拥有的故事。这绝不意味着不希望生活比现在更好。相反,正如“超越”一章中所主张的,有许多人性的和“内在”的超越方式,以及其他包含逃避与否定(人性)的(超越)方式。在追求人类的自我理解以及人类能够充分地理解自我的社会的过程中,第一种方法看上去是可行的,文学艺术家的想象与措辞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引导: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在堕落的世界中,天使在感知和同情方面是警觉的,爱的智慧让它明明白白地感到困惑与惊奇。

[1] 亨利·詹姆斯,《金钵记》( The Golden Bowl )序言,《小说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Novel ,1907)第339页。在收录有《金钵记》的纽约版本(1907—1909)中,这段文字出现在第一卷第十六章。詹姆斯实际上是在谈论“修订”的活动,作者/读者对文本的语言和形式的重新想象。
[2]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 Summa Theologica )1 q.89 a.1。
[3] 关于艺术如何塑造生活,参见纳尔逊·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 Languages of Art ,1968)第一、六章,以及他的《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 Ways of Worldmaking ,1978)。到目前为止,关于读者活动的文献已经很丰富了,尤其是:韦恩·布斯《我们所交往的朋友:小说的伦理学》(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1988);彼得·布鲁克斯《为情节而阅读:叙事中的设计与意图》(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1984);W.伊瑟尔《文本中的读者》( The Reader in the Text ,1980)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一文,第106—119页;另见前者的《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1978)。
[4] 有关这一点,参见本书“‘细微的体察’”和“洞察力”两章。“投射的道德”一词出自《一位女士的画像》( Portrait of a Lady )序言,《小说的艺术》第45页。
[5] 类似的区别,参见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1961;第二版1983),以及《我们所交往的朋友:小说的伦理学》( The Company We Keep: An Ethics of Fiction )中区别有关道德评估的分析。
[6] 理查德·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第二版( Art and Its Objects ,1980)以及《绘画作为一种艺术》( Painting as an Art ,1987)很好地说明了意图在解释中的作用。沃尔海姆认为,观者(或读者)活动的正确性标准必须参照艺术家的意图来确定。但是,只有那些与作品的创作有因果关系的意图才是相关的。他还坚持在艺术家角色的每一个阶段都要与观众的角色交织在一起,这不是两个人的两个角色,而是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占据观众的角色,这与詹姆斯在《金钵记》中对作者重读的微妙分析非常接近。关于意图,另见E.D.赫施《解释的有效性》(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1967)。
[7] 在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与《绘画作为一种艺术》中可以找到类似的,具有相似约束的广泛意向概念。另见斯坦利·卡维尔《言必所指?》(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1969;1976)。
[8] 在此之后,格雷戈里·纳吉(他是印欧语言学和计量学的创始人)在哈佛开始创作他现在很有名的关于传统流派与英雄观点之间联系的作品:《古希腊神话人物精选》( The Best of the Achaeans ,1979)。
[9] 卡维尔在这方面的最早工作收集在《言必所指?》(详见注释14)。有关以后的工作,参见《理性的主张:维特根斯坦、怀疑论、道德和悲剧》( The Claim of Reason: Wittgenstein, Skepticism, Morality, and Tragedy ,1979)和《对知识的放弃:论莎士比亚的六部戏剧》( Disowning Knowledge in Six Plays of Shakespeare ,1987)。
[10]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罗尔斯的观点在本书“感知的平衡”一章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关于罗尔斯和我对“道德哲学”一词的使用,参见“感知的平衡”注释2。罗尔斯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也应该说,前期一些哲学家集中于对道德语言的分析,他们的研究也涉及实质性的道德问题:参见R.M.黑尔《道德语言》( The Language of Morals ,1952)、《自由与理性》( Freedom and Reason ,1963)、《道德思考》( Moral Thinking ,1981)。
[11] 参见G.E.L.欧文《逻辑学、科学与辩证法:希腊哲学论文集》( Logic, Science, and Dialectic: Collected Papers in Greek Philosophy ,1986)。
[12] 例如,A.W.H.阿德金斯的《功绩与责任》( Merit and Responsibility ,1960)中举例说明了研究“大众道德”的方法。K.J.多佛的《希腊大众道德》( Greek Popular Morality ,1974)在方法论上要恰当得多,其论点丝毫没有排除文学作品作为整体或以其本身的权利对伦理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可能性。但这并非该书主题。
[13] K.J.多佛编辑的《会饮篇》( Symposium ,1980)封底上有这样一段简介:“柏拉图的《会饮篇》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富文学性的一部,所有古典文学的学生无论是否在学习柏拉图的哲学,都可能会想读这本书。”不管这段文本是谁写的,它都是我所描述的那个时期典型的叙述方式,事实上,它与多佛本人所采用的方式是一致的。
[14] 在1987年6月《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对一组关于柏拉图的新书的评论中,可以看到我对柏拉图学术研究中这些趋势的讨论;同样可参见《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第六、七章。有关最近试图消除这些分离的鼓舞人心的例子,参见查尔斯·卡恩,《柏拉图的〈高尔吉亚〉中的戏剧和辩证法》,《牛津古代哲学研究》第1期(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1983)第75—121页;C.格里斯沃尔德,《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的自我认识》( Self-Knowledge in Plato’s Phaedrus ,1986);G.费拉里,《聆听蝉声》( Listening to the Cicadas ,1987)。
[15] 参见《善的脆弱性》第二、三、十三章,以及插曲一、插曲二。有关悲剧性节日及其社会功能,请参阅约翰·J.温克勒的《男青年之歌》一文,刊载于《表象》第11期( Representations ,1985)第26—62页。
[16] 关于雅典人对公共批判性辩论的喜爱与理性论证的发展之间的联系,见G.E.R.劳埃德《魔法、理性与经验》( 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 ,1981)。
[17] 参见努斯鲍姆,《人文学科的历史概念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一文,刊载于《应用人文学科》( Applying the Humanities ,1985),第3—28页。
[18] 参见努斯鲍姆《自然的规范》( The Norms of Nature ,1986)中《治疗性论证:伊壁鸠鲁和亚里士多德》一文,第31—74页。由M.斯科菲尔德和G.斯特里克编辑。
[19] 关于这个观点,参见我的《治疗性论证》一文和《欲望的治疗》( The Therapy of Desire ,1986)。请一并参考P.拉宝《灵魂的方向》( Seelenführung ,1954)及I.哈多《塞涅卡与灵魂指引的希腊-罗马传统》( Seneca und die griechisch-rRömische Tradition der Seelenleitung ,1969)。
[20] 参见《善的脆弱性》第八至十二章;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文体,见该书插曲二。另见《古代作家》( Ancient Writers ,1982)中我所撰写的《亚里士多德》一篇,第377—416页。
[21]
科拉·戴蒙德,1988年8月30日的信。另见迈克尔·坦纳在《语言的状况》(
The State of Language
,1980)《哲学的语言》一文中对此问题的机智讨论,第458—466页。坦纳的论文首先评论了以下针对专业人士的哲学论文,摘录自一篇题为《对爱的概念探询》的论文:
现在,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勾勒出我们在使用“爱”时假定的概念。关于这些概念的想法可以通过勾勒一系列的关系来获得,我们认为这些关系的成员在决定A和B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爱的关系时是相关的。从作为进一步关系发展的证据的意义上讲,它们是不相关的,但作为存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爱”的组成部分。顺序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A了解B(或至少部分了解B)
(2)A在乎(或关心)B
A喜欢B
(3)A尊重B
A被B吸引
A对B抱有好感
(4)A向B承诺
A希望B的福利提高
这些关系之间的联系,我们称之为“包含着爱的关系”(LCRs),除了“知道”(knowing about)和可能“感受到爱”(feels affection for),不像精确的内涵那样严谨。〔W.牛顿-斯密,《哲学与个人关系》(
Philosophy and Personal Relations
,1973),第188—219页。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实际上是空间与时间哲学方面的杰出专家,在那个领域内,这种文体风格看似更为常见。〕
对于不熟悉专业哲学散文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应当证实了我在这一节中所讨论的内容。坦纳得出了令人钦佩的结论:“我们需要认识到,存在着那些类似形式的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严谨和精确的模式。深刻并不需要那种近乎晦涩难懂的方式。”
[22] 参见尤其是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 The Great Tradition ,1948),L.特里林《自由主义的想象:文学与社会论文集》( The Liberal Imagination: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50)。
[23] 阿瑟·丹托在发表于《美国哲学学会论文集》(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1984)的《文学与/作为/中的哲学》一文中对这一立场进行了有效的批评,第58期第5—20页。
[24] 韦恩·布斯在《我们所交往的朋友:小说的伦理学》中雄辩地主张复兴广泛而灵活的伦理批评,批评那种过于简化的版本,并指出伦理批评不需要有这些缺陷。我的评论参见本书“阅读”一章。另一个为伦理批评辩护的例子是马丁·普莱斯的《生命的形态:小说中的人物和道德想象》( Forms of Life: Character and the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Novel ,1983)。布斯的作品包含了全面广泛的伦理批评书目。
[25] 其他相关哲学著作,参见:斯坦利·卡维尔(上文引用的著作,详见注释20);理查德·沃尔海姆(详见注释13);伯纳德·威廉斯《自我的问题》( Problems of the Self ,1973)、《道德运气》( Moral Luck ,1981)、《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1983);希拉里·普特南《意义和道德科学》( Meaning and the Moral Sciences ,1978);科拉·戴蒙德《关于道德哲学言不尽意的故事》一文,刊载于《新文学史》第15期( New Literary History ,1983)第155—170页,以及《错过冒险》一文,摘录于《哲学期刊》第82期(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85)第529页及以下页;艾丽丝·默多克《善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od ,1970);大卫·威金斯《需求,价值,真理》( Needs, Values, Truth ,1987);巴斯·范·弗拉森《自我欺骗的观点》( Perspectives on Self Deception ,1988)中《爱与欲望的特殊效应》一文,第123—156页;彼得·琼斯《哲学与小说》( Philosophy and the Novel ,1975)。
[26] 康德的“理性建筑术”概念出自他的《纯粹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一书,是一种指使单纯聚集的知识成为一个体系的思想。“我所理解的建筑术(Archtektonik)就是对于各种系统的艺术。因为系统的统一性就是使普遍的知识首次成为科学,亦即一个使知识的单纯聚集成为一个系统的东西,所以建筑术就是对我们一般知识中的科学性的东西的学说,因而它必然是属于方法论的。”引自《纯粹理性批判》第二部分“先验方法论”第三章,[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
[27]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第46—53页;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第七版( The Methods of Ethics ,1907),尤其参见第六版序言(在第七版中已重新发布)。
[28] 对于这一挑战,参见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所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 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 ,1988)。我在《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讨论了麦金泰尔的论点(1989年12月7日)。
[29] 参见努斯鲍姆《非相对性美德:一种亚里士多德式方法》一文,刊载于《美国中西部哲学研究》第13期( Midwest Studies in Philosophy ,1988),第32—53页;以及内容关于伯纳德·威廉斯哲学工作的努斯鲍姆作品(1991)中《亚里士多德论人性与伦理学基础》一文。这类调查的政治结果概述见努斯鲍姆《亚里士多德式的社会民主》一文,《自由主义和利益》( Liberalism and the Good ,1990)。
[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Politics )1268a39及以下,《非相对性美德》中也有相关讨论(详见注释57)。
[31] 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与解构主义结盟的文学理论家明显地转向了伦理道德。例如,雅克·德里达选择就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在美国哲学协会发表演讲〔《哲学期刊》第85期(1988),第632—644页〕;芭芭拉·约翰逊的《差异的世界》( A World of Difference ,1987)认为解构主义可以在伦理和社会方面做出有价值的贡献。总的来说,似乎又回归到伦理和实践——如果不是,也许,回归到严格参与伦理思想,这是道德哲学领域最好作品的特征,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文学的”。毫无疑问,这种变化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保罗·德·曼的政治生涯丑闻,这使得理论家们急于证明,解构主义并不意味着忽视伦理和社会考量。
[32]
作者特别强调本段英文版本由自己翻译,故放上原版以供读者对比阅读:
You have implored me, Novatus, to write to you telling you how anger might be allayed. Nor does it seem to me inappropriate that you should have an especially intense fear of this passion, which is of all the passions the most foul and frenzied. For in the others there is some element of peace and calm;this one is altogether violent and headlong, raging with a most inhuman lust for weapons, blood, and punishment, neglecting its own so long as it can harm another, hurling itself on the very point of the sword and thirsty for a revenge that will drag the avenger down with it. For these reasons some of the wisest thinkers have called anger a brief insanity;for it is just that lacking in self-control, forgetful of decency, unmindful of obligations, persistent and undeflected in what it begins, closed to reasoning and advice, stirred up by empty causes, ill suited for apprehending the just and true—altogether like a ruin that crushes those beneath it while it itself is shattered.
——译者注
[33] 这些段落分别是斯宾诺莎《伦理学》( Ethics )开篇、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David Copperfield )开篇、亨利·詹姆斯《使节》( The Ambassadors )开篇,以及塞涅卡《论愤怒》( De Ira )第一卷开篇。《伦理学》是塞缪尔·雪莉的译本(1982),《论愤怒》是我自己翻译的。请注意,我在这里承认了某种意义上的意译,也就是说,一篇好的译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其风格与原文相似,值得在其位置上加以讨论。一个人不可能总是做得很好,尤其是诗歌作品;在任何情况下,这里所介绍的问题都应该询问译文,看看它如何很好地重建了原文的文体信息。伊恩·瓦特的文章《〈使节〉第一段:一种解释》对詹姆斯段落的风格进行了精彩的讨论,发表于《批评文集》第10期( Essays in Criticism ,1960),第254—268页;修订版见《20世纪对〈使节〉的诠释》( Twentieth-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Ambassadors ,1969),第75—87页。
[34] 托马斯·内格尔使用此短语来表征某种科学客观性的概念以及适用于它的观点。参见《本然的观点》( The View from Nowhere ,1986)。
[35] 关于叙事分析中的观点和相关概念,参见法国文学评论家G.热奈特《叙事话语》( Narrative Discourse ),J.E.卢因译本(1980)。
[36] 关于塞涅卡,参见努斯鲍姆《阿派朗》第20期( Apeiron ,1987)中《斯多亚学派论根除激情》一文,第129—177页;以及于1990年出版的《灵魂中的巨蛇:解读塞涅卡的〈美狄亚〉》,以纪念斯坦利·卡维尔。
[37] 文学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大课题。有两种途径可以了解它,一种是布鲁克斯的《为情节而阅读》,另一种是沃尔海姆的《艺术及其对象》。以及沃尔海姆于1989年2月在布朗大学发表的主题为“乱伦、弑父和艺术的甜蜜”的演讲。在这一领域具有代表性的两本同名著作《文学和精神分析》( 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 ),分别是1982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版本和1983年纽约版本。
[38] 为与我在此描述的立场密切相关的立场辩护的当代哲学家包括大卫·威金斯(详见注释46)、伯纳德·威廉斯(详见注释46)、科拉·戴蒙德(详见注释46)、约翰·麦克道威尔〔《美德与理由》一文,刊载于《一元论》第62期( The Monist ,1979),第331—350页〕,以及针对某些问题的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 Sources of the Self ,1989)〕。有关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讨论,参见A.罗蒂《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研究论文集》(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1980)和N.谢尔曼《性格的构造》( The Fabric of Character ,1989)。也见L.布卢姆《友谊、利他主义和道德》( Friendship, Altruism, and Morality ,1980)。
[39] 关于对特殊事物的感知,参见本书“洞察力”“‘细微的体察’”“感知的平衡”“感知与革命”和“斯蒂尔福斯的手臂”等章节。有关哲学讨论,参见前面引用的威金斯和麦克道尔的著作,以及保罗·德·曼《论辩与知觉:文学在道德探究中的角色》,《哲学期刊》第85期(1988)第552—565页,L.布卢姆《艾丽丝·默多克与道德领域》一文,《哲学研究》第50期(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86)第343—367页,以及《儿童道德的出现》( The Emergence of Morality in Young Children ,1987)中《特殊性与响应能力》一文。
[40] 尼采,《快乐的知识》( The Gay Science ,1974),第341节。米兰·昆德拉关于这种观点的讨论,参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1984)。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参见《政治学》1262b22—23,其中的观点在本书“洞察力”一章及《善的脆弱性》第十二章得到了讨论。
[41]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这种争论始于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对修辞学的抨击,对洛克(详见注释11)和康德有着巨大影响。同时参见L.布卢姆《友谊、利他主义和道德》(详见注释75)以及C.卢茨《非自然的情感》( Unnatural Emotions ,1988)。
[42] 对于这种立场不同类型的批评,参见人类学家卢茨和R.哈雷编辑的《情感的社会建构》(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Emotions ,1986)、梅勒妮·克莱恩在精神分析方面的作品以及詹姆斯·埃弗里尔关于认知心理学方面的著作。哲学领域,参见R.德苏萨《情感的理性》( The Rationality of Emotion ,1987),伯纳德·威廉斯收录于《自我的问题》中的《道德与情感》一文(详见注释46)。A.罗蒂编辑的《解释情感》( Explaining Emotions ,1980)中很好地汇集了各个领域的最新内容。
[43] 参见本书“洞察力”一章,《善的脆弱性》第三章有关克瑞翁的内容,以及科拉·戴蒙德刊登于《哲学研究》第5期(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1982)第23—41页的《绝非争论》一文。
[44]
出于明显的文化原因,实践推理中的情绪恢复已成为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一个突出主题:例如,参见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
In a Different Voice
,1982)。这本书的论点与女权主义的这项工作和其他相关工作有许多联系,提出了对所有想好好思考的人类都重要的问题。最近,关于情感在法律和法律判决中的作用,出现了非常有趣的进展。有关最近的两个不同示例,参见保罗·葛维宝收录于《哈佛法评论》第101期(
Harvard Law Review
,1988)第1043—1055页的《埃斯库罗斯法》一文,以及玛莎·L.米劳和伊丽莎白·V.斯佩尔曼共同创作的《正义的激情》一文,收录于《卡多佐法评论》第10期(
Cardozo Law Review
,1988)第37—76页。这两篇文章都深刻关注文学和文学风格在法律中的作用,并看到了这个问题与情感角色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且两者都与女权主义有关。)葛维宝雄辩的结论把这些兴趣汇集在一起:
……但是,非理性情绪虽然可以扭曲、迷惑或失控地迸发,但它们本身也有价值,也可以发挥作用,增进理解。法律体系的价值观和实现,以及律师、法官和参与法律体系的公民的价值观和实现,都是由他们的情感所决定的……这些观察结果表明,文学与法律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很少被明确化。文学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特殊主张,正是因为它滋养了人类的各种理解,而这种理解不是仅通过理性就能实现的,而且还涉及直觉和情感。如果像
奥瑞斯泰亚
建议的那样,法律涉及非理性因素,需要最全面的理解,那么文学可以在律师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将愤怒纳入法律范畴——这一范畴代表了情感领域与法律之间的联系——打通了文学本身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并强调了文学在发展法律意识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其达到最丰富和复杂的程度。(1050页)
关于这些问题,另见詹姆斯·博伊德·怀特《法律想象力》(
The Legal Imagination
,1973)、《当语词失去意义》(
When Words Lose Their Meaning
,1984)和《赫拉克勒斯的弓》(
Heracles’ Bow
,1985)。
[45] 参见本书“有瑕疵的水晶”一章,以及我刊载于《伦理学》第98期( Ethics ,1988)第332—340页的《论保罗·西布赖特》一文。
[46] H.詹姆斯《小说的艺术》第65页。关于詹姆斯的道德观,另见F.克鲁斯《风尚悲剧:亨利·詹姆斯后期小说中的道德戏剧》( Tragedy of Manners: Moral Drama in the Later Novels of Henry James ,1957)。
[47] 接近这一点的是艾丽丝·默多克在《善的主权》中使用的例子。其他开始研究这种复杂程度的哲学家包括伯纳德·威廉斯(详见注释46);托马斯·内格尔《人的问题》( Mortal Questions ,1979);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权利、补偿与风险:道德理论论文集》( Rights, Restitution, and Risk: Essays in Moral Theory ,1986)。
[48] D.科恩的《透明的头脑》( Transparent Minds ,1978)对意识小说中的隐私问题进行了精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