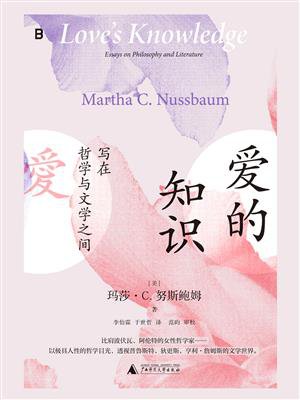Ⅱ.特殊事物的优先性
“洞察取决于感知。”这句话取自我的标题,亚里士多德在攻击伪科学理性图像的另一个特征——坚决主张在一般规则或原则的系统中把握理性选择,就是将这些规则或原则简单地应用于每个新案例——时用了这个短语。亚里士多德对“感知”的优先性的辩护,以及对实践智慧不能是一门涉及普遍和一般原则的系统科学的坚持,显然是一种对具体情境判断的优先性的辩护,这种判断对于任何这类体系而言都更为非正式和更直观。他再一次抨击了一个在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公共领域,被普遍视为理性标准的事项。他对伦理一般性的抨击与对可通约性的抨击密切联系。因为这两个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在他们的辩护者看来,这两个概念都是进步的策略,我们可以用它来摆脱伦理上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产生于对异质性的感知。太多的异质性会让看到它的能动者有可能感到惊讶和困惑。一种新的情况可能会使她感到不一样。一件有价值的事物可能看起来完全不同且新颖。但是,如果她告诉自己,要么只存在一项,按照它来看,所有的价值都是可衡量的——要么有一个有限数量的一般价值,按照它来看,所有的新案例必然会沦为实例——通过这两种途径中的任何一种,她都会摆脱棘手和意想不到的负担。每到一个新情况,她都准备只看那些她已经知道如何进行慎思的事项。
对异质性的感知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易受损失。如果把心爱的人(国家、职业)看作并不独特的,而是同质的一般概念的一个实例,即如果世界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现在拥有的东西,那么这个实例就有可能被另一个类似的实例所替代。柏拉图笔下的狄奥提玛认为,以这种方式使一般优先于特殊,可以“放松”和“缓解”在规划生活中所涉及的紧张。就价值的一般性而言,就像可通约性更激进地化约为单一价值一样,如果这个世界拿走了你喜欢的东西,那么很可能就会有其他类似价值的物品作为替代。许多希腊思想家认为,一个真正理性的决策程序的标准是,它应该消除我们的一些伦理困惑和脆弱性,让我们在控制更重要的事情的过程中更为安全。这个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在这里,我们必须开始区分
一般性
(general)与
普遍性
(universal),亚里士多德自己并没有对二者加以区分,或区分得并不清晰。
一般性
与
具体性
相对,一般规则不仅适用于许多案例,而且凭借某些相当不具体的特点,它还应用于这些案例。相反,
普遍性
规则应用于所有相关方式相似的案例。但是普遍性可能是高度具体的,它所援引的特征不太可能被复制。许多基于普遍原则而正确选择的道德观念,采用了广泛的一般性原则。如果人们对原则的编纂和行动指导力量感兴趣,那么这是一个自然的联系。一个人不能用规则来教孩子做什么,它的条款太过具体,以至于无法让孩子为尚未遇见的新情况做好准备;传统上,道德规则的认识论作用之一是简化和系统化道德世界,这是一项高度精细和具体的普遍性所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普遍性也可能是具体的。许多哲学家,尤其是R.M.黑尔对道德规定的普遍性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也坚持认为,原则通常应该具有高度的情境特殊性。亚里士多德有关在伦理推理中“特殊事物”是“优先的”的主张,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论证,既针对一般原则,也针对普遍原则。他对一般性的抨击,更具有全球性和根本性。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普遍性,尽管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他否认其道德角色,他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说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同样的选择也将再次正确是不正确的。为了清楚地描述这一观点和支持它的论证,我们必须比亚里士多德更有力地坚持这种区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对手是柏拉图,他的普遍性也具有高度的一般性。
他也坚持认为,原则通常应该具有高度的情境特殊性。亚里士多德有关在伦理推理中“特殊事物”是“优先的”的主张,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论证,既针对一般原则,也针对普遍原则。他对一般性的抨击,更具有全球性和根本性。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普遍性,尽管我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他否认其道德角色,他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说相同的情况再次发生,同样的选择也将再次正确是不正确的。为了清楚地描述这一观点和支持它的论证,我们必须比亚里士多德更有力地坚持这种区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对手是柏拉图,他的普遍性也具有高度的一般性。
亚里士多德对可通约性的反对论证本身,并不意味着特殊的判断优先于一般规则。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他对可通约性的攻击依托于那幅有各种独特价值的多元图景,在那里每种价值都有其自身的主张,但每种价值也有其自身的一般性定义,并且可在任何数量的特定情况和行动中以实例的方式呈现。因此,例如,勇气、正义和友谊是多元的和独特的,这一简单事实并不能支持特殊感知优先于规则或原则体系。相反,我们关于定义中的独特性的讨论表明,亚里士多德可能对这样一个体系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见,亚里士多德坚持实践智慧不是 理论认识 (epistēmē),即系统的科学理解。他通过论证其与 终极特殊事物 (ta kath’ hekasta)有关,这些特殊事物不能被包含在任何 理论认识 (一个普遍原则的系统)之下,而是必须通过经验的洞察来把握(《尼各马可伦理学》1142a11及以下)。在赞赏感知时,他赞赏的是对这种经验判断中所包含的对特殊事物的把握。他的声明似乎是对 一般性 的优先性的攻击,也可能是对 普遍性的 优先性的攻击。于是我们需要问,从多元性到特殊性或具体性,有时也是从具体性到单一性的进一步运动是如何得到辩护的。我们还需要知道,各种各样的规则在亚里士多德式理性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规则可以在实践理性中发挥重要作用,而无须先于对特殊性的感知。
 因为它们可能不是作为感知的规范,也不是作为评估特定选择正确性的最终权威,而是作为总结或经验法则,对各种目的都非常有用,但只有当它们正确地描述了好的具体判断时才有效,并最终根据这些判断进行评估。在这第二幅图景中,仍有空间将我们面前案例的新的或令人惊讶的特征、规则中未预料到的特征,甚至原则上无法在任何规则中捕捉到的特征,识别为伦理上的突出特征。如果亚里士多德关于规则的论述属于第二种类型,那么他对规则和定义的明显兴趣与他对感觉优先性的辩护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立。我现在想论证,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并探讨他给予特殊性优先性的原因所在。
因为它们可能不是作为感知的规范,也不是作为评估特定选择正确性的最终权威,而是作为总结或经验法则,对各种目的都非常有用,但只有当它们正确地描述了好的具体判断时才有效,并最终根据这些判断进行评估。在这第二幅图景中,仍有空间将我们面前案例的新的或令人惊讶的特征、规则中未预料到的特征,甚至原则上无法在任何规则中捕捉到的特征,识别为伦理上的突出特征。如果亚里士多德关于规则的论述属于第二种类型,那么他对规则和定义的明显兴趣与他对感觉优先性的辩护之间根本不存在对立。我现在想论证,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并探讨他给予特殊性优先性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从提出了我们标题中的句子的这两篇文章开始,在这两篇文章中他都明确声称,在实践选择中,优先考虑的不是原则,而是感知,这是一种与理解具体特殊事物有关的辨别能力:
然而,尽管我们不谴责稍稍偏离正确——无论是过度还是不及——的人,但我们会谴责偏离得 太多 的人,因为偏离已显而易见。至于一个人偏离得多远、多严重就应当受到谴责,这很难依照原则来确定。这正如很难确定感知的题材一样。因为这类事物处于具体的特殊状况中,对它们的洞察取决于对它们的感知。(《尼各马可伦理学》1109b18—23)
在讨论特定的德性之一,即温和的脾气时,亚里士多德再次写道:“什么程度和类型的差异性应该受到指责,很难依照任何一般的原则来确定。因为洞见取决于特殊事物以及对它们的感知。”(1126b2—4)。一个复杂的伦理情境的微妙之处必须在与情境本身的对抗中予以把握,这种把握凭借的是一种适合将这种情境作为一个复杂整体来处理的能力。先前的一般性规划缺乏所需的具体性和灵活性。它们不能容纳近在眼前的、特殊化了的细节,而后者则是决策必须把握的东西;它们对现有的情况缺乏回应,而一个好的决策必须如此。
这两个相关的批评被反复强调,因为亚里士多德主张具体描述较之于一般陈述在伦理上的优先性,特殊判断较之于一般规则的优先性。“在关于行动的表述中,”他在相邻的段落写道,“那些
普遍性
(katholou)的更具
一般性
(koinoteroi,许多事物的共性),
 但那些特殊事物则更为真实——因为行动关乎特殊事物,表述也必须同这些相吻合。”(1107a29—32)原则只有在正确的情况下才具有权威性,但它们只有在所涉及特殊事物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一个旨在涵盖许多不同特殊事物的表述不可能达到很高程度的正确性。因此在他对正义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能动者的经验判断必须纠正和补充法律中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表述:
但那些特殊事物则更为真实——因为行动关乎特殊事物,表述也必须同这些相吻合。”(1107a29—32)原则只有在正确的情况下才具有权威性,但它们只有在所涉及特殊事物没有错误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一个旨在涵盖许多不同特殊事物的表述不可能达到很高程度的正确性。因此在他对正义的讨论中,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能动者的经验判断必须纠正和补充法律中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表述:
法律是普遍性的,但有些事情不可能只靠普遍陈述解决。所以,在需要用普遍性的语言说话但是又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地方,法律就要考虑通常的情况,尽管它不是意识不到可能发生的错误。……所以,法律制订一条规则,就会有一种例外。当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而有缺陷和错误时,由例外来纠正这种缺陷和错误,来说出立法者自己如果身处其境会说出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137bl3及以下)
只要法律是明智决定的总结,它就具有权威性。因此,用临场做出的明智的新决定来补充它是适当的;如果它与一个好的法官对于案件所做的评判相偏离,那么纠正它也是恰当的。在这里,我们再次发现,对特殊性的判断在正确性和灵活性方面都是更具优势的。
亚里士多德用一个生动而著名的隐喻阐明了伦理灵活性的观念。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在做出每一个选择的时候,都是根据某种预先存在的一般性原则,这种原则在应对特定场合时是固定的且缺乏灵活性,就像一个建筑师试图用直尺画出一个有凹槽的柱状物的复杂曲线。没有一个真正的建筑师会这样做。相反,他将跟随莱斯沃斯岛建造者的脚步,用一种灵活的金属条“莱斯比亚尺”来测量,这种金属条“弯曲成石头的形状且不固定”(1137b30—32)。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这种工具仍在使用。我就有一个。它对于测量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老房子的奇怪形状部分极其有用。(有功利主义者最近写道,“我们”更喜欢包豪斯风格的道德体系,
 考虑到他对规则的看法,他有这样的建筑品位算幸运。)它也可以用于测量身体的各个部分,人体笔直的部分很少。并不很奇怪,我们可以预见我们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有关伦理现实的图景是一种人类身体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数学上的构造。好的慎思,就像莱斯比亚尺,适应它所找到的形状,回应并尊重复杂性。
考虑到他对规则的看法,他有这样的建筑品位算幸运。)它也可以用于测量身体的各个部分,人体笔直的部分很少。并不很奇怪,我们可以预见我们的观点,即亚里士多德有关伦理现实的图景是一种人类身体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数学上的构造。好的慎思,就像莱斯比亚尺,适应它所找到的形状,回应并尊重复杂性。
但也许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只是谈论实际规则系统的缺陷;或许他并没有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如果规则足够精确或复杂,伦理科学就会出现。莱斯比亚尺的形象并不鼓励这种想法。但我们可以进一步回答这个反对意见,首先表明他认为正确的选择,即使在原则上,也不可能在一个规则系统中获得,然后继续指出“实践事务”的三个特点,以表明为什么不这样做。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的同一部分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实践事务在其本质上是不确定的或 无法定义的 (aorista)——不仅仅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充分定义。普遍陈述的失败是因为缺乏能充分捕捉到这一问题的普遍性。“错误不在于法律或者立法者,而在于事物的本性,因为实践事务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1137b17—19)。在第二卷中,他再次讨论了普遍定义和陈述在伦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准备提出他自己对美德的定义),他写道:
让我们从开始达成共识,每一种有关实践事务的陈述都应该以粗略的、而不是精确的方式表达。我们一开始就说过,这些陈述被要求以一种适合于临场情况的方式予以表达。实践事务的问题以及什么更为优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正如健康的问题一样。如果普遍的定义是这样的,那么涉及特殊性的定义在精确性上甚至会更为缺失。因为这些情况不会被归入任何科学或者规则,但能动者自身必须在每一种情况下发现适合于这一情况的选择,就如在医疗与航海领域一样。(1103b34—l104a10)
一般性陈述
应该
 仅仅作为一个提纲,而不是精确的结束语而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伦理学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精确性,它甚至不应该试图如此精确。
仅仅作为一个提纲,而不是精确的结束语而存在。这不仅是因为伦理学还没有达到科学的精确性,它甚至不应该试图如此精确。
这段简短的篇章中暗示了三点理由。首先,实践事务是可变的,或者说缺乏稳定性。一个预先建立的规则体系只能包含以前见过的东西——就像医学论文只能给出一种已认识到的疾病形式一样。但是,变化的世界使我们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结构、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来决定美德行为的取向。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德本身是有个体性的,并且是根据特定的情境来定义的(例如,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一个拥有共产主义财产制度的城市里,不存在慷慨的美德),
 好的能动者可能不仅需要在陌生的新事件中确立美德行为,而且还需要处理一个不断变化的、与情境相关的美德列表。亚里士多德说,即使是人类的自然正义“都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植于历史之中的,跟稀缺环境有关,也跟个人的独立性相关,这种独立性相对稳定,但仍然存在于自然的世界之中。
好的能动者可能不仅需要在陌生的新事件中确立美德行为,而且还需要处理一个不断变化的、与情境相关的美德列表。亚里士多德说,即使是人类的自然正义“都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植于历史之中的,跟稀缺环境有关,也跟个人的独立性相关,这种独立性相对稳定,但仍然存在于自然的世界之中。
 一个医生在面对一种新的症状时只求助于教科书,那他将是一个糟糕的医生。当面对一次在方向和强度上都无法预料的风暴时,一个只会按规则驾驶船只的船长将是无能的。即便如此,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必须以回应和想象来迎接新事物,培养灵活性和洞察力,用修昔底德的话(亚里士多德是其阐明的雅典理想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的话来说,这将使他们能够“就所需要的东西进行即兴发挥”(Ⅰ. 118)。在好几篇文章中,亚里士多德都把实践智慧说成一种与
随机思维
(stochazesthai)相关的能力。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瞄准目标”,后来表示一种对理性的即兴揣测性的使用。他告诉我们,“一个善于慎思但缺乏学历的人是一个能够根据理性
瞄准目标
(stochastikos)从而实现人可获得的最大的善的人。”(1141b13—14)。他将这种典范与实践智慧关注特殊事物而非普遍事物的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1141b14—16)。
一个医生在面对一种新的症状时只求助于教科书,那他将是一个糟糕的医生。当面对一次在方向和强度上都无法预料的风暴时,一个只会按规则驾驶船只的船长将是无能的。即便如此,拥有实践智慧的人必须以回应和想象来迎接新事物,培养灵活性和洞察力,用修昔底德的话(亚里士多德是其阐明的雅典理想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的话来说,这将使他们能够“就所需要的东西进行即兴发挥”(Ⅰ. 118)。在好几篇文章中,亚里士多德都把实践智慧说成一种与
随机思维
(stochazesthai)相关的能力。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瞄准目标”,后来表示一种对理性的即兴揣测性的使用。他告诉我们,“一个善于慎思但缺乏学历的人是一个能够根据理性
瞄准目标
(stochastikos)从而实现人可获得的最大的善的人。”(1141b13—14)。他将这种典范与实践智慧关注特殊事物而非普遍事物的观察紧密联系在一起(1141b14—16)。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以及第二卷的一个含蓄的段落的表达中,亚里士多德暗示了实践的第二个特征,即它的 不确定或难以定义的特性 (to aoriston)。这一特征很难解释,这似乎与实践语境的多样性和恰当选择的情境相对性有关。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亚里士多德写道,好的笑话 没有定义 (horismos),它是 不确定的 (aoristos),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悦特定的听众,而且“对不同的人来说,令人厌恶或愉快的事物是不同的”(1128a25及以下)。从这个例子中可以推断出,卓越的选择不可能通过一般规则来把握,因为这是一个让一个人的选择符合具体情况的复杂要求的问题,要考虑到它的所有情境特征。一个规则,就像一本幽默手册,只会不到位或做过头:不到位,是因为最重要的是对具体事物的回应,而这点被忽略了。太过头,是因为这条规则意味着它本身具有对回应的规范性(就像一本笑话手册要求你根据其所包含的公式去剪裁你的巧智),这将对良好实践的灵活性造成很大影响。之所以称莱斯比亚尺为 不确定的 (aoristos),大概是因为此类尺子会根据面前需要丈量的事物的形状而改变自己的形状。在说到可变性时,亚里士多德强调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以及与道德相关的惊奇;在谈到 难以定 义 (aoriston)时他强调了复杂性和语境。这两个特点都要求回应性、柔软的灵活性、语气的贴切以及任何一般陈述都无法充分捕捉到的那种确信。
最后,亚里士多德指出,具体的伦理案例可能只包含某种终极的特殊性与不可重复的要素。当他说它们根本不属于任何一般科学或规则时,这就是他的意思的一部分。复杂性和多样性已经产生了高度的情境特殊性,直截了当地说,因为属性的出现,这些属性在其他地方以无尽的多样性组合实例化,使得整个情境显得独一无二。但亚里士多德也认识到不可重复成分的伦理相关性。摔跤手米洛的适度饮食和亚里士多德的适度饮食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对任何其他人来说也不同),因为米洛具体且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体型、体重、需求、目标和活动的组合,都与确定适合他的饮食有关。这是一种对普遍性的偶然限制。我们可以试着说,我们在这里有一种仅有唯一实例的普遍原则,如果有其他任何人以那样精确的尺寸、重量等出现,道德准则将是相同的。即便如此,这也不是那种能满足大多数原则信徒的普遍原则,因为它根植于米洛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中,在某种程度上,它不可能被预先精确地预料到;也许(确实很有可能)在未来将不再有用。一种依托于特定情境下的“原则”的伦理科学需要有一系列大量的、可以无限扩展的原则,这不是一门能够满足那些寻求科学的人的科学。
但在某些情况下,亚里士多德走得更远一些。爱情和友谊的特殊性似乎需要一种更加强烈意义上的不可重复性。好朋友会关心他们朋友的特殊需要和关切,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需求甚至更多。其中一些“他们自身”由可重复的性格特征组成,但是,共享的历史和家庭关系的特征,即使在原则上是不可重复的,也被允许承担重要的伦理重量。在这里,能动者的个体背景特点(和/或关系本身的背景特点)以一种原则上不能产生普遍性原则的方式进入了道德慎思,因为伦理上重要的(在其他事情中)是把朋友当作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存在,一个不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人的存在。
 “实践智慧也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认识到特殊事物。因为它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关注特殊性。”(1141b4—16)
[11]
“实践智慧也不是只同普遍的东西相关。它也要认识到特殊事物。因为它是与实践相关的,而实践就是要关注特殊性。”(1141b4—16)
[11]
所有这些被视为对于判断的正确性具有规范性的方法、规则,无论一般的和/或普遍的,在本质上都无法面对实践选择的挑战。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不仅强烈反对系统等级规则的规范性使用,而且一般来说反对用任何一般算法来做出正确选择。其对莱斯比亚尺的辩护和对情境相关工具的描述含蓄指出,不仅优秀的法官不会根据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案件,而且也没有一般性的程序或算法在每个案件中来计算应该做什么。适当的回应并不是以机械的方式抵达;关于如何找到它,并不存在一般性的程序说明。或者,如果有的话,它的用途就如同一本笑话手册,并具有潜在的误导性。在这里,亚里士多德的图景与当代试图描述一种有关选择的一般性公式或技术的尝试截然不同,前者可被应用于每一个新的特殊事物。亚里士多德并不反对为特定目的而使用一般性的指导方针。只要不偏离自己的位置,它们就能扮演有用的角色。规则和一般性的程序能够成为道德发展中的助手,因为那些还没有实践智慧和洞察力的人需要遵循总结他人明智判断的规则。同样,如果眼前情况没时间做出一个充分具体的决定,那么遵循一个好的概要规则或标准化的决策程序,而不是做出匆忙和不充分的情境选择是更好的。同样,如果在一个既定情境中我们对自己的判断没有信心,如果有理由相信偏见或兴趣会扭曲我们的特殊判断,那么规则就会给我们更好的一贯性和稳定性。〔这是亚里士多德偏爱法治(rule by law)而非政令统治(rule by decree)的首要论证。〕即使对那些不缺时间的明智成年人来说,这一规则也有一个功能,它可以尝试性地通过其方式引导他们接近新的特殊事物,帮助他们找出其显著特征。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研究它的功能。
但亚里士多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的观点是,规则或算法体现了一种对恰当的实践理性的背弃,而不是它的繁荣或完成。一种形式上的选择功能的存在并不是理性选择的条件,就像导航手册的存在不是良好导航的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通常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一样。选择功能仅仅是对优秀法官到目前为止所遇到的情况所做或已经做过的判断的总结——在这种情况下,它是真实的,但却是事后的,而且越是事后的,它就越简化。
 或者它试图从他们所做的和已经做过的事情中提取一些更简洁和简单的程序,这样以后就可以成为他们行为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错误的,甚至是堕落的。
或者它试图从他们所做的和已经做过的事情中提取一些更简洁和简单的程序,这样以后就可以成为他们行为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它将是错误的,甚至是堕落的。
在评估这一主张时,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亚里士多德式慎思并不将自己限制在手段—目的的推理中。正如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它也与终极目的的特殊性相关。但这意味着这些基于情境的和不可重复的材料可以在一个层面上进入能动者的慎思之中,这一层次较之于计算和(例如)与此相关的概率计算更为基本。 理性 慎思的很大一部分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此时此刻的某一行动是否真的可以算作实现了某些重要的价值(比如勇气或友谊),这是她对好生活的初步认识;或者甚至是某种行为方式(某种特定关系——类型或特殊性)是否真的是她想要包含在她的好生活概念中的东西。这种友谊,这种爱,这种勇敢的冒险,是否真的是这样一些如果缺失将会使她的生活变得不那么有价值以及不那么完整的东西。对于这类问题,看起来显然没有数学意义上的回答;唯一能够遵循的路径(我们将会看到)是尽可能完整而具体地想象所有相关的特征,把它们与我们带入情境或者能够在其中形成的任何直觉、情感、计划和想象相对照。这里真的根本没有任何捷径,或者说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关于正确程序的理论,我们所掌握最多的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作的关于好的慎思的论述,这一论述故意说得不多,在谈论品格的时候涉及了这个内容。他的论述不仅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计算中庸之道,而且他还说这个问题没有一般性的正确答案。除此之外,理性选择的内容必须由混乱程度不亚于经验以及经验的故事所提供。在各种关于行动的故事中,最为真实和最能增长见识的是文学作品、传记以及历史;故事越抽象,将其当作一个人的唯一向导就越缺少理性。好的慎思就像戏剧或音乐的即兴表演,关键在于灵活性、回应性以及对外界的开放性。在此依赖一种算法不仅是不够的,而且还是不成熟和虚弱的表现。根据乐谱演奏爵士独奏曲是可能的,只要对自己乐器的特殊性质稍加改动就可以了。问题是,谁会这么做,又为何这么做?
如果这一切都是这样,亚里士多德也必须避免对成年人的慎思理性的特点给出任何正式的规范解释。因为,就像它的主题一样,它太灵活了,以至于无法用一般性的方式来确定。相反,他强调经验在赋予实践智慧内容方面的重要性,并在实践洞察力和科学或数学理解之间进行了对比:
实践智慧显然不是化约了的
科学理解
(epistēmē)。如已说明的,它是终极的和特殊的——因为行动就是如此。它是一种理论洞察(
奴斯
 )的模拟:因为,奴斯相关于始点,对这些始点是讲不出逻各斯来的。实践智慧相关于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科学的对象。不过这不是说那些具体感觉,而是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1142a23)
)的模拟:因为,奴斯相关于始点,对这些始点是讲不出逻各斯来的。实践智慧相关于具体的事情,这些具体的东西是感觉而不是科学的对象。不过这不是说那些具体感觉,而是像我们在判断出眼前的一个图形是三角形时的那种感觉。(1142a23)

实践洞察力就像一种非推理的、非演绎意义上的感知;它是一种识别复杂情况的显著特征的能力。正如理论性的 奴斯 (nous)只能来自对第一原则的长期经验和在经验中逐渐获得的感觉,来自这些在话语和解释中的原则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同样,实践感知,亚里士多德也称其为 奴斯 ,只有通过长期的生活和选择历程才能获得,这一历程会发展能动者的足智多谋和回应能力:
青年人可以成为数学家或几何学家,并对类似事物颇有智慧,但是我们在他们身上却看不到实践智慧。原因就在于,实践智慧是同具体的事情相关的,这需要经验,而青年人缺少经验。因为,经验总是日积月累的。(1142al2—16)
以及:
我们用体谅、理解、实践智慧和奴斯来说同样一些人,我们说他们长大了,懂得体谅了,有奴斯
 了,拥有实践智慧了和学会理解了。因为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同终极的、具体的问题相关的……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是终极的、具体的(拥有实践智慧的人都承认这些事情),而理解与体谅也是同终极的实践问题相关的。其次,奴斯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在把握基本原理和把握终极细节之间,出现了一种平行的发展。)……所以,对有经验的人、老年人和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见解与意见,即使未经过证明,也应当像得到了验证的东西那样给予重视。因为经验使他们生出慧眼,使他们能看得正确。(1143a25—bl4)
了,拥有实践智慧了和学会理解了。因为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同终极的、具体的问题相关的……所有的实践问题都是终极的、具体的(拥有实践智慧的人都承认这些事情),而理解与体谅也是同终极的实践问题相关的。其次,奴斯把握终极的、可变的事实和小前提。……(在把握基本原理和把握终极细节之间,出现了一种平行的发展。)……所以,对有经验的人、老年人和拥有实践智慧的人的见解与意见,即使未经过证明,也应当像得到了验证的东西那样给予重视。因为经验使他们生出慧眼,使他们能看得正确。(1143a25—bl4)
现在,我们倾向于问:如果实践智慧所看到的事物是独特的和崭新的,那么经验可能会做出什么贡献?然而,对灵活性的强调不应使我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感知是毫无根据的和极为特殊的、拒绝了过去的一切指导。好的航海家不会根据规则手册来导航,她已经准备好应对她从未见过的情况。但她也知道如何利用她已经看到的东西,她并不假装自己以前从未坐过船。经验是具体的,而无法在一个规则系统中得到彻底的概括。不同于数学上的智慧,它无法通过一篇论文来得到充分体现。但它确实提供了指导,它确实敦促我们认识到那些重复性的特征以及独一无二的特征。即使规则是不充分的,但它们也可能非常有用,甚至经常是必要的。我们将在第五节讨论这一重要问题,并以亚里士多德式慎思的具体例子加以讨论。现在我们来看他的概念的第三个特征,这将进一步阐明其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