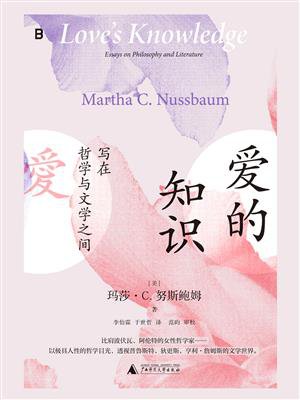Ⅲ.情感与想象的理性
到目前为止,亚里士多德式的图景抨击了两个被普遍认为是理性标准的事项。他的第三个目标甚至更为宽泛:理性选择不是在情感和想象的影响下做出的。关于理性慎思可能利用甚至被这些元素所引导的观点,有时甚至(在古代和现代)被认为是一种概念上的不可能,即“理性的”被定义为与灵魂的这些“非理性的”部分相对立。(情感尤其如此,古代和现代的重要作家都把想象力纳入他们对非理性的指责中。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像斯图尔特·汉普希尔这样的哲学家同样如此,他在其他方面都赞同亚里士多德的选择概念。)
 柏拉图否定了情感和欲望,认为它们是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者,坚持认为只有鼓励理智“自身独立”,尽可能不受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正确的实践判断。引导或指引理智的人的状态被赋予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名字“疯狂”,这是与理性或健全的判断相对立的。
[12]
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主流道德理论,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激情的怀疑丝毫不减;事实上,这是他们(通常)达成共识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对康德来说,激情总是自私的,以个人的满足状态为目标。即使是在爱情和友谊的背景下,他也敦促我们避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因为一种行为只有在其本身被选择时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考虑到他对激情的理解,他不能允许行动仅仅或主要是因为激情而被选择。功利主义者认为,像个人爱情这样的激情往往因为过于狭隘而阻碍了理性:它导致我们强调个人间的联结,并以远近来决定亲疏关系,阻碍了对世界持完全无偏倚的态度,而这种无偏倚性是功利主义理性的标志。
柏拉图否定了情感和欲望,认为它们是具有破坏性的影响者,坚持认为只有鼓励理智“自身独立”,尽可能不受它们的影响,才能达到正确的实践判断。引导或指引理智的人的状态被赋予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的名字“疯狂”,这是与理性或健全的判断相对立的。
[12]
我们这个时代的两大主流道德理论,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对激情的怀疑丝毫不减;事实上,这是他们(通常)达成共识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对康德来说,激情总是自私的,以个人的满足状态为目标。即使是在爱情和友谊的背景下,他也敦促我们避免受到它们的影响,因为一种行为只有在其本身被选择时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考虑到他对激情的理解,他不能允许行动仅仅或主要是因为激情而被选择。功利主义者认为,像个人爱情这样的激情往往因为过于狭隘而阻碍了理性:它导致我们强调个人间的联结,并以远近来决定亲疏关系,阻碍了对世界持完全无偏倚的态度,而这种无偏倚性是功利主义理性的标志。
想象力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柏拉图对感性认识影响的拒绝是他对身体影响的普遍拒绝的一部分。在不试图描述康德自己关于想象的复杂观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现代康德主义者对抑制慎思想象力的飞翔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慎思想象力被视为对按照职责来行动的潜在巨大障碍。想象常常被认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和任性的、过于关注特殊事物以及它们与自我的关系。一个人可以在不发展想象的情况下被责任正确地激励,因此,想象力的培养往好里说是一种奢侈,往坏里说是一种危险。
功利主义者也不赞成想象力用它们所有的色彩和奇异性来对选择方案做栩栩如生的描绘。这种能力再次被怀疑致力于特殊性和对不可通约性的认识,因此是一种对事实和可能性的公正评估的威胁。不管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作为功利主义的一个肖像存在什么错误——错误还很多——但其对那位边沁式的父亲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这位父亲持有“幻想(fancy)”是一种危险的自我放纵的观点。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合宜公正的社会,这个理由(被认为是一种储存事实和计算的能力,正是凭借这种能力,葛莱恩先生总是“随时准备掂量和测算人性的每一部分,并准确地告诉你它共计多少”)是唯一一种教育在设法恰当培养的能力。(关于路易莎,她从摇篮起就没有接触过任何幻想,他带着道德上的满足沉思着,“那将是任性的……但是为了她的成长”。)当代理论家以这些作为榜样,要么明确地否定想象和情感,认为其是非理性的,要么提供一幅理性在其中并不扮演积极角色的图景。
我已经勾勒出这些拒绝想象和情感的动机,以表明亚里士多德式感知可能有相应的动机来培养它们。如果这些能力确实与我们掌握特殊事物的丰富性和具体性的能力密切相关,那么感知漠视它们的话就会处于险境。当我们追寻这条线索时,我们同时需要看到亚里士多德如何对认为这些能力始终是扭曲的和自私的指控做出回应。
亚里士多德没有一个与我们的“想象”完全一致的概念。他的
幻想
(phantasia)——通常如此翻译——是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人类与动物的能力,即专注于某些具体事物,无论是在场还是不在场的,以将其视为(或以其他方式感知)某物的方式,识别其突出之处。
 这个功能是感知的积极的和选择性的方面。但
幻想
也与记忆密切相关,使人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在场的被经历过的事物的具体性上,甚至还构成了尚未经历过的,源自感觉经验中的事物的新的结合。因此它能承担很多我们的想象力的工作。尽管需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重点是幻想的选择性和辨别力特征,而不是其自由幻想的能力。它的工作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是创造非现实。
这个功能是感知的积极的和选择性的方面。但
幻想
也与记忆密切相关,使人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在场的被经历过的事物的具体性上,甚至还构成了尚未经历过的,源自感觉经验中的事物的新的结合。因此它能承担很多我们的想象力的工作。尽管需要强调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重点是幻想的选择性和辨别力特征,而不是其自由幻想的能力。它的工作更多地关注现实而不是创造非现实。
幻想 似乎是一种适合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慎思活动的能力,所以他在“实践三段论”的小前提中引用它,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造物将世界上某个事物感知 为 某物是对他或她的实践利益或关切的回答。在其他地方,他展示了想象力与一种善的伦理概念之间的紧密合作:我们对一种情况的想象力“标记”或“决定”了它所呈现的元素与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相对应。 [13] 他认为人类有一种特殊的想象能力,这不足为奇,这种想象被称为“慎思 幻想 ”,它包含了一种将各种想象或感知联系到一起的能力,“从多样中形成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思想(在有限的生物里)都必然伴随着一种具体的想象,即使思想本身是抽象的。这只是人类心理的一个事实。然而,当数学家在证明一个三角形的定理时,可以安然地忽视他或她所想象的具体特征,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则在思考美德与善时不会忽视想象力的具体释放。不同于从特殊上升到一般,慎思性的想象将各种特殊事物联系起来,不忽视它们的独特性。 [14] 例如,它包括回忆过去经历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与手头的案例相关,同时仍然以丰富和生动的具体方式构思两者。我们现在要理解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这种对具体性的关注并不是具有危险性的非理性,而是一种负责任的理性的关键要素,是由教育者培养的。
至于情感,亚里士多德出了名地将其重新置于道德的中心地位,柏拉图曾在此将其驱逐。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好人不仅会在行动上做得好,而且会对自己的选择产生恰当的情感。不仅是正确的动机和动机性情感,而且正确的反应或回应性情感,也都构成了这个人的美德或善。如果我出于错误的动机或欲望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获得),那就不能算作具有德性的行为。就连康德也承认这一点。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必须在没有勉强或内心情绪紧张的情况下做正确的事。如果我的正确选择总是需要内心的斗争,如果我必须始终要克服那些与美德相悖的强烈情感,那么我就不如那些情感与行为一致的人具有美德。我的激情跟我的计算同样是易于实现的,所有这些都是实践理性的组成部分。
这背后是一幅激情作为个体的回应性和选择性元素的图景。它们不是柏拉图式的冲动(urges)或推力(pushes),它们具有高度的可教育性和辨别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甚至食欲也是具有意向性的,并能进行识别;它们可以告知能动者所需对象的存在,与知觉和想象进行回应性的互动。
[15]
它们的意向性对象是“表面的善”。情感是信念和感觉的混合物,由发展的思想所塑造,并且在反应中具有很高的辨别度。它们可以引导或指导感知的能动者,在具体的想象情境中“标记出”要追求和避免的对象。简而言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认知和情感之间做出明显的划分。情感可以扮演认知的角色,而认知如果要得到正确的信息,就必须利用情感因素的作用。
 毫无疑问,选择被定义为一种介于理智和激情之间的能力,兼具两者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指出,它或者可以被描述为慎思,或者也可以被描述为慎思的欲望(《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10—12,1139b3—5)。
毫无疑问,选择被定义为一种介于理智和激情之间的能力,兼具两者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指出,它或者可以被描述为慎思,或者也可以被描述为慎思的欲望(《尼各马可伦理学》1113a10—12,1139b3—5)。
综上所述,并允许我们以一种似乎符合其精神的方式从文本中进行推断,我们可以说,一个具有实践洞察力的人会在面对新情况时培养情感上的开放性和回应性,而不是那种超然的思考,前者会将她引向恰当的认知。“当一个朋友需要我的帮助时”:这通常首先会被视为友谊的组成部分的感情,而不是纯粹的知性。富于才智的人经常会想要求教于这些感觉以获得有关情况的真实性质的信息。没有它们,他处理新情况的方式将是盲目和迟钝的。即便选择是正确的,但在缺失感觉与情感回应的情况下发生,亚里士多德还是认为较之基于情感的选择,这种选择在美德上是有缺失的。如果我没有感情地帮助朋友,比起带着适当的爱和同情去帮助朋友,那么我就不值得赞扬。的确,我的选择可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美德;要使行为具有美德,它不仅必须与具有美德倾向的人的行为具有同样的内容,还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去行动,就像一个热爱善的人所做的。没有感觉,正确感知的一部分就会丧失。
我相信,这样的陈述暗示了感知不仅得到了情感的协助,而且部分也由适当的回应所构成。好的感知是对实践情况本质的充分认识或承认,从整个人格看到它的本质。一个理智地辨别出朋友需要帮助或所爱的人去世的能动者,却不能以适当的同情或悲伤来回应这些事实,显然缺乏部分亚里士多德式美德。此外,似乎可以这样说:此人缺乏部分辨别力或感知。这个人没有真正地,或者没有完全 看到 发生了什么,没有以一种强烈的情感方式认识它或领会它。我们想说的是,她只是说说而已。“他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她死了”,但实际上说此话者还没有完全 意识到 这一点,因为认知中的情感部分是缺失的。这并不仅仅是有时我们需要情感来正确地(理智地) 看待 情况;这是事实,但不是全部。这也不是说情感提供了认知之外值得称赞的元素,而是说没有这些元素美德就不完整。情感本身就是视觉(vision)或认知的模式。它们的回应就是“知道”的一部分,也就是真正的认知或承认。这就回应了:“在适当的时间、参考适当的对象,对于适当的人,出于适当的原因,以适当的方式感受这些感情,就既是适度的又是最好的,这就是卓越的特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6b21—23)
以这种方式阅读亚里士多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解释上和哲学上的好处,在此只能简要地描述一下。在拒绝了苏格拉底关于 不自制 (akrasia)的解释之后,它一直困扰着诠释者,根据那个解释,所有违背伦理知识的行为都是由理智失败造成的,亚里士多德进而提供了自己的解释,把 不自制 本身描述为理智的失败。在苏格拉底那里,这种认为一个人由于被愉悦或激情所压倒,从而知道什么是更好、什么是更坏的日常信念遭到了嘲笑,他认为,这些失败实际上要归结于无知。亚里士多德坚定不移地捍卫日常信念,确实提到了在 不自制 状态中对快乐的欲望所扮演的激发性角色;但他说,这种欲望不会压倒知识,但会与此同时导致理智的失败,即能动者无法把握实践三段论的“小前提”意义上的失败。他或她有一般性的伦理知识并使用它,但或者缺乏或无法使用具体的有关这一特殊案例本性的感知。那么,他如何面对他自己的批评呢?
在不过分纠缠于围绕这一棘手文本的演绎性问题的情况下,我想建议,如果我们采取我刚才勾勒的感知的包容性观点,根据这个观念,感知具有情感的、想象的,还有知性的成分,那么这种经常遭到蔑视的立场就会有更大的意义。被快乐所左右的能动者并不必然去除了对他或她情况的事实知识,也就是说,能了解这是不忠的或饮食过量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她自始至终是知道的。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同一背景中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当她在受到质疑时可能会做出所有正确的回答,并提供事实上正确的描述。他补充道,她甚至可以正确地展开目标—手段的慎思,并与她的不自制行为并行,如果她在某种意义上没有通过知性把握其特性,那么她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而,她却躲躲闪闪。她不完全面对或承认这种情况,让自己清晰地看到它对自己和他人生活的可能影响,并做出适合这种视觉的回应。对短期快乐的兴趣使她把自己与这些回应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知识隔绝开来。所以她的理智把握并不等同于感知,也不等同于对小前提的真正把握和运用。尽管她所掌握的事实是对的,但她有着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在其中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而这非常不苏格拉底式。
然而,她却躲躲闪闪。她不完全面对或承认这种情况,让自己清晰地看到它对自己和他人生活的可能影响,并做出适合这种视觉的回应。对短期快乐的兴趣使她把自己与这些回应以及它们所形成的知识隔绝开来。所以她的理智把握并不等同于感知,也不等同于对小前提的真正把握和运用。尽管她所掌握的事实是对的,但她有着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在其中她不知道她在做什么,而这非常不苏格拉底式。
这种解读为 不自制 的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置于一种启发性的关系中,既与其自身的传统有关,也与我们的传统有关。我们的英美传统倾向于,像柏拉图一样,认为 不自制 关乎激情,其解决办法要么是对令人烦恼的激情做某些理性的修正,要么采取某些掌握和控制的技术。再一次跟柏拉图那样,我们倾向于(毫无疑问受我所提到的现代道德理论的影响)认为激情是危险的自私和自我放纵的项目,在任何范围内,它会膨胀并引导我们远离善。从苏格拉底的观点来看,是伦理知识通过改变复杂情感所基于的信念,阻止了 不自制 ;以成熟的柏拉图式的观点看,知识必须与压迫和“饥饿”相结合。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的根源都在灵魂的所谓非理性部分。
如果我是对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解释悄然地完全改变了这一图景,指出 不自制 经常是(尽管不总是)由理论过多与在情感回应上的不足所引起。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缺乏自制,违背他或她有关善的知识,而这个人经常在所有的理智方面都表现得正确,那么她缺乏的是心灵与具体伦理现实的冲突。我们可以这样说:知识需要得到回应才能在行动中发挥作用;我们也可以说,缺乏正确的回应,那就没有或没有完整的实践知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促使我们把真正的实践洞察力和理解力看作一个涉及整个灵魂的复杂问题。柏拉图式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亚里士多德式感知的对立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是无知,但在其他情况下,它也可能是否认或自欺欺人的合理化。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显然,对知性力量的依赖会阻碍或削弱这些回应,从而成为对真正的伦理感知的阻碍。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理论家会为自己的理智能力感到自豪,并对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技术充满信心;然而却被他们的理论承诺所引导,对作为正确感知组成部分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具体回应毫不在意。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克瑞翁着迷于他的理论努力,试图用公民的生产能力来定义所有人类的关切,他甚至没有察觉到在某种程度上他知道的事情,即海蒙是他的儿子。他说出这句话,但他并没有真正承认这种关系——直到失去亲人的痛苦向他揭示了这一点。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在使用精确的经验心理学方法对他的心灵进行系统研究后,得出他并不爱阿尔贝蒂娜的结论。这个错误结论(他很快在痛苦的回应中承认这个结论是错误的)的得出并不是由于理智,但某种程度上其原因就在于理智。因为他鼓励它“自行其是”而无须回应和情感相伴。亨利·詹姆斯的《神圣之泉》引人入胜地描述了世界在一个始终坚持这种分离的人的眼中是什么样子,他让理论理性决定他与所有具体现象的关系,拒绝与其他任何人类联系,但同时却为自己敏锐的感知而自豪。在我们阅读时,我们发现这样一个人不可能对他周围的人和事有
任何
知识。他那种残缺不全的感知绝对无法触及那个主题或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投入其中。所以亚里士多德式的立场并不是简单地告诉我们理论化需要通过直觉和情感回应来完成;他警告我们,理论的那些方式会妨碍我们的视野。理智不仅不是自足的,它还是一个危险的掌控者。由于它的过度扩张,知识会“像奴隶一样被拖来拖去”。

所有这一切,再一次对当代的选择理论有了明确的暗示。许多在学院和公共生活中被教授和实践的当代理性理论,与葛莱恩先生的目标和政策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尽一切努力培养计算理智,却绝不培养“幻想”和情感。他们不会让自己去关心会培养那些回应的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事实上,他们含蓄地否认它们与理性的关联。亚里士多德明确地告诉我们,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培养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和想象,并且会非常小心,不要过分依赖技术或纯理智理论,因为这些理论可能会扼杀或阻碍这些回应。他们将通过文学和历史作品来促进一种培养想象和情感的教育,教授适当的回应时机和程度。他们会认为 不 哭、 不 生气或 不 在需要的时候体验和展示激情是孩子气的和不成熟的。在寻找个人榜样和公共领袖时,跟他们的理智能力一样,我们应该希望他们具有敏感性和情感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