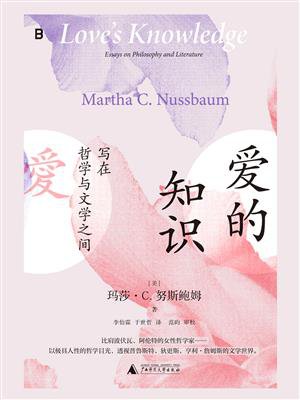Ⅳ.三种要素的集合
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感知和实践知识的三个不同部分。这些部分似乎构成了他对“实践理性是科学理解的一种形式”的观念攻击的一部分,而柏拉图为这一观点进行了明显的辩护。柏拉图的观念(至少在某些时期)坚持价值之间的同质性,认为实践知识是在一个(永恒的)高度普遍的系统中得到全面总结的;它还坚持理智是正确选择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柏拉图当然不是历史上唯一将这三个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概念看起来已经是统一的,因为它针对的是单一连贯立场的不同要素。但是,关于这种感知图景的内在连贯性,我们可以谈得更多。因为它的各种要素相互支持,而不仅仅是以一种争论的方式存在。
正如我们所说的,不可通约性不足以使特殊性优先于普遍性。但在单一性的强形式中的可通约性,对于一般性和普遍性优先于特殊性来说肯定是足够的:因为单一性度量必须是某种高度一般的普遍性,也就是说,一种在质量上出现的东西在许多不同的事情上都是一样的。即使是可度量性的有限的可通约性也足以拒绝实践特性中独特的不可重复属性。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不可通约性的总体精神,直接导向他对特殊事物优先性的论述的支持。因为他的不可通约论指出,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终极价值是多么丰富和多样。不要忽视每一个有价值的事物,珍惜它本身的特性,而不要把它化约为别的事物。这些禁令指向了一份长长的、开放式的清单——因为我们不想预先排除一些新事物出现的可能性,这些新事物本身的独特性质与我们以前认识到的那些事物有不可简化的区别。特别是在友谊和爱情的背景下,这些禁令几乎可以肯定地保证最终价值清单将包括一些不可重复的特殊事物:因为每个朋友都是为了他或她自身的缘故而被珍惜,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价值友谊的实例而存在。这似乎不仅包括性格,还包括共同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这样一来,虽然亚里士多德对特殊事物(它们与模糊性和可变性有关)的优先性有独立的论证,但前两个因素确实也互相支持。
情感和想象的解释进一步支持了这两个元素,并也得到了这两个元素的支持。我们已经说过,认识高度具体的、经常是特殊的对象是想象的本质。我们最强烈的激情所依附的对象也经常是这样的。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有两个因素使人们喜欢和关心某物,即认为它是他们自己的和认为它是他们唯一拥有的(1262b22—23);因此,我们最强烈的爱、恐惧和悲伤的感觉,很可能是针对那些在本质上其本身以及与我们的关系被视为不可化约的特殊的对象与人。论证情感和想象是实践知识和判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强烈地暗示:好的判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关注具体的,甚至是特殊性的,并被视为与其他事物不可通约。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第九节中,他确实明确地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的关系与一种伦理知识联系起来,而这种伦理知识在具体的特殊性上优于公共教育者那里的知识(1180b7—13)。另一方面,捍卫不可通约性就是要重新打开空间,在其中,情感和想象得以运作并发挥其力量。亚里士多德似乎可信地指出,柏拉图主义的伦理立场削弱了情感的力量(《政治学》1262b23—24);柏拉图本人也会承认,对可通约性和普遍性的信念至少会减除许多最常见的情感回应,因为他也承认,这些情感回应是基于对特殊性的感知。再一次,为特殊性的优先性辩护就是告诉我们,想象可以在慎思中扮演角色,而这种角色不能被抽象思想的功能完全取代。在不突出情感和想象角色的情况下,捍卫一种灵活的、以情境为导向的对于特殊性的感知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可能会试图描述一种纯粹的理智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足以抓住相关特征。在前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希腊对实践智慧的描述中,就有某些这样的先例,它捍卫了一种对理性在特定情境中的即兴使用,这种使用看起来很酷、狡猾并且自制。 [16] 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会觉得,这种理性不足以完成对目的进行慎思的敏感任务,尽管对于技术性的手段—目的推理来说可能没问题。在这里,他认同雅典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传统。我们已经提到过,修昔底德赞扬了地米斯托克利足智多谋的即兴发挥能力,而没有提及情感,但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却非常清楚地表明,充分的政治理性需要激情,这种判断需要通过爱和远见卓识来实现。希腊人要培养那种在想象中构想城邦的伟大和更大的希望的能力;当他们看到这种伟大时,就会“爱上”她(Ⅱ. 43.1)。他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并不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没有感受到这种爱的公民,在某种程度上无法意识到雅典和他自己在雅典的位置。
这个特征和另外两个特征之间的最后一个联系是:如果一个人跟柏拉图一样相信,强烈的情感是人类生活中无法忍受的紧张和压力的来源,那么他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培养一种观察和判断的方式,评估它们的局限并削弱其力量。正如柏拉图所说,可通约性和普遍性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式立场把情感依恋视为人类生活中丰富和善的内在价值来源,所以它缺乏柏拉图的一个最显著的动机,去推动前两个特征的转变。
这三个要素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幅有关实践选择的连贯图像。我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明显的紧张关系,而且关于为何一方的捍卫者也希望捍卫另一方的原因有很多。它们似乎阐明了一个想法的不同层面。借用亨利·詹姆斯的一句话说,我们可以将这个中心思想描述为“细微的体察与完全的承担”,做一个“无所错失”的人。
[17]
为了对她面前的价值世界负责,这种感知的能动者被指望去调查和审视每一个事物和每一种情况的性质,以充分的敏感和想象的活力对她面前的事物做出回应,不会因为逃避、科学的抽象,或者是对简化的热爱而无法看到和感觉到那些事物。亚里士多德式的能动者是我们可以信任的,他以充分的具体细节和情感差异来描述复杂的情况,不遗漏任何实践相关性。正如詹姆斯所写的:“在特定情况下,能够比其他人更多地感受到事物应有的价值,并在最大程度上戏剧性地、客观地记录它的人,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他是不会背叛、不会贬低,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不会放弃事物的价值和美的人。”
 但这意味着,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与艺术家和/或艺术的感知者惊人地接近,不是在这种观念将道德价值降低为审美价值,或将道德判断变成品位问题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被要求将道德视为一种高层次的远见和对特殊事物的回应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我们在最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我们的小说家身上寻求并重视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小说家的价值首先是其实践性,他从不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相脱离。好的行为首先需要正确的描绘,这种描绘本身就是道德上可进行评估的行为的一种形式。“‘说’事情要非常准确、负责以及永不停止。”小说家是一个道德能动者,而道德能动者,就其“好”的程度而言,也分享了小说家的才能。
但这意味着,具有实践智慧的人与艺术家和/或艺术的感知者惊人地接近,不是在这种观念将道德价值降低为审美价值,或将道德判断变成品位问题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被要求将道德视为一种高层次的远见和对特殊事物的回应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我们在最伟大的艺术家,尤其是我们的小说家身上寻求并重视的能力,对我们来说,小说家的价值首先是其实践性,他从不与我们如何生活的问题相脱离。好的行为首先需要正确的描绘,这种描绘本身就是道德上可进行评估的行为的一种形式。“‘说’事情要非常准确、负责以及永不停止。”小说家是一个道德能动者,而道德能动者,就其“好”的程度而言,也分享了小说家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