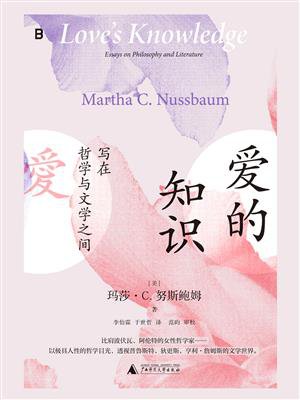V.思想的渴望,同情的旅程
那么,让我们通过一本小说来进一步检验这个概念。一般规则系统或一般决策程序的信徒现在可以继续列举这些规则或描述该程序。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转而寻找具有示范性、经验性的实践智慧模型的指导。亚里士多德式实践智慧致力于对异质性进行丰富的描述,对情境敏锐的感知,以及对情感和想象活动的投入——这已经向我们表明,某些类型的小说将是很好的例子,在其中可以看到这个概念恰当表达的好处。就像我已经说过的,我相信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小说:如果我们想要更多地了解亚里士多德式选择方式的内容,以及为什么它是好的,我们最好求助于其中的一本。没有比展示和评论恰当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式观点的散文更好的方式,来表明这种图景和多种决策理论中的选择图景之间的差异了。
把亚里士多德和詹姆斯并列在一起,并不是要否认他们对理性的概念在许多显著特征上是不同的。他们对意识、对情感的性质和分类有着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都应该牢记在心。然而,同情的趋同比这些差异更为显著,这种趋同也不是纯粹的偶然。有一点是,詹姆斯和亚里士多德之间有着无数的联系——从他自己的直接阅读到多种多样间接的哲学和文学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如果就像我所说的那样,这个概念真正回答了人类关于实践理性的深层直觉,这些直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以不完全相同的形式重现,那么,这两个关于实践理性有洞察力的作家会独立地达成共识,这就不足为奇了。关于做出好选择的问题具有显著的持久性,与在错误上的融合相比,在好的回应上的融合并不需要太多的解释。
将如此冗长而神秘的散文片段放在一篇文章的中心可能显得很独特。它是有意为之,读者应该反思这种差异,并追问那些在道德哲学的高谈阔论中失去的东西,道德哲学否认这种类型的资源。
下面这部分摘自亨利·詹姆斯《金钵记》的最后几页,可以看到玛吉·魏维尔的一部分思考:
“如何?”艾辛厄姆太太催着。
“呃,我倒希望……”
“希望他会见到她?”
然而,玛吉犹豫着,没有正面回答。“光希望是没用的,”她很快地说,“她不会的。但是他应该会。”前不久她朋友才为粗鲁行为表达了抱歉,这会儿刺耳的声音更加延长——像是按着电铃久久不放。现在竟然要被拿来讲一讲,夏洛特有可能“苛责”那个爱她那么久的男人,说得如此简单,其实真是很难过,不是吗?当然,所有的事情里,最怪的莫过于玛吉的顾虑,像想要做成什么,又有什么要应付的;更怪的是,有时候她这边几乎陷入一种状态,不甚清楚地盘算着她和丈夫一起,对这件事能打探出多少。这样是否会很恐怖,如果过去这几个星期里,她突然很警觉地对他说:“为了个人荣誉,你不觉得似乎真的应该在他们走之前,私底下为她做点儿什么吗?”玛吉能够掂掂自己精神上要冒多大的风险,能够让自己短暂神游去了,即使像现在还一面跟别人说着话——这个人可是她最信任的,出神期间她好去追踪后续的可能发展。说实在的,艾辛厄姆太太可以在这类时间里面,多多少少感到心理平衡些,因为不至于完全猜不到她在想什么。然而,她刚刚的想法不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而是一串,一个接一个地呈现。这些可能性的确也让她壮起了胆子,顾虑到艾辛厄姆太太可能还想要多少的补偿。可能性总是存在,毕竟她是够条件来苛责他——事实上,她已经不断、不断地这么做。没什么好拿来对抗的,除了范妮·艾辛厄姆站在那儿,一脸确定自己被剥夺了权利的样子——那是被残忍地加之于身的,或者说,是在这些人实际的关系里无助地感受到的;尤其回头一看已经不止三个月的时间,王妃心里当然觉得像是确实认定了。这些臆测当然有可能并无根据,因为阿梅里戈的时间好多好多,没有任何习惯癖好,他的解释里也没任何假话;因为波特兰道的那一对都知道,夏洛特不得已去伊顿广场,也不是一次、两次而已,那是没办法的事,因此她有不少人的东西正在搬走。她没去波特兰道——有两次不同日子,家里知道她人在伦敦一整天,却连来吃个午餐也没有。玛吉很讨厌,也不愿比较时间和样貌前后有何不同;或衡量一下这个念头,看看能否在这几天的某些时刻,临时见个面,因为季节的关系,窥伺的眼睛都被清空了,这种气氛下事情可能会非常顺利。但其实部分原因是,有个画面一直萦绕着她,那可怜女人摆出一副英勇的模样,尽管她手上已经握有秘密,发现了她心情并不平静,但心里几乎容不下任何其他影像。另一个影像可能是被掩盖的秘密,指出心情多多少少已经获致平息,有点儿被逼出来的意味,但也有受到珍惜;这两种隐藏的不同之处太大了,容不得一点错误。夏洛特没有隐藏骄傲或是欢欣——她隐藏的是羞辱;这种情况是,王妃根本没办法爆发报复的怒火,因为每当她在对抗自己硬得像玻璃的问题时,她的热情就势必会伤到它的痛处。
玻璃后方潜伏着 整个 关系的历史,她曾经几乎把鼻子压扁在上面,想看个究竟——此阶段,魏维尔太太很可能从里面疯狂地敲着,伴随着极度难以压抑的祈求。玛吉和继母最后在丰司的花园会面之后,心里沾沾自喜地想已经都做完、没事了,她可以把手交叠起来休息了。但是,就个人的自尊心而言,为什么没留点儿什么好再推上一把、好匍匐得更低些?——为什么没留点儿什么好令她毛遂自荐来传话,告诉他,他们的朋友很痛苦,并说服他,她的需要是什么?这么一来,她就可以把魏维尔太太敲着玻璃的事——那是我这么叫的——用五十种方式表达出来了;最有可能把它用提醒的方式说出来,刺到心灵深处。“你不知道曾经被爱又分手的滋味。你不曾分手过,因为在 你的 关系里,有哪一个值得说是分手呢?我们的关系真切无比,用知觉酿的酒斟得都要满出来;假如那是没有意义的,假如意义没有好过你这个私底下痛苦的时候,只能轻轻说出口的人,那么我为何要自己应付所有的欺瞒呢?为什么要受这种罪,发现闪着金光的火焰,才短短几年之后——啊,闪着金光的火焰!——不过是一把黑色的灰烬?”我们的小姐很同情,但是同情里的慧心注定也有机巧,偶尔她也只得臣服无法反抗;因为有时候才几分钟的时间,似乎又有一件新的职责加诸她身上——分离之前若有意见分歧,她就有责任要说话、祈求他们能在放逐之旅前,带走些有益处的东西,像那些准备要移民的人一样,拿着最后保留下来的 贵重物品 ,用旧丝绸包着的珠宝,以便哪天在悲惨的市集里讨价还价。
此位女子不由自主地想象着这个画面,这其实是一个陷阱,因为玛吉在路的每个弯道,都会被困住;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只要咔嗒一响,就紧抓住心思不放,接着就免不了一阵焦躁不安,羽翼乱扑,细致的羽毛四散。这些思想的渴望与同情的旅程,以及这些没将他们打倒的震荡,都即刻被感受到——这位非常突出的人物使得大家都动弹不得,前几周在丰司,他一直周而复始地在大家观望的未来、更远的那端,走过来又走过去。至于有谁知道、或谁不知道夏洛特有没有拿伊顿广场当幌子,把其他机会混进去,或混入到什么程度,都是那位个头小小的男士自己用他一贯令人无法预测的方式,在安静地仔细思量。这是他已经固不可移的一部分习惯,他的草帽和白色背心,他插在口袋的双手不知在变什么把戏,他透过稳稳地夹在鼻梁的眼镜,目光盯着看自己缓慢的步伐,那种不在乎外在世界的专注神情。此时画面上不曾消失片刻的一件东西,是闪着微光的那条丝质套索,无形地拴着他的妻子,玛吉在乡间最后的那一个月时间,感觉特别清晰。魏维尔太太挺直的颈项当然没有让它滑掉,长长绳索的另一端也没有——呵,够长了,颇为上手——把圈住大拇指较小的环解开,他手指头握得紧紧的,但她丈夫的身影则是不得见。尽管貌似微弱,但这条套索收拢的力道,不由得让人纳闷着,到底是什么样的魔法在拉扯,它经得住什么样的压力,但是绝不会怀疑它是否足以发挥效用或是它绝佳的耐用程度。事实上,王妃一想起这些情况,又是一阵目瞪口呆。她父亲知道这么多的事,而她甚至仍不知道!
此时艾辛厄姆太太和她在一起,所有的事情迅速地掠过她的心头,轻轻震颤着。虽然她仍未完全想通,但她已经表达了看法,认为阿梅里戈这边“应该”有条件地要做点儿什么,然后感觉她同伴用瞪眼的方式回答她。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意思。“他应该希望见她一面——我是说要有点儿保障又单独的情况下,跟他以前一样——以免她自己来安排。那件事,”玛吉因为胸有定见而勇敢地说,“他应该要准备就绪,他应该要很高兴,他应该要觉得自己一定——如此终结这么一段过去,实在微不足道!——得听她说说。仿佛他希望得以脱身,没有任何后果。”

当我们读到这几页的时候,首先注意到的是,与我们对形式决策理论的例子,甚至与一个发展良好的非技术性的哲学家的案例相比,在这里我们处于茫然无措之中。如果我们对整部小说没有一定的了解,就很难搞清楚这里到底在考虑什么、决定什么,更不用说每个因素的意义和权重了。因此,也很难确定玛吉在这里的想法和回应是理性的、值得称赞的,还是相反的。要做出这个决定,我们需要对她的整个故事有很多了解;在对整部小说进行最全面的审视之前做出任何判断似乎是仓促和武断的。(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通过强调它是由许多可能的观点中的几个组成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相关现实的整体比文本更复杂,许多潜在的相关洞见正被否认。)正是这些事实使这个篇章成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个很好案例。好的选择所具有的丰富情境,以及它对所有情境中特殊性的关注,都暗示着我们不应该期望能够如此接近一个复杂故事的目的,并理解或评估每一个事物。作为一名好医生,他既不会提前对病人的病史进行全面审视,也不会在不掌握医生做出选择时所用的所有背景材料的情况下去评估同事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指望玛吉的理由会得到我们的理解和评估,除非我们沉浸在她的故事中。这个例子确实不可被概述,这是它的优点,也是玛吉的优点。如果她在文章最后所做的与她的选择相关的一切
是
能在这几段中为我们充分总结出来的,那么她的选择几乎肯定是非理性的和糟糕的。如果一个现实中人在缺乏任何情境的情况下做出选择,我们就会对他持高度的怀疑,他的选择就像哲学的案例经常表明的那样。这意味着我们真的应该引用整部小说作为我们的例子。这也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最有帮助的典范将是那些他们的故事具有足够细节的人,他们对特殊性的慎思的意义和丰富性是可以被理解的——也就是朋友们以及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只要我们允许这些人物成为我们的朋友。之所以自由地使用这个例子,只是因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与小说的关系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友谊关系,这种关系就像慎思本身一样,既具有理智,又具有情感。

一旦我们注意到我们在没有更完整上下文的情况下迷失了方向,我们也会发现,这个例子的风格听起来根本不属于哲学。把它与决策理论著作中的文本实例相比,未免太滑稽了。但是,即使是一个典型哲学家的不那么科学化的散文,把它放在这篇复杂而神秘的构思旁边,它本身也显得简单,后者模糊性十足,且拐弯抹角、迂回和间接,用隐喻和图像而不是用逻辑公式或普遍性命题来传达它的核心含义。我相信,这些亚里士多德式观点,表达了“思想的渴望与同情的旅程”,这是拥有实践智慧之人会做的。这段散文表达了能动者的承诺,即面对所有的复杂情况,在所有的不确定性和特殊性中,将慎思行为视作整体的人格的冒险。它以抑扬的节奏描绘了一种道德上的努力,即努力正确地观察事物,并诉诸恰当的图景或描述;它的张力、拐弯抹角和来回兜圈子,都表现出要找到对眼前事物的正确描述或描绘是多么的困难。正如詹姆斯所说,如果“放置”就是“做”,那么展示这些就是展示一种有价值的道德活动。
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种慎思的内容时,我们注意到亚里士多德式慎思的每一个主要特征都出现了,并且以某种方式使我们相信,
这
是理性所要求的,而不是更简单或更简洁的东西。不可通约性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在小说的早些段落,玛吉根据一种单一数量的尺度将她的所有主张设想为同质性的。对于伦理价值而言,财务意象尤为突出地表现了这一还原策略。即使当她不使用这一意象时,她也在以多种方式不断表现出不承认相互冲突的义务的决心,不会在“理想的一致性”上有所动摇,“她的道德慰藉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依赖于这种理想的一致性”。这让她反复地,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重新诠释她所关切的价值观,以确保它们彼此和谐,是“圆融的”而不是棱角分明的。只有当某种主张在一定程度与其他固有主张相一致的情况下,该主张才会被承认;但这让玛吉对每一种不同主张的独特本质都有相当大的忽视。因为每一种特性都是粗边的有棱角的事物,很难被纳入一个预先存在的结构。她的建筑意象,就像可通约性的财务意象一样,表达了对独特本性的否定。道德生活的结构被比作坚实、简单、线条清晰的建筑,纯白色的古典房屋和伊顿广场修剪整齐的花园,而不是波特兰广场那种模糊的灰色和复杂的形状。

在这个场景中,就像在小说第二部分的大部分情节中一样,玛吉展现了她所获得的认识,尤其是可通约性,一般而言的一致和谐,并非一个成年女性理性慎思的好目标。她允许自己充分探索每一个相关主张的独特性质,进入它,想知道它是什么,试图在感情和思想上公正地对待它。“她刚刚的想法不只是一个方面而已——而是一连串,一个接一个地呈现。”首先,她考虑了丈夫和夏洛特的情况,问自己他们目前的关系最可能是什么样的。然后,她从对这种可能性的考虑转而更深入地审视夏洛特的性格以及他们爱情的特质,试图理解这一点及其对她的选择所具有的意味,让自己生动地描绘和想象她的朋友遭受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这让她认识到她自己的计划在道德上的困难,它是造成这种痛苦的原因。随后,当她几乎被怜悯所淹没时,她的“思想的渴望与同情的旅程”突然停止,就像被碰撞了一下,她父亲同样生动的形象出现在她面前,是一个“如此鲜明的人物”,迫使她考虑他的主张。她曾经把父亲看作所有道德要求的源泉,是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冲突的权威。现在她看到的他是“对比和对立的,简而言之,是被客观地呈现的”。也就是说,她看到的是
他
,透过其自身独特的本性,只是因为她现在以关注特殊性的方式看到他的需求和愿望与其他主张之间形成了紧张。她对他的独特性和质性上的个体性有着鲜明的感受,因为他的利益抗拒她对夏洛特的同情所形成的“震荡”。她把他视为夏洛特被囚禁和遭受痛苦的原因,因此她认为,任何想要公正地满足他的需要的努力,最终都会使她受到伤害和感到痛苦;另一方面,怜悯和诚实的计划,必然会威胁到他的控制能力和尊严。
 当我们遵循这一切,我们感到这种对分离的和异质的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察方式,并不比她过去坚持可通约性或坚持较弱的相关原则更
不
理性。这是一种道德成长的方式,一种像一个成熟的女性而不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那样的推理方式。
当我们遵循这一切,我们感到这种对分离的和异质的事物的独特性的观察方式,并不比她过去坚持可通约性或坚持较弱的相关原则更
不
理性。这是一种道德成长的方式,一种像一个成熟的女性而不是一个胆怯的孩子那样的推理方式。
这个案例也通过对特殊性优先于一般性的坚持为理解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空间。这并不是说到头来玛吉放弃了她所有的指导原则,转而诉诸某些对这个不可化约的特殊性的盲目的直觉。她的大量慎思都是基于历史的,询问过去所做的承诺和所做的行动对当前形势有何影响。它被视为与过去完全连续并受其影响。此外,如果我们不使用一般性的术语,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中许多承诺对她的影响。她表达了诸如信守承诺、对给予帮助和鼓励的朋友的感激之情、孩子对父母的责任等一般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关注。如果我们使用专有名词来描述她的思想所涉及的细节,避免使用诸如“父亲”“丈夫”和“朋友”之类的一般性术语,我们将无法正确地捕捉到它们对她的意义。她并没有简单地将亚当视为一个根本上与众不同的事物,提出其自成一格(sui generis)的主张。甚至在她反思非常
具体
的地方——例如,当她想到自己对一位与之有着特定具体历史的朋友有所亏欠时——她的大部分想法都是可以被普遍化的,并带有这样的含义:如果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出现完全相似的情况,同样的选择将再次是正确的。所有这些都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相一致,亚里士多德主义非常强调好的习惯,并致力于对美德的一般性定义。

此外,在她愿意承认责任和承诺的冲突中,玛吉比一个简单地否认可能存在真正的责任冲突的能动者,或者从一个角度看待冲突的能动者更忠实于她先前的一般原则。因为这个世界产生了一场关于“应该”的悲剧性冲突,这一事实不会使她做出判断,这些相互冲突的原则的其中之一不再约束她,或者也不会改写冲突的性质,使它不再呈现同样的悲剧面相。亚里士多德式的慎思远不是缺乏根据的和极其特殊的,在这一点上,它比许多其他被提出的慎思类型更忠实于它的过去。

但与此同时,有几种方法可以使玛吉境况的具体特殊性优先于一般性准则。首先,她准备承认不可重复和独特的事物与可普遍化的事物具有道德相关性。“父亲”一词并没有详尽地描述她与亚当在道德上的显著特征,出现在她面前的“如此显著不同的人物”也不是抽象的父母。一般和普遍性的描述必须通过注意他的个人品质和他们独特的个人历史来完成——正如她对“最好的朋友”关系的关心必须通过对夏洛特的个体的思考和感受来完成。其中一些将是具有普遍性的,尽管一点也不具有一般性。其中一些则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如果我们重写这篇文章,只留下可重复的特征,而忽略生动具体的图景和不可重复的记忆,我们就会失去很多道德的丰富性,慎思也会显得出奇地非理性。
然后,玛吉也看到,正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应该看到的那样,场景中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交织,是如何遮蔽它们的道德意义的。她不能简单地考虑一般意义上她对朋友夏洛特的职责是什么。她必须考虑到夏洛特所处的具体情况,即她专注于的令人痛苦的细节。为了判断该敦促什么,甚至为了说出她每一个可能相互冲突的义务所需要的东西,她必须想象夏洛特目前的处境,她可能会有什么感觉和欲望。如果仁爱的行动自身不能恰到好处地适合那种默默的痛苦和那种隐藏的耻辱的具体要求,那么它并不会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就像航行中的一个行动,根据航海手册来说是正确的,但却不考虑到领航员的具体情况而加以选择一样。再多说一些,这并不是简单地说,正确的行动必须“调节”到符合它的情境。我们还可以看到,如果不参考情境的特征,就没有办法描述所选择的行动本身,这些特征太过具体,无法在有效的行动指导原则中体现出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可能完全具有普遍性。玛吉的选择不是以维护家庭尊严为结果而敦促最后的对抗,而是为了以特定的方式来处理夏洛特在此境况下的特定痛苦,以保护一位非常特殊的父亲的尊严。行动(或非行动)的调性本身是特殊的、缠绕的,缺乏了小说家笔下的那些细节,它几乎就很难被很好地描述(如果我们想把握它的 正确性 )。
最后,在某种意义上,特殊性在玛吉坚持允许发现和惊奇,甚至可能导致她整个伦理观念发生严重逆转的惊奇的意义上获得了优先性。小说的前半部分表现出她在对待他人的过程中,就仿佛把他们当作雕塑或绘画,那些情境似乎都是对自己收藏的这些物品的沉思片段。这些物品不行动或移动,他们缺乏以不可预测和令人震惊的方式行事的力量,整个道德场景都有一种冷静沉思控制的气氛。后半部分以戏剧性的即兴发挥的形象展示了她的想法。她已经成为一名演员,突然发现她的剧本没有提前写好,她必须“非常英勇地”即兴表演她的角色。“准备和练习只走了很短的路。她的角色越演越好,她时时刻刻都在想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将在下一节详细讨论这个具有启发性的隐喻,但很明显,这表明了一种对此时此刻的敏锐的责任感,以及一种对可能包含的这种惊奇的开放性。
玛吉的慎思很清楚地向我们显示,想象和情感回应在感知中所扮演的指导角色,它们是道德知识的组成部分。如果她仅仅以理智的方式来看待夏洛特、亚美利哥和亚当的处境,她是否能看到她应该看到的全貌,这很值得怀疑。夏洛特敲打玻璃的形象,亚当牵着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缰绳套住的夏洛特的形象,都有能力传达给玛吉并表达出夏洛特困境的准确伦理意义;我们觉得,这种能力在与夏洛特的任何对抗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它避免了对形象的使用。我们也看到,这种想象功能与情感的工作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玛吉的画面充满了感情。事实上,我们有时会看到这幅画面是由一种情感所暗示或引起的。她的想法被一次 震荡 打断了,之后又在她父亲走路的图景中得到了表达。这种对亚当的情感震惊,或者说对他所涌起的关切,是她对他所采取的描述方式的来源。情感似乎是这幅画面 中 不可废弃的元素。她把亚当想象成一个受人爱戴的父亲,她的想象本身就是可爱的。(我们也可以说,使用想象是她生动而敏感的情感生活的一个特点。如果不提到她如何看待自己所爱和所焦虑的对象,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描述她的情感。)所有这些融合在一起的、高度复杂的材料,似乎对引导她正确理解对她的每一项要求做出正确伦理感知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她不允许自己通过那样的细节来看亚当,被那幅震荡的图像“突然中断”,她就不会明白在那种情况下她欠他什么。情感可能会过度与具有误导性,从她对夏洛特的同情几乎使她对整个情况的全面努力化为乌有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修正随之到来,当它到来时,它不是以冷静的理智判断的形式,而是以笼中之鸟这样自我批判而又饱含感情的画面形式到来,然后为亚当这个复杂的形象留出了空间,深受爱戴的和令人害怕的,他手指间的缰绳徘徊在她的脑海中。
再一次,我想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想象力的旅程和对同情的渴望,并不是仅仅作为一种在原则上不同于它们的理智知识(虽然也许实际上不是)的手段。我们在这里看不到这样的认知。专注于具体的意图,一个她的全部人格都积极地投入其中的行动,本身看起来就像一个目的。假设我们重写了这一场景,在亚当的画面之后又加上了几个类似的句子:“从这一点上,她推断她对她父亲的责任是……”我们会确信这进一步的阶段代表了道德认识的真正进步吗?这对她感知的“快速振动”有帮助吗?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认为:并没有——除非,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它以一种形式僵化或保留了感知的工作,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或在没有时间来充分感知时作为一种替代。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会坚持认为理智结论很可能是一种倒退,或者导致不能再充分知晓或了解情况,就像我刚才指出的:那样是站得住脚的,但也是危险的,因为僵化的部分认知很容易成为一种否定形式,除非它被不断地唤醒进入感知。
最后,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告诉我们,实践智慧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卓越表现,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而不是产生美德行为的倾向。我们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这里所引用的思考前后,玛吉说话和行动的方式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她不会改变想法,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言行。詹姆斯用“但是她坚持她的意思”这句话使我们注意到这一点,并赋予她前后几乎相同的词语。但他也坚持认为,在这些思想被记录下来之前,“她思想的革命是未完成的”。如果这种慎思具有道德价值,那么它似乎并不体现在它明显的行动的生产力上。但是我们相信它确实具有一种道德价值。
 即使决定本身没有改变,通过她如实地面对所有这些因素,某些颇有意义的东西还是得以增加。感知的无声的内在工作,在这里被展示出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卓越性的一个值得称赞的案例。这意味着它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的好生活的组成部分。
即使决定本身没有改变,通过她如实地面对所有这些因素,某些颇有意义的东西还是得以增加。感知的无声的内在工作,在这里被展示出来,它本身就是人类卓越性的一个值得称赞的案例。这意味着它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的好生活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