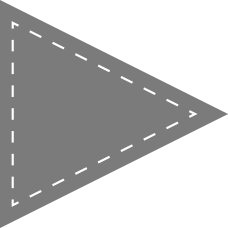 第一节
第一节
“网络总统”奥巴马及美国的网络外交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网络科技高度发达,也是当今世界网络政治走在前面的国家。互联网促推奥巴马入主白宫,而奥巴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网络政治的深入发展。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高调鼓吹“互联网自由”,大打“网络外交”牌,对国际政治、经贸、外交、军事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奥巴马推动美国网络政治深入发展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其成功竞选堪称网络政治营销中的一件杰作。奥巴马阵营对互联网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推动了美国网络政治的深入发展。
探析美国的网络政治,不能不先谈一谈奥巴马。事实表明,奥巴马堪称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其对推动美国网络政治深入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借助媒介工具进行政治营销,历来是美国政治家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在竞选活动中,新闻媒体通常成为候选人传播政见、争取选民的重要工具。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第一位“报刊总统”,其“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的名言影响深远。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美国第一位“广播总统”,其以广播形式进行“炉边谈话”,宣传施政纲领和政府政策,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电视总统”,其首次采用电视直播方式阐述政见、发布新闻,英俊潇洒、干练自信的形象赢得了诸多选民的欢心。而奥巴马,则是成功地借助互联网赢得了举世瞩目、意义深远的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谱写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新篇章。
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堪称网络政治营销中的一件杰作。许多人认为,网络科技的发达,促成了奥巴马的成功;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今天的奥巴马。其实,早在奥巴马参加竞选前的2006年,Google公司CEO埃里克就曾预言:“能够发挥互联网全部潜力的候选人,将会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纽约时报》也有评论称:“2008年,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懂网络。”
 不难看到,在竞选和执政期间,奥巴马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沟通的积极作用,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营销的能力可谓娴熟而高超。
不难看到,在竞选和执政期间,奥巴马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沟通的积极作用,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营销的能力可谓娴熟而高超。
竞选之初,奥巴马就招揽了一批知名的网络营销专家,组建一个强大的网络筹款团队,其中包括克里斯·休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SNS网站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卫斯礼(全球著名网上购物网站eBay的创始人之一)等。首先,奥巴马在筹措竞选款项方面别出心裁,他拒绝接受大面额的公共资金,而是通过互联网、以网络小额支付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草根性筹款网络,大量吸收公众50美元、25美元的小额捐款,奇迹般地募集了超过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据媒体报道称,奥巴马筹措的竞选款项超过85%来自互联网,来自总计310万名捐款人,65%都是小额捐助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实际上,这种筹款方式更容易培育支持者的忠诚度。
其次,奥巴马高度重视利用互联网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善于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其竞选团队为他建立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官方网站,全方位地介绍候选人及团队的相关情况,通过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手段,宣传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及其对重要议题的立场和主张,还在最热门、最具人气的社交网站(如MySpace、Facebook、Flickr等)树立直接代表奥巴马的虚拟主体,让选民以自己最便捷的方式连接到“奥巴马”,在自己最熟悉的网络社区与奥巴马的其他支持者建立联系。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曾持续通过微博网站Twitter上的Barack Obama账号发布信息,展开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这些举措,让“无处不在的奥巴马”理念成为现实,使奥巴马赢得了大量年轻选民追星式的崇拜和力挺。有调查资料显示,在30岁以下的选民中,奥巴马赢得了三分之二的支持率,而攻击其“缺乏经验”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只赢得32%的支持率。
完全可以说,奥巴马及其团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互联网的高度重视和高超的驭网能力。在发布竞选信息、刊登政治广告、开展民意调查、组织互动交流等各个方面,互联网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的崛起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互联网和“草根”阶层的力量,其对未来竞选活动乃至整个政治运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著名网站“在线政治”(Politics On-line)的主编菲尔诺贝尔曾感慨地说:“网络已经成为如今总统竞选的基础。”

就任总统之后,奥巴马仍然把网络平台作为手中的一个重要法器,原来他在Twitter网站的账号仍旧使用,且经常保持与Facebook、MySpace上的“粉丝”进行互动,不时发布总统行踪、未来打算等方面的信息,以和蔼可亲的形象和平易近人的方式消褪了总统生活的神秘感,进一步赢得追随者们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频频现身于YouTube等网络视频,立体化地展现其强大的亲和力和全方位拉近与民众距离的政治姿态。执政期间,奥巴马除了理所当然地将白宫官网(whitehouse.gov)作为美国政府提供政务资讯、发表时事评论的官方平台外,他还始终保持更新自己的个人博客,特别是在一些时政热点问题的讨论上,其博文跟进频率仍然较高。比如,在2010年备受关注的医疗改革问题上,奥巴马就用了10页、近20天的博文来宣传新政府的医改理念和相关举措,呼吁民众为通过医疗改革法案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如此,奥巴马在利用网络开展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促进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民间力量的沟通互动方面也相当活跃。上任后,他致力于利用社交网站推广美国的公共外交,曾多次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介机构代表、记者、博主和网络专家与美国政府领导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主动介绍美国情况,旨在加深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了解和认同。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美国驻华使馆专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邀请网友举行座谈会,解释奥巴马访华的目的,探测这些网友的关注重点,同时,还通过各种社交网站搜集意见,包括在腾讯网开设中文博客,呼吁中国网民提交自己最想询问奥巴马的问题。在奥巴马及其团队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方式。
、促进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民间力量的沟通互动方面也相当活跃。上任后,他致力于利用社交网站推广美国的公共外交,曾多次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介机构代表、记者、博主和网络专家与美国政府领导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主动介绍美国情况,旨在加深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了解和认同。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美国驻华使馆专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邀请网友举行座谈会,解释奥巴马访华的目的,探测这些网友的关注重点,同时,还通过各种社交网站搜集意见,包括在腾讯网开设中文博客,呼吁中国网民提交自己最想询问奥巴马的问题。在奥巴马及其团队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方式。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职业政治家,奥巴马的用“网”行为始终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无论是在竞选过程还是在执政期间,无论是在本国借“网”执政还是对外开展网络外交,奥巴马一直把网络媒体作为宣传政治主张、传播施政理念、开展政治互动、构建良好形象、争取公众支持的重要工具。当然,奥巴马的高明在于他本人及其团队善于运用网络平台,娴熟地操纵网络政治。他们巧妙设置的政治议程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色彩,让公众在生活化气息浓厚的博文、微博、音视频节目中被潜移默化,这无疑对网络政治运作带来了诸多启示。换个角度看,奥巴马阵营对互联网的重视和运用,客观上也有利于其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提高政务透明度,推进信息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网络政治深入发展。
二、希拉里强势鼓吹“互联网自由”
◎希拉里强势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国利益划线、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的说辞,其根本目标是要强化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为其借助网络传播实现自身战略意图扫除障碍。
2010年1月2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高调鼓吹要保障信息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而不受国家主权的约束,多次点名批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网络监管,指责中国、朝鲜等国家限制互联网自由。时至一年后的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再次在华盛顿大学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重申“互联网自由”,并公然宣称将斥巨资研发“破网”、“翻墙”技术,帮助他国民众摆脱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锁。
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两次讲演,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其实,两次事出有因、背景复杂的演讲莫不散发着浓郁的政治气息,具有明晰的政治意图。
希拉里第一次发表演讲时,正是“谷歌公司声称退出中国”事件最受世人关注的时候。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司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鲁蒙德(David Drummond)通过博客发布“不再应中国要求过滤信息,并有可能撤离中国”的消息。希拉里当天即就此声称:“谷歌公司已就有关指称向我们简要地通报了情况。这些指称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关切和疑问。”之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尼克·夏皮罗(Nick Shapiro)、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Pelosi)以及多位议员纷纷“声援”谷歌公司,“赞赏”其敢于挑战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呼吁更多的网络公司效仿。1月21日,希拉里为彰显美国提倡的所谓“新闻自由”,特意选择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其中多次提及中国,批评中国政府对网络信息进行管制。1月22日,奥巴马总统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国方面对谷歌公司遭到所谓“黑客袭击”一事做出解释。美国高层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之举、如此强势地为谷歌公司撑腰、助威,这既说明美国政府与谷歌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更让世人强烈地感受到“互联网自由”背后的政治意蕴。
希拉里第二次发表演讲,是在埃及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之时。自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发生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连续发生多起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埃及国内局势一度陷入混乱之中。2月11日,穆巴拉克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事件中,网络媒体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尽管埃及自身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是导致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但美国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方面十分活跃,作用明显。参与集会、抗议和示威的民众普遍利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来传递信息、互相串联,促使沸腾的“民意风暴”愈刮愈烈。事后,不少人士认为此次政变不啻是一场“互联网的革命”。希拉里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四天发表大肆宣扬“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声称美国政府将“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进一步增设Twitter等网络传播渠道,促进其他国家的互联网自由。这种高调而露骨的演讲,令人忧思。
不难看到,希拉里强势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其实是一种以美国利益划线、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的说辞,其根本目标不在于推动全球网络传播良序的建构,而是要强化美国在网络空间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为其借助网络传播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传输和意识形态渗透、实现战略意图扫除障碍,让美国在全球网络信息空间可以横冲直闯而免受其他主权国家的“约束”。希拉里试图把自己装扮成网络世界里的“自由女神”,而隐藏在其“自由”面具背后的虚伪性却昭然若揭。希拉里在演讲中,悍然点名批评中国、古巴、伊朗、越南等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公开宣称将斥巨资“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突破网络压制”。显然,这种言论包藏的险恶用心不言而喻。近几年来,互联网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拓展自身利益的一柄利器,成为许多国家的异见势力借以散布谣言、扰乱政局、煽动非法集会、挑动“街头政治”的重要工具,这不能不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自由”保持警醒。
反观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人们可以清楚地洞悉希拉里鼓吹的“互联网自由”的欺骗性。对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网络监管,其动辄以“自由”为名,横加指责和干涉;而一旦遇到“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美国军事外交电文等事情,则完全置别人的“自由”于不顾,竭力进行打压。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是一种典型的霸权逻辑。希拉里发表第二次演讲后仅仅48小时,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与参议员科林斯、卡珀即联名提交了信息安全法案,其中规定:总统可以宣布“信息空间的紧急状态”,在此状态下,政府可以部分接管或禁止对部分站点的访问。这种含糊不清的“规定”,无疑是为自己实施网络霸权而有意准备的托词。希拉里的演讲遭到众多媒体的质疑和批评。越南《西贡解放报》曾发表题为《是网络自由还是网络统制》的评论文章称,希拉里的演讲充分暴露了美国欲将“互联网自由”拔高到人权层面,并借此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英国《卫报》评论说:“希拉里的演讲给互联网自由投下了虚伪的阴影。”美国《佛罗里达鳄鱼报》嘲讽道:“谴责他国之前,希拉里更应该先用镜子照照自己的国家。”还有人曾著文称:“美国频频利用自身优势向他国输出美式意识形态,倡导‘互联网自由’的美国政府很多时候却掩耳盗铃,拿着‘宽己严人’的双重标准,到处挥舞道德大棒作恶不断”,并对其扼杀他国“互联网自由”的霸道行径进行了披露——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工作被掌握着根服务器的美国终止,伊拉克被美国在虚拟世界里“抹去”。
2004年4月,由于在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ly”(利比亚顶级域名)瘫痪,利比亚在互联网上消失了三天。
2009年5月,根据美国政府的授意,微软公司切断了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的MSN即时通信服务端口。美国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担心这5个所谓的“敌对国家”会以某种方式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后局势产生动荡。美国政府下令“推特”网站推迟网络维护时间,帮助伊朗反对派传送信息,为伊朗局势煽风点火。
2010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将三家中东电视台列入黑名单,表示将“抵制所有助长反美情绪的中东地区电视台”。

对于“互联网自由”,中国政府看得相当透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1年4月10日发布的《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美国极力标榜和鼓吹互联网自由,而实际上,美国对互联网的限制相当严格。2010年6月2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通过对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将保护网络作为国家资产法案》。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关闭互联网,再次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的权力。这只是目前美国政府对互联网限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运营网站须经政府许可以及个人身份信息验证。美国一向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对外要求别国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自由”,并以此作为外交施压和谋求霸权的重要工具,对内则对互联网进行严格管制。BBC2011年2月16日刊文指出,美国政府在鼓动“封闭社会”的人民争取互联网自由并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新闻管制提出质疑的同时,却在本国设立法律封锁以缓解维基揭密网发起的挑战。美国政府在国内对电子信息的自由流动非常敏感,但在国外却设法对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运用外交手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文章也承认,“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依然充满问题和矛盾”。
三、美国的网络外交风头正劲
◎网络外交是美国政府在网络政治时代对外政策的一项新举措、新内容。美国大打“网络外交”牌,主要目的在于借助互联网推介其现行政策,传播其价值观念,提升其国际形象,拓展其战略利益。
希拉里连续发表“互联网自由”这种政治色彩极浓的演讲,无疑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绑上美国外交政策战车”
 。近年来,“互联网自由”这一概念已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网络外交”成为美国政府在网络政治时代对外政策的一项新举措,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乃至整个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近年来,“互联网自由”这一概念已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网络外交”成为美国政府在网络政治时代对外政策的一项新举措,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乃至整个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有观察人士指出,希拉里在发表第一次“互联网自由”演讲的前几天,曾对美国IT界高层人士称,美国21 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Google、Twitter和YouTube 等技术力量来推动外交工作。
 在第一次演讲中,希拉里公开宣称“美国已经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点”。在第二次演讲中,希拉里大肆呼吁维护“网络上的表达自由”,并声称“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同时,她还宣称,为了使美国“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美国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并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
在第一次演讲中,希拉里公开宣称“美国已经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点”。在第二次演讲中,希拉里大肆呼吁维护“网络上的表达自由”,并声称“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同时,她还宣称,为了使美国“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美国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并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的网络外交,是美国整个政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的传统外交发展至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拓展、新表现。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方式,网络外交显然是网络传播新技术与传统外交的结合物。从现实条件看,网络外交的提出及推行,一方面与公共外交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美国强大的网络科技优势有关。
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里恩(Edmund A. Gullion)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公共外交是以普通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政府领导干部为对象;在实施方式上,这种外交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接触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进而说服和影响外国公众,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误解,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实践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公共外交对于推进对外交流颇具积极意义。美国高层对此甚为关注。身为奥巴马政府高级技术顾问的亚历克·罗斯(Alec Ross)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不仅仅是政府与政府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的活动”(people-to-people-to-government)的外交模式,同时,他一直倡导积极利用先进通信方式从事外交活动。
 显然,互联网恰恰为推行这种公共外交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显然,互联网恰恰为推行这种公共外交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使之已成为公众与公众、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交流的便捷桥梁,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组织相互联系的有效平台。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和网络应用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等方面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强大优势。Web2.0、Web3.0时代的到来,促使世界各地网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更加便捷,更为活跃。特别是对于作为网络用户主体的年轻人来说,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参与社会活动,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习惯。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利用互联网加强对年轻一代的争夺,自然是其外交战略中的题中之义。2010年9月10日,希拉里在参加美国官方举办的“民主短片竞赛”活动颁奖仪式时曾说:“我们经常在国务院这里谈到有必要用21世纪的外交来解决21世纪的种种问题,而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

从本质上说,美国政府推行网络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借助国际互联网这一自身主导的全球性信息流通平台,利用网络传播的新技术新应用,对外推介美国的现行政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拓展美国的战略利益,增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外交工具,其既是美国对外传输政治、文化、商业等各种观念和资讯的绝佳渠道,又是美国借以干涉他国内政、实施政治压制的一个幌子。在中东、北非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担当了美国政府网络外交的急先锋,不仅为美国政府传播政见、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在煽动公众不满情绪、挑拨矛盾冲突、引导舆论走势等方面发挥了“鼓风机”的作用。《纽约时报》曾刊文称,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站已成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随着“白宫2.0”时代的到来,美国政府不断掀起网络外交的旋风,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网络外交活动,且在议题设置、过程控制等方面日臻娴熟老到。比如,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时,美国政府在实施网络外交方面即下了很大气力。首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奥巴马访华的前几天组织了一次中国博客吹风会,邀请了8名知名中国博主与9名美国使馆领导干部、白宫专员讨论奥巴马访华事宜和中美关系,北京的现场还视频连线上海、广州,使身在沪、穗两地的多位博主亦能参与讨论。在奥巴马抵达上海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开启通过CO.NX网站,征求中国网友向奥巴马的提问。网站首页写道:“如果你可以向奥巴马总统提一个问题,你会提什么问题?”在网页中,网友无须注册便可以访客身份参与,输入昵称便可参与讨论和网页设置的调查。同时,美国大使馆还在腾讯网开设了官方中文博客(usembassy.qzone.qq.com),呼吁中国网友提交自己最想询问奥巴马的问题。应当说,互联网在此次重要外交活动中的运用是相当成功、效果显著的。
实践表明,网络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基本使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具体实施上,网络外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利用网络传播手段进行针对性的政治营销,以期促进交流、扩大影响;二是经常性地利用网络渠道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和政治主张,旨在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三是借“网”说事,打着“互联网自由”旗号,在其他国家培植亲美力量、提供技术支持,不断扩张自身在国际互联网上的版图,或通过对目标国家“挑刺”、施压,以实现自身的外交目标。
当前,美国的网络外交风头正劲,其对美国的政治生活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网络元素。当然也不难看到,随着2013年“斯诺登事件”和“棱镜门”浮出水面,美国政府在网络外交中一直高腔高调、咄咄逼人的形象显然被泼了一瓢冷水,弄得颇为尴尬。受此影响,美国的网络外交活动或许会在世人的质疑、嘲讽、批评和抗议中稍见收敛,但为长远战略利益计,美国的网络外交绝对不会因此而止步。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这一“贼喊捉贼”、混淆视听的行径,即令人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