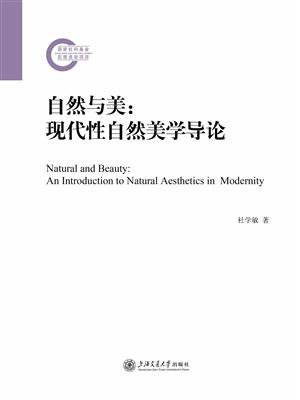一、卢梭启蒙思想中的“自然”概念
“自然”在卢梭整个生平活动与思想观念中占据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以至罗曼·罗兰说卢梭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罕见的师生或情人关系:“他的最大教师不是任何书本。他的老师是自然。他从童年时就热烈地爱上了她,而这种热情不表现在他的累赘的描写上面;自然浸染他的全身……她使他陷入狂喜状态,愈到晚年愈甚,这使他很奇怪地近似东方的神秘主义者。”
 卢梭的“自然”并未超出“自然界”与“本性”这两种自然概念的基本内涵,但被他大量使用的“自然”随着其不同运思方向的展开实际获得了多个层面的内涵与用法。正如他自己所言,“自然这个词的意义是太含糊了,在这里,应当尽量把它明确起来。”
卢梭的“自然”并未超出“自然界”与“本性”这两种自然概念的基本内涵,但被他大量使用的“自然”随着其不同运思方向的展开实际获得了多个层面的内涵与用法。正如他自己所言,“自然这个词的意义是太含糊了,在这里,应当尽量把它明确起来。”
 不过,卢梭其实并未对“自然”概念给出明确界定,其颇具特色的“自然”概念及其内涵与用法总体而论是功能性的,而非实质定义性的。
不过,卢梭其实并未对“自然”概念给出明确界定,其颇具特色的“自然”概念及其内涵与用法总体而论是功能性的,而非实质定义性的。
首先,作为人类文明对立面的“自然”概念,成为卢梭指控人类文明社会各种弊端与罪状,批判现代社会腐朽与堕落的立足点和参照系。
从1750年对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复兴能否敦风化俗?”独树一帜的否定性回答,即从《论科学与艺术》开始,卢梭将“自然”视为科学与艺术的对立面:“在艺术还没有塑成我们的风格,没有教会我们的感情使用一种造作的语言之前,我们的风尚是粗朴的,然而却是自然的……那时候,人性根本上虽然不见得更好;然而人们却很容易朴素深入了解,因此就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安全;而这种我们今天已不再可能感到其价值的好处,就使得他们能够很好地避免种种罪恶。今天更精微的研究和更细腻的趣味已经把取悦的艺术归结成了一套原则。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
 卢梭认为,在科学和艺术产生之前的原始时代,虽然各方面并非完美无缺,但社会风尚纯洁质朴,人们依其自然天性或德性而生活得自由、安全;而到了文明时代,日渐精微、细腻的科学研究与艺术趣味不断地败坏社会风尚,人们不再听从自我天性,表现真我,转而听从习俗和礼节的摆布,追求虚荣华贵,整个社会流行的是一种邪恶而虚伪之风。因而,科学、艺术同人的自然本性是完全对立的,或者说是对人自然本性的背叛,而这正是科学与艺术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伤风败俗的根本原因。
卢梭认为,在科学和艺术产生之前的原始时代,虽然各方面并非完美无缺,但社会风尚纯洁质朴,人们依其自然天性或德性而生活得自由、安全;而到了文明时代,日渐精微、细腻的科学研究与艺术趣味不断地败坏社会风尚,人们不再听从自我天性,表现真我,转而听从习俗和礼节的摆布,追求虚荣华贵,整个社会流行的是一种邪恶而虚伪之风。因而,科学、艺术同人的自然本性是完全对立的,或者说是对人自然本性的背叛,而这正是科学与艺术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伤风败俗的根本原因。
在其五年后的另一征文名作《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意义上揭示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他指出,在人与人之间大自然安排了平等,而人自己则制造了不平等,所以“人类的苦难都是自己造成的;大自然对我们并无过错”
 。在承认人类文明巨大成就和进步性的同时,卢梭更对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与麻烦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诚然,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巨大的成就:完成了许多深入的科学研究,发明了无数的技艺,找到了那么多可供我们使用的自然力量;山谷中的高山被削平,岩石被击碎;江河通航了,土地被开垦了,湖泊挖掘成功了,沼泽地被弄干了;地上建起了高楼大厦,海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船舶和水手;然而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稍稍思考一下这一切究竟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我们就不能不吃惊地发现这些事情的得失是多么的不平衡;不能不惊叹人类的盲目:为了满足妄自尊大的骄傲心和毫无根据的自我赞赏,竟如此热衷地去追求他必将遭遇的苦难;而这些苦难,造福人类的大自然是花了多少心血想使人类远远躲开啊。”
。在承认人类文明巨大成就和进步性的同时,卢梭更对给自己带来巨大痛苦与麻烦的人类文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诚然,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人类巨大的成就:完成了许多深入的科学研究,发明了无数的技艺,找到了那么多可供我们使用的自然力量;山谷中的高山被削平,岩石被击碎;江河通航了,土地被开垦了,湖泊挖掘成功了,沼泽地被弄干了;地上建起了高楼大厦,海上到处是来来往往的船舶和水手;然而另一方面,只要我们稍稍思考一下这一切究竟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多少真正的好处,我们就不能不吃惊地发现这些事情的得失是多么的不平衡;不能不惊叹人类的盲目:为了满足妄自尊大的骄傲心和毫无根据的自我赞赏,竟如此热衷地去追求他必将遭遇的苦难;而这些苦难,造福人类的大自然是花了多少心血想使人类远远躲开啊。”
 人类之所以能够超出于动物之上,能够同时利用和违背造福人类的大自然,是因为有动物所无的“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种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过错,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做出了许许多多“欺骗大自然”“侮辱大自然”
人类之所以能够超出于动物之上,能够同时利用和违背造福人类的大自然,是因为有动物所无的“自我完善的能力”,而“这种几乎是无可限量的特殊能力,反倒成了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过错,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做出了许许多多“欺骗大自然”“侮辱大自然”
 的丑恶之事。
的丑恶之事。
倡导“自然教育”的《爱弥儿》开篇伊始,卢梭对人类违背自然的各种罪责做出了鞭辟入里地分析与揭露:“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他要强使一种土地滋生另一种土地上的东西,强使一种树木结出另一种树木的果实;他将气候、风雨、季节搞得混乱不清;他残害他的狗、他的马和他的奴仆;他扰乱一切,毁伤一切东西的本来面目;他喜爱丑陋和奇形怪状的东西;他不愿意事物天然的那个样子,甚至对人也是如此,必须把人像练马场的马那样加以训练;必须把人像花园中的树木那样,照他喜爱的样子弄得歪歪扭扭。”
 “结束他的体系的”
“结束他的体系的”
 《爱弥儿》反复渲染的主题就是:自然和乡村使人幸福,文明和城市则使人堕落。改变此反常现象的具体方略就是:循序渐进地按照自然规律及儿童自然天性听任其身心自由发展,培养与现代文明人相对的“自然人”的“自然教育”。
《爱弥儿》反复渲染的主题就是:自然和乡村使人幸福,文明和城市则使人堕落。改变此反常现象的具体方略就是:循序渐进地按照自然规律及儿童自然天性听任其身心自由发展,培养与现代文明人相对的“自然人”的“自然教育”。
在晚年的《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中,卢梭借对话人之一的“法国人”之口继续强调,在自己所有著作中“到处看到对他的伟大原则的发挥、展开:他的原则就是:人天生是幸福而善良的,但是社会使他堕落使他变坏了”
 。所谓“天生”即“自然天性/本性”。可以说,无论是大自然意义上的自然概念,还是自然而然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均成为卢梭用以批判人类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依据。
。所谓“天生”即“自然天性/本性”。可以说,无论是大自然意义上的自然概念,还是自然而然意义上的自然概念,均成为卢梭用以批判人类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本依据。
其次,在卢梭看来,与人类社会相对的“自然”也是一位考验、启示、呼唤人类的良师益友和真诚伙伴。
卢梭认为,并非人人都适合从事科学与艺术活动,这从大自然似乎是有意设置的种种障碍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执迷不悟的所谓文明人,置人类导师大自然的忠告劝诫于不顾,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以致造成了种种祸端。不过,卢梭尽管否定科学与艺术可以敦风化俗的功能,但他并不否定科学与艺术活动本身所分别体现出来的人的理性精神与自然情感。卢梭其实并非完全否定科学(或艺术),更非否定科学本身,他只是对启蒙思想家们竭力进行的科学普及化持保留意见。因为科学一经普及就蜕化为意见,所以并不适合普通常人;科学只是那些“自然注定了要使之成为自然的学徒”的少数人如培根、笛卡儿、牛顿等这些人类的导师们的领地。

卢梭在后来的著作中反复重申大自然“这本书”对于人类的重大意义。他号召:人应该不是在人世间“谎话连篇的著述家的书中,而是在从不撒谎的大自然这本书中”阅读自己“真实的故事”,因为“凡是来自自然的东西,都是真的
 ;“若想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你只要善于阅读大自然这本书就行了”
;“若想成为世上最聪明的人,你只要善于阅读大自然这本书就行了”
 ;“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
;“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
 。在卢梭看来,相比于人类所写的书,大自然的书才是更值得人们永远信赖和学习的真理之书,是人类真正的知识之源,是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汲取真养料和营养之所。
。在卢梭看来,相比于人类所写的书,大自然的书才是更值得人们永远信赖和学习的真理之书,是人类真正的知识之源,是需要每个人认真去汲取真养料和营养之所。
在《爱弥儿》中,卢梭直接把“自然”称作“老师”,称作一本大书的“作者”,认为这位老师和作者应该是每一个孩子和每一个人崇奉的对象:“教育是随生命的开始而开始的,孩子在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学生,不过他不是老师的学生,而是大自然的学生罢了。”
 “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
“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
 卢梭还指出,自然就像一位真诚的伙伴一样向人类发出深切的呼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倾听“自然的呼声就是天真无邪的声音”
卢梭还指出,自然就像一位真诚的伙伴一样向人类发出深切的呼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倾听“自然的呼声就是天真无邪的声音”
 ,“圣洁的自然呼声,胜过了神的呼声,所以在世上才受到尊重,它好像把一切黑恶和罪人都驱逐到天上去了”
,“圣洁的自然呼声,胜过了神的呼声,所以在世上才受到尊重,它好像把一切黑恶和罪人都驱逐到天上去了”
 。因而,只要“我们服从自然,我们就能认识到它对我们是多么温和,只要我们听从了它的呼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做自己的行为的见证是多么愉快”
。因而,只要“我们服从自然,我们就能认识到它对我们是多么温和,只要我们听从了它的呼声,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做自己的行为的见证是多么愉快”
 。对于卢梭而言,人只有听从内外在自然的召唤,才能不致迷失本性,懂得自己职责,从而走在正确道路上。
。对于卢梭而言,人只有听从内外在自然的召唤,才能不致迷失本性,懂得自己职责,从而走在正确道路上。
最后,对于卢梭而言,“自然”也是和谐完满人性的理想状态、生活原则与终极依据。
此种意义上的“自然”观集中体现在卢梭的“自然状态”和“自然人性”及“自然情感”等概念上。卢梭的自然状态观是在批判继承霍布斯和洛克“自然状态”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卢梭认为纯粹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人虽然有年龄、健康、体力、智力等的不同,但这些并不具有道德的意义,不会因此造成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他们的生活尽管是粗野无知,但也平等自由、纯朴。自然人中没有一个人依赖他人的劳动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没有发生奴役的情况。对此,卢梭以生动的笔墨描述道:“野蛮人既然成天在森林中游荡,没有固定的工作,没有语言,居无定所,没有战争,彼此从不联系,既无害人之心,也不需要任何一个同类,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许从来都不互相认识,所以野蛮人是很少受欲念之累的;他单靠他自己就能生活,他只具有适合于这种状态的感情和知识;他只能感知他真正的需要,他只注意与他有关的事物;他的虚荣心不发达,他的智慧也不发达。即使他偶尔有所发明,他也无法传授给别人,因为他连他的孩子都不认识,所以根本无人可传。技术随着发明人死亡而消失。在自然状态中,既没有教育,也没有进步;子孙一代一代地繁衍,但没有什么进步的业绩可陈,每一代人都照例从原先那个起点从头开始;千百个世纪都像原始时代那样浑浑噩噩地过去;人类已经老了,但人依然还是个孩子。”因而,自然状态“对人类来说是最好的状态……人类本来就是为了永远处于这种状态而生的,这种状态是人类真正的青年时期”
 。卢梭的“自然状态”思想一经提出,在当时即遭受了很大的误解甚至辛辣讥讽(如伏尔泰),认为卢梭是要人退回到动物状态中去。但卢梭提出的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思想并非倡导“尚古主义”(primitivism)
。卢梭的“自然状态”思想一经提出,在当时即遭受了很大的误解甚至辛辣讥讽(如伏尔泰),认为卢梭是要人退回到动物状态中去。但卢梭提出的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思想并非倡导“尚古主义”(primitivism)
 和要开历史倒车,它与其说是描述了人类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不如说是表达了对桃花源般的人类理想状态的向往,并试图以此理想状态来省察现有文明的偏误和缺陷
(1)
。所以,“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只有在他似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痛苦才最为轻微,因为,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
和要开历史倒车,它与其说是描述了人类已经逝去的黄金时代,不如说是表达了对桃花源般的人类理想状态的向往,并试图以此理想状态来省察现有文明的偏误和缺陷
(1)
。所以,“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路程就没有那么遥远。只有在他似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痛苦才最为轻微,因为,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
 。有学者指出,卢梭的“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意义,他没有清晰地说明,并且常不能自圆其说。凡前人所曾用过的意义,他差不多都曾用到。不过,在他将这名词胡乱应用之时,他有一个观念却不容加以误会。这观念就是:人们的自然状态,优于人们有文化的或有社会的状态,因而后者应以前者为其准绳”
。有学者指出,卢梭的“自然状态究竟是什么意义,他没有清晰地说明,并且常不能自圆其说。凡前人所曾用过的意义,他差不多都曾用到。不过,在他将这名词胡乱应用之时,他有一个观念却不容加以误会。这观念就是:人们的自然状态,优于人们有文化的或有社会的状态,因而后者应以前者为其准绳”
 。换言之,即便卢梭本人对“自然”术语的使用是随意甚至矛盾和混乱的,却并不影响他使用此概念的价值性指向,即借此反思源于自然却经常反自然的所谓人类文化,并强调“自然”之于人类文化的优先性及其标准地位。
。换言之,即便卢梭本人对“自然”术语的使用是随意甚至矛盾和混乱的,却并不影响他使用此概念的价值性指向,即借此反思源于自然却经常反自然的所谓人类文化,并强调“自然”之于人类文化的优先性及其标准地位。
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还论述了与“自然状态”相联系的两种重要的“自然人性”。人的心灵活动被卢梭一分为二,一是理性的部分,一是前理性或超理性的部分。自然的人是用前理性或超理性的感情、本能来考察事物,采取行动的:“仔细思考人的心灵的最初的和最朴实的活动,我敢断定,我们就会发现两个先于理性的原动力:其中一个将极力推动我们关心我们的幸福和保存我们自身,另一个将使我们在看见有知觉的生物尤其是我们的同类死亡或遭受痛苦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
 卢梭将前/超理性的两个原动力分别称作自爱心和怜悯心,并强调自爱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
卢梭将前/超理性的两个原动力分别称作自爱心和怜悯心,并强调自爱心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
 ,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的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
,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的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
 。卢梭也把“自爱心”和“怜悯心”视为人的自然情感,认为正是它们的相互制约使人生活于和平友善的状态之中。
。卢梭也把“自爱心”和“怜悯心”视为人的自然情感,认为正是它们的相互制约使人生活于和平友善的状态之中。
卢梭还反复强调“自然”对于人类真善美三种元价值的本源性地位及其根本意义,“凡是来自自然的东西,都是真的;只有我添加的东西才是假的”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
 。对于卢梭来说,真善美的典型均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只有自然才是鉴别我们行为是否正当的永恒标准。所以,与往往视“自然”为“蒙昧”“动物本能”为同义语的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们不同
。对于卢梭来说,真善美的典型均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只有自然才是鉴别我们行为是否正当的永恒标准。所以,与往往视“自然”为“蒙昧”“动物本能”为同义语的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们不同
 ,卢梭主要是从塑造、建构完整而全面的理想人性立论的,他以自然状态、自然人性和自然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自然”概念具有鲜明的人文理想性,而且既被视为人性完满与和谐的终极依据,也成为用以批判现代社会腐朽与堕落的参照系。
,卢梭主要是从塑造、建构完整而全面的理想人性立论的,他以自然状态、自然人性和自然情感为主要内容的“自然”概念具有鲜明的人文理想性,而且既被视为人性完满与和谐的终极依据,也成为用以批判现代社会腐朽与堕落的参照系。
正是在用“自然”观念对抗科学与艺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用原始人的自然本性对抗现代文明的社会性,深刻揭露文明与社会进步之间尖锐矛盾的过程中,卢梭提出了其著名的“回归自然”思想:“我们对风尚加以思考时,就不能不高兴地追怀太古时代的纯朴的景象。那是一幅全然出于自然之手的美丽景色,我们不断地回顾它,并且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不感到遗憾。”
 卢梭对“自然”概念中的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双重性是有清醒认知的,故而他所要回归的“自然”,既指的是自由、平等的人性自然,也指的是给予人类最真实启示的自然界。卢梭的“回归自然”思想实际存在回归外界大自然与回到自然本性两种内涵。
卢梭对“自然”概念中的外部自然与内部自然的双重性是有清醒认知的,故而他所要回归的“自然”,既指的是自由、平等的人性自然,也指的是给予人类最真实启示的自然界。卢梭的“回归自然”思想实际存在回归外界大自然与回到自然本性两种内涵。
总体而论,卢梭在其整个思想中往往从多个层面上用到“自然”概念。自然有时是用以指称独立于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界的实体概念,有时则意指用以启迪人类当顺应自然及其规律的价值概念;有时意指外在自然,有时则意指内在自然;有时是他批判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把有力武器,有时又成为寄托其社会政治、文学艺术思想的一种理想状态。尽管卢梭明确地认识到并不存在完美的自然界
 ,其“自然”概念也具有不能予以简单归纳的复杂性甚至含混性,但理想的自然状态意义上的自然仍然构成了卢梭“自然”概念的核心内涵,它既是卢梭“回归自然”命题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理解卢梭自然美观念及其价值的前提。
,其“自然”概念也具有不能予以简单归纳的复杂性甚至含混性,但理想的自然状态意义上的自然仍然构成了卢梭“自然”概念的核心内涵,它既是卢梭“回归自然”命题产生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理解卢梭自然美观念及其价值的前提。
(1)
请看卢梭晚年的一个表述:“但是人的天性不会逆转,人一旦远离了洁白无瑕和平等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这是他最最强调的另一原则。所以,他的目标不可能是让人数众多的民众以及大国回到他们原始的单纯和纯洁上去,而是如果可能的话,制止一些人前进的步伐:这些人的渺小以及他们的处境防止了他们那么快地朝着社会的完美和人类的退化走去。这些独特的见解很有价值,却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人们坚持谴责他想毁灭科学,毁灭艺术,毁灭戏院,毁灭学术机构,并将宇宙重新投入最初始的野蛮与愚昧中去。”[法]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袁树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7-258页。
对此,康德也曾指出:“卢梭对敢于从自然状态中走出来的人类作了忧郁的(伤感的)描述,宣扬重新回到自然状态和转回森林里去。人们可不能完全把这种描述当作他的真实意见,他是以此来表述人类在不断接近人的规定性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卢梭从根本上说并不想使人类重新退回到自然状态中去,而只会是站在他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上去回顾过去。”[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上海人民2002年版,第254页、第255页。另参阅[德]卡西尔在其《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12页、第31页)和《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5页)中对康德上述观点的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