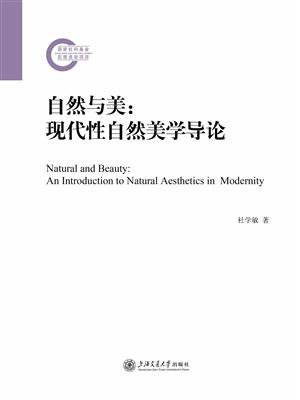二、回归自然:卢梭的自然美与自然审美论
由于卢梭没有关于美学问题的专门论著,其主要涉及美学问题的《新爱洛伊丝》《爱弥儿》《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和《漫步遐想录》等作品本身也未能提供一个独立的美学体系
 ,因而较之于人们对其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之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神学等诸领域的杰出贡献与影响的不断追溯与阐发,西方美学史家从美学方面对卢梭的研究与关注显得非常有限
,因而较之于人们对其在西方思想和文化史上之于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文学、神学等诸领域的杰出贡献与影响的不断追溯与阐发,西方美学史家从美学方面对卢梭的研究与关注显得非常有限
 。正像罗素指出的卢梭尽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却对哲学产生了很有力的影响
。正像罗素指出的卢梭尽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却对哲学产生了很有力的影响
 一样,卢梭虽然也不是专门的美学家,但他却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美学某些方面的气质。在其大量文学和非文学著作中,卢梭自觉不自觉地深入论及美的问题,其中就有本书特别关注自然美。卢梭的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自然美学观念具有鲜明而深刻的现实指向,足以使他能够从美学人才辈出的18世纪脱颖而出,成为在自然美学史中占据一章或至少一大截篇幅位置的美学家。
一样,卢梭虽然也不是专门的美学家,但他却很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美学某些方面的气质。在其大量文学和非文学著作中,卢梭自觉不自觉地深入论及美的问题,其中就有本书特别关注自然美。卢梭的启蒙思想体系中的自然美学观念具有鲜明而深刻的现实指向,足以使他能够从美学人才辈出的18世纪脱颖而出,成为在自然美学史中占据一章或至少一大截篇幅位置的美学家。
卢梭的心灵似乎生来就富于感受大自然的美。童年在一个名为包塞的乡村度过的两年时光,培养了他对宁静、纯朴的田园生活的感情。青年时代他在意大利都灵有过为期七八天的徒步旅行,阿尔卑斯群山美丽的风光更是激发了他丰富的想象力与对大自然及其美的喜爱、赞叹。这样,当卢梭日后成为作家时,就被公认为是法国文学中最早表达过对自然美的热爱和欣赏的作家
 ,《新爱洛伊丝》《爱弥尔》《忏悔录》《漫步遐想录》等文学作品中对湖泊(瑞士的日内瓦湖和比埃纳湖)、山谷(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和法国尚贝里城附近的厄歇勒山崖)与乡野(法国尚贝里城附近的沙尔麦特乡野和巴黎近郊的蒙莫朗西乡野)等自然风景或自然事物之美的生动而精彩的描绘是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
,《新爱洛伊丝》《爱弥尔》《忏悔录》《漫步遐想录》等文学作品中对湖泊(瑞士的日内瓦湖和比埃纳湖)、山谷(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和法国尚贝里城附近的厄歇勒山崖)与乡野(法国尚贝里城附近的沙尔麦特乡野和巴黎近郊的蒙莫朗西乡野)等自然风景或自然事物之美的生动而精彩的描绘是他在文学史上不朽的篇章
 。也正是在他自己或借助于他笔下的人物对自然美景进行具体描述的过程中他也零零星星地表明了他对于自然美和自然审美的洞见。
。也正是在他自己或借助于他笔下的人物对自然美景进行具体描述的过程中他也零零星星地表明了他对于自然美和自然审美的洞见。
“在所有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景象中,最美的是大自然的景象。”
 早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就设想理想的共和国除了政治上的诸多优点之外,还需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最美好的景致:“如蒙上帝眷顾,使这个国家能有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普天之下最美好的景致。”
早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卢梭就设想理想的共和国除了政治上的诸多优点之外,还需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最美好的景致:“如蒙上帝眷顾,使这个国家能有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普天之下最美好的景致。”
 后来,卢梭根据自己深切的自然审美体验这样写道:“一个平原,不管那儿多么美丽,在我看来绝不是美丽的地方。我所需要的是激流、巉岩、苍翠的松杉、幽暗的树林、高山、崎岖的山路以及在我两侧使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深谷。”
后来,卢梭根据自己深切的自然审美体验这样写道:“一个平原,不管那儿多么美丽,在我看来绝不是美丽的地方。我所需要的是激流、巉岩、苍翠的松杉、幽暗的树林、高山、崎岖的山路以及在我两侧使我感到胆战心惊的深谷。”
 卢梭似乎更赞同由中国谚语“无限风光在险峰”所强调的那种别样的自然美:“大自然似乎不愿意人们看见它真正的美,因为人们的眼睛对大自然的美太不敏感,即使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也会看错它本来的样子的。大自然躲开人常去的地方,它把它最动人的美陈列在山顶上,陈列在密林深处和荒岛上。”
卢梭似乎更赞同由中国谚语“无限风光在险峰”所强调的那种别样的自然美:“大自然似乎不愿意人们看见它真正的美,因为人们的眼睛对大自然的美太不敏感,即使摆在他们的眼前,他们也会看错它本来的样子的。大自然躲开人常去的地方,它把它最动人的美陈列在山顶上,陈列在密林深处和荒岛上。”
 他还写道:“我想聚精会神地沉思,但经常被一些突然出现的景物分散了我的心。有时候是高高悬挂在我头上的重重叠叠的岩石,有时候是在我周围喷吐漫天迷雾的咆哮的大瀑布,有时候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激流,它在我身边冲进一个深渊,水深莫测,我连看也不敢看……有时候在走出一个深谷时,看到一片美丽的草原,顿时感到心旷神怡。”
他还写道:“我想聚精会神地沉思,但经常被一些突然出现的景物分散了我的心。有时候是高高悬挂在我头上的重重叠叠的岩石,有时候是在我周围喷吐漫天迷雾的咆哮的大瀑布,有时候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激流,它在我身边冲进一个深渊,水深莫测,我连看也不敢看……有时候在走出一个深谷时,看到一片美丽的草原,顿时感到心旷神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描写山峦,描写湖水,还是描写乡野,卢梭笔下的大自然都具有一种粗犷雄浑的美,这是自然之美在卢梭的感受和描写中表现出的基本特色”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论是描写山峦,描写湖水,还是描写乡野,卢梭笔下的大自然都具有一种粗犷雄浑的美,这是自然之美在卢梭的感受和描写中表现出的基本特色”
 。换言之,卢梭所欣赏的自然美景有偏于荒凉、险峻、怪异、雄奇的特征,亦即他所欣赏的自然美有偏重于崇高而非优美的倾向。这显然对崇拜卢梭并对有别于优美的崇高和有别于艺术美的自然美做出过经典研究的康德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换言之,卢梭所欣赏的自然美景有偏于荒凉、险峻、怪异、雄奇的特征,亦即他所欣赏的自然美有偏重于崇高而非优美的倾向。这显然对崇拜卢梭并对有别于优美的崇高和有别于艺术美的自然美做出过经典研究的康德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但卢梭重视崇高的自然美,并不轻视优美的自然美。这从前引其文字不难发现。如:“你想象那些变化多样的风光,广阔的天地和千百处使人感到惊骇不已的景观,看到周围都是鲜艳的东西、奇异的鸟和奇奇怪怪叫不出名字的草木、处处另有一番天地,另有一个世界,心里真是快乐极了。眼中所看到的这一切,五色斑斓,远非言词所能形容;它们的美,在清新的空气中显得更加迷人……总之,山区的风光有一种难以名之的神奇和巧夺天工之美,使人心旷神怡,忘掉了一切,甚至忘掉了自己,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了。”
 从文中描写的景色和主人公圣普乐心旷神怡的情感反应看,这里涉及的自然美并不是崇高的,而是优美的。
从文中描写的景色和主人公圣普乐心旷神怡的情感反应看,这里涉及的自然美并不是崇高的,而是优美的。
卢梭特别强调人对自然美的直接接触与真切感受,并认为必须从儿童抓起:“自然的景色的生命,是存在于人的心中的,要理解它,就需要对它有所感受。孩子看到了各种景物,但是他不能看出联系那些景物的关系,他不能理解它们优美的和谐。要能感受所有这些感觉综合起来的印象,就需要有一种他迄今还没有取得的经验,就需要有一些他迄今还没有感受过的情感。如果他从来没有在干燥的原野上跑过,如果他的脚没有被灼热的沙砾烫过,如果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太阳照射的岩石所反射的闷人的热气,他怎能领略那美丽的早晨的清新空气呢?花儿的香、叶儿的美、露珠的湿润,在草地上软绵绵地行走,所有这些,怎能使他的感官感到畅快呢?如果他还没有经历过美妙的爱情和享乐,鸟儿的歌唱又怎能使他感到陶醉呢?如果他的想象力还不能给他描绘那一天的快乐,他又怎能带着欢乐的心情去观看那极其美丽的一天的诞生呢?最后,如果他不知道是谁的手给自然加上了这样的装饰,他又怎能欣赏自然的情景的美呢?”
 在卢梭看来,就儿童教育而论,整体优美的自然美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可以发挥其更重要的审美教育价值。事实上,对于卢梭,欣赏、追求大自然的美——不论是优美还是崇高的——均具有有益身心的双重功效:“高山上的空气清新,使人的呼吸更加畅快,身体轻松,头脑非常清醒,心情愉快而不激动,情欲也得到了克制。在这样的地方,心中思考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大问题,而且随着所见到的景物的大小而增减其重大的程度,感官也得到一种既不令人过于兴奋、也不令人产生肉欲的美的享受。看来,站在比人居住之地高的地方,就会抛弃所有一切卑下的尘世感情;当我们愈来愈接近苍穹时,人的心灵就会濡染苍穹的永恒的纯洁……我不相信人们在这样的地方长住,会产生骚动的情绪和无病呻吟的心情;人们没有把山区有益健康的清新的空气浴,当作医治疾病和整饬风尚的良药之一,这使我感到吃惊。”
在卢梭看来,就儿童教育而论,整体优美的自然美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可以发挥其更重要的审美教育价值。事实上,对于卢梭,欣赏、追求大自然的美——不论是优美还是崇高的——均具有有益身心的双重功效:“高山上的空气清新,使人的呼吸更加畅快,身体轻松,头脑非常清醒,心情愉快而不激动,情欲也得到了克制。在这样的地方,心中思考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大问题,而且随着所见到的景物的大小而增减其重大的程度,感官也得到一种既不令人过于兴奋、也不令人产生肉欲的美的享受。看来,站在比人居住之地高的地方,就会抛弃所有一切卑下的尘世感情;当我们愈来愈接近苍穹时,人的心灵就会濡染苍穹的永恒的纯洁……我不相信人们在这样的地方长住,会产生骚动的情绪和无病呻吟的心情;人们没有把山区有益健康的清新的空气浴,当作医治疾病和整饬风尚的良药之一,这使我感到吃惊。”
 亚里士多德就悲剧等艺术而提出的“净化说”在此被卢梭从自然美视角做出了更为确切的美学阐释
亚里士多德就悲剧等艺术而提出的“净化说”在此被卢梭从自然美视角做出了更为确切的美学阐释
 。
。
卢梭的自然美思想不仅涉及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更重要的是他明确涉及了自然本性之美的自然美与自然审美。卢梭写道:
在人做的东西中所表现的美完全是模仿的。一切真正的美的典型是存在在大自然中的。我们愈是违背这个老师的指导,我们所做的东西便愈不像样子。因此,我们要从我们所喜欢的事物中选择我们的模特儿;至于臆造的美之所以为美,完全是由人的兴之所至和凭借权威来断定的,因此,只不过是因为那些支配我们的人喜欢它,所以才说它是美。支配我们的人是艺术家、大人物和大富翁,而对他们进行支配的,则是他们的利益和虚荣。他们或者是为了炫耀财富,或者是为了从中牟利,竞相寻求消费金钱的新奇的手段。因此,奢侈的习气才得以风靡,从而使人们反而喜欢那些很难得到的和很昂贵的东西。所以,世人所谓的美,不仅不酷似自然,而且硬要做得同自然相反。

卢梭在此十分明确地立足于产生根源而区分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美,即自然而然的美与人工臆造的美,而且旗帜鲜明地厚前薄后。在卢梭看来,人工产品的美原本就是模仿大自然自然而然的美的,其范本与价值也当以大自然为标准,但现实中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人造产品的美常常不仅不酷似自然的美,反而完全背离自然的美,因为其趣味标准常常是由艺术家、权贵、富翁的随心所欲、贪心和虚荣心操纵的。
对此种非自然的人工造作之美,卢梭曾在《新爱洛伊丝》卷四中借主人公圣普乐的书信表达了强烈的厌恶感。面对沃尔玛夫妇的“爱丽舍”果园,圣普乐对它大加赞赏,因为他看到的果园虽经人工整治但仍像大自然的创造那样没有人为的痕迹,并且对上流社会所崇尚的反自然的园林趣味予以辛辣讽刺:“如果有一位巴黎或伦敦的富翁来做这座房屋的主人,而且还带来一位用重金请来破坏这里的自然美的建筑师,他走进这个简朴的地方,一定会看不起的!一定会叫人把所有这些不值钱的东西通通拔掉!他要把一切都排列得整整齐齐的,小路要修得漂亮,大道要分岔,美丽的树木要修剪成伞形或扇形,栅栏要精雕细刻,篱笆要加上花纹,弄成方形,篱笆的走向要拐来拐去的,草坪上要铺上英国的细草,草坪的形状有圆的、方的、半圆的和椭圆的,美丽的紫杉要修剪成龙头形、塔形和各种各样的怪物形,花园里要放上漂亮的铜花瓶和石头雕刻的水果!”
 由于热爱纯粹本性天成的美,卢梭不仅反对任何出于功利与虚荣目的从而与自然美对立的臆想的美,而且反对任何反季节、反自然的人工的美:“我要把一个季节的美都一点不漏地尽情享受;这个季节没有过完,我绝不提前享受下一个季节的美……正月间,在壁炉架上摆满了人工培养的绿色植物和暗淡而没有香味的花,这不仅没有把冬天装扮起来,反而剥夺了春天的美。”
由于热爱纯粹本性天成的美,卢梭不仅反对任何出于功利与虚荣目的从而与自然美对立的臆想的美,而且反对任何反季节、反自然的人工的美:“我要把一个季节的美都一点不漏地尽情享受;这个季节没有过完,我绝不提前享受下一个季节的美……正月间,在壁炉架上摆满了人工培养的绿色植物和暗淡而没有香味的花,这不仅没有把冬天装扮起来,反而剥夺了春天的美。”
 在自然物的美与人工制品及艺术品的美之间,卢梭高度推崇前者而贬低后者,原因很简单:构成自然物之美基础的自然物是纯粹自然天成的,因而自然美(自然物的美及自然而然的美)也是天然、真实的;产生人工制品及艺术品的人是造作、虚伪甚至是丑恶的,亦即非自然的,因而艺术及艺术美也是人为、虚假的。
在自然物的美与人工制品及艺术品的美之间,卢梭高度推崇前者而贬低后者,原因很简单:构成自然物之美基础的自然物是纯粹自然天成的,因而自然美(自然物的美及自然而然的美)也是天然、真实的;产生人工制品及艺术品的人是造作、虚伪甚至是丑恶的,亦即非自然的,因而艺术及艺术美也是人为、虚假的。
卢梭不仅对双重意义上的自然美问题均有深刻论述,而且从趣味或审美力(taste)的视角对产生自然美(尤其是自然而然之美意义上的自然美)的自然审美做出了深入探讨。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偏后部分专门对人类“审美的原理(the principles of taste)”进行了一番具体而微的哲学探讨。卢梭指出:“审美力是对大多数人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进行判断的能力”,它“只用在一些不关紧要的东西上,或者,顶多也只是用在一些有趣味的东西上,而不用在生活必需的东西上,对于生活必需的东西,是用不着审美的”
 。他认为,原始人并不具备审美力
。他认为,原始人并不具备审美力
 ,但现代人的“审美力是人天生就有的”,因为“审美力是听命于本能的”“我们对审美力的原理无可争辩的”
,但现代人的“审美力是人天生就有的”,因为“审美力是听命于本能的”“我们对审美力的原理无可争辩的”
 。卢梭对趣味或审美力的界定表明,他已经在康德对“审美”与“美”做出经典界定之前,不仅把捉到了现代美学的核心观念——审美无利害性即审美是人无关功利的情感判断活动
。卢梭对趣味或审美力的界定表明,他已经在康德对“审美”与“美”做出经典界定之前,不仅把捉到了现代美学的核心观念——审美无利害性即审美是人无关功利的情感判断活动
 ,而且认为审美是人的一种既自然又自由的先天能力。就卢梭对双重内涵的自然而非人工化了的艺术之推崇而论,卢梭所关注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应该主要是基于对双重内涵的自然之欣赏来讲的,他所关注的审美能力应该主要指针对双重内涵自然的审美能力或自然审美能力。
,而且认为审美是人的一种既自然又自由的先天能力。就卢梭对双重内涵的自然而非人工化了的艺术之推崇而论,卢梭所关注的审美无利害思想应该主要是基于对双重内涵的自然之欣赏来讲的,他所关注的审美能力应该主要指针对双重内涵自然的审美能力或自然审美能力。
对美与审美的关系问题,卢梭认为二者是共属一体的,而非分离的。所以,尽管卢梭论及多种多样的美,但他并不认为以这些事物来命名的美就是这些事物的一种属性。就自然美而言,卢梭说:“自然的壮丽存在于人心中,要看到它,必须感受到它。”
 换言之,自然美并非自然物的自然属性
换言之,自然美并非自然物的自然属性
 ,而是人在审美过程中获得的。相对于人们更为熟悉的作为审美活动成果的“自然美”,卢梭其实应该更看重根本而过程化的“自然审美”活动。
,而是人在审美过程中获得的。相对于人们更为熟悉的作为审美活动成果的“自然美”,卢梭其实应该更看重根本而过程化的“自然审美”活动。
卢梭深知,人类文明愈是发展,非自然化的程度便愈甚;人的社会化程度高,人便愈是远离天性自然,人也就愈丧失先天的自然趣味与自然审美能力:“我们愈脱离自然的状态,我们就愈丧失我们自然的口味(natural tastes),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习惯将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而且将那样彻底地取代第一天性,以至我们当中谁都不再保有第一天性了。”
 因而,古人比现代人更接近自然:“古代的人既生得早,因而更接近于自然,他们的天才更为优异。”
因而,古人比现代人更接近自然:“古代的人既生得早,因而更接近于自然,他们的天才更为优异。”
 社会地位低的下层人士比社会地位高的上流人士更接近自然:“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所处的阶层越是低贱,天性自然越少被伪装。”
社会地位低的下层人士比社会地位高的上流人士更接近自然:“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所处的阶层越是低贱,天性自然越少被伪装。”
 所有人为的人工制品及由此产生的美是在违背自然人性即不自然的背景下产生的,就此卢梭有理由宣布现代社会中一般由上流社会贵族和精英们所代表的非自然的审美与美都是不合法的。
所有人为的人工制品及由此产生的美是在违背自然人性即不自然的背景下产生的,就此卢梭有理由宣布现代社会中一般由上流社会贵族和精英们所代表的非自然的审美与美都是不合法的。
卢梭由此强调,远离不自然和反自然的社会,通过回归自然、接近和热爱自然来保持或重新获得自然审美能力:“我时时刻刻要尽量地接近自然,以便使大自然赋予我的感官感到舒适,因为我深深相信,它的快乐和我的快乐愈相结合,我的快乐便愈真实。我选择模仿的对象时,我始终要以它为模特儿;在我的爱好中,我首先要偏爱它;在审美的时候,我一定要征求它的意见。”
 以自然及自然(审)美为美与审美的原型、标准不只是卢梭本人热爱、推重自然与自然美的证明,也应成为处于义无反顾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现代人需要牢记的箴言。
以自然及自然(审)美为美与审美的原型、标准不只是卢梭本人热爱、推重自然与自然美的证明,也应成为处于义无反顾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现代人需要牢记的箴言。
为此,卢梭在论教育的《爱弥儿》中特别宣示了一种可称之为自然审美教育的美学理念。他写道:“我的主要目的是:在教他认识和喜爱各种各样的美的同时,要使他的爱好和审美力(taste)贯注于这种美,要防止他自然的口味改变样子,要防止他将来把他的财产作为他寻求幸福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本来就是在他的身边的……我们可以通过它们去学习利用我们力所能及的好的东西(good things)所具有的真正的美来充实我们的生活。我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道德上的美,因为这种美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心灵的良好倾向的;我所说的只是排除了偏见色彩的感性的美,真正的官能享受(real delight)的美。”
 联系前述卢梭对于受控于艺术家、权贵、富翁的随心所欲、贪心和虚荣心的艺术美之现状的抗议,以及卢梭对大自然给良心没败坏之人所安排的最简朴、最宁静、最自然且最有乐趣的田园生活的推崇
联系前述卢梭对于受控于艺术家、权贵、富翁的随心所欲、贪心和虚荣心的艺术美之现状的抗议,以及卢梭对大自然给良心没败坏之人所安排的最简朴、最宁静、最自然且最有乐趣的田园生活的推崇
 ,可以肯定:第一,在众多美的种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自然美和自然审美,因为自然美是避免了偏见的侧重感性和官能享受的美,它虽非道德美却与人的良心或美好心灵密切相关,因而是“真正的美”;第二,自然美的获得和保持或培养自然审美能力的关键是尽量与大自然保持亲密接触,过一种简单朴实而有规律、天然宁静而有乐趣的自然而然的生活;第三,自然审美的实质或宗旨不过是一个人经由“自然”而完成的自我个体启蒙或从席勒开始备受青睐的审美教育。
,可以肯定:第一,在众多美的种类中,最值得珍视的是自然美和自然审美,因为自然美是避免了偏见的侧重感性和官能享受的美,它虽非道德美却与人的良心或美好心灵密切相关,因而是“真正的美”;第二,自然美的获得和保持或培养自然审美能力的关键是尽量与大自然保持亲密接触,过一种简单朴实而有规律、天然宁静而有乐趣的自然而然的生活;第三,自然审美的实质或宗旨不过是一个人经由“自然”而完成的自我个体启蒙或从席勒开始备受青睐的审美教育。
综上所述,卢梭是存在着清晰、完整的以回归自然为旨趣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然美及自然审美思想的。此“回归自然”,首先意味着回归到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其次意味着回归到一种自然状态,过一种可称之为自然审美的自然而然的生活。相对于研究者看重的自然物之美的自然美观念,卢梭与自然物之美密切相关的自然天成之美的自然美思想更为根本,也更加重要。启蒙背景下卢梭的自然美与自然审美论即本书所指称的卢梭自然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