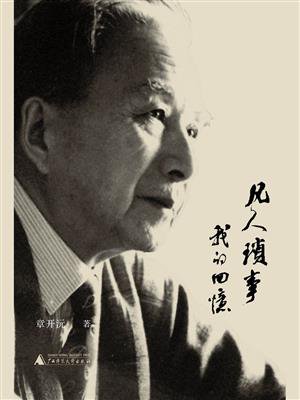青弋江边的家
解放前我没有固定的家。童年时期总是随着父母流转,时而上海,时而芜湖,时而苏州,时而凹山(今马鞍山),时而武汉,时而重庆。直到1938年秋天,父亲应好友贾伯涛邀请,前往赣南师管区(贾为司令)担任军需工作,母亲与他同行,我们姐弟四人(开明、开诚、开沅、开永)被送往江津乡下国立九中读书,遂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但是对我这样家庭观念淡薄的无知少年来说,学校仿佛就是我的家,而且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管吃管住管学习,虽然相对艰苦,倒也衣食无愁。不过好景不长,1943年暑假被九中校方开除,我才真正产生无家可归的感觉。
抗战胜利以后,我终于回到芜湖老家,重新与祖父母、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众多家庭成员团聚。但我很快就到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经常住在学校,无非寒暑假抽空回家看望长辈而已,因此家庭观念仍然比较淡薄。1948年冬天从南京进入中原解放区,加入了革命大家庭,从此再未回过芜湖那个老家。全国解放以后,由于无力继续经营,祖父兄弟三人把芜湖面粉厂连同祖屋全部卖给国营粮食公司。祖父携大姑一家迁往南京,二叔祖夫妇从上海搬到苏州,潜心休养,闭门谢客,年龄最轻的三叔祖也在南京自立门户。从此,芜湖老家永远消逝,我终身任教的华中师大俨然成为我的又一个大家,直到1957年与怀玉结婚,这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家。
然而,芜湖老家留给我的印象毕竟难以磨灭,因为从曾祖父开始,那里住过我家四代人,而我的童年在那里也生活得最久。
老家在芜湖东门(原名金马门)外青弋江边,当时应属郊区,基本上是个农村,只有一条长长的青石板路通往县城,本地人自豪地称之为“十里长街”。我家孩子们上小学,每天都要成群结队走过这条交通要道。我很喜欢这条路,因为铺路的青石板平整而又光滑,尽管那一条条独轮车碾压刻下的凹槽记录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沧桑。离家不远处路的右侧有一家规模较大的杂货店,早上还卖豆浆和油条之类的点心。路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水塘,种植莲藕并养鱼,夏季那满池红白相间的荷花赏心悦目,冬季又可以看到清塘后众多抓鱼的热闹场景。再往前走,路的两侧都是条条块块的水田与菜地,青石板路俨然成为大号田埂。途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几座密集的大石牌坊,记载着几个大户人家(包括李鸿章后代)的功名与节烈。历经岁月消磨,牌坊的浮雕与文字漫漶不清,但我每次放学回家经过,总不免要抚摸端详一番,当然这与考古和史学无涉,完全是出于童稚的好奇。
从牌坊群继续往城里走,还要经过一座高架铁路桥。我们最大的乐事便是观看长长的火车轰隆驶过。因为那些年城乡之间未通汽车,连黄包车与自行车都极少,与我们相伴而行的,除肩挑手提的菜贩以外,只有那运货或载人的吱吱呀呀的手推独轮车。对于我们这些乡间儿童来说,火车便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物,正如四川乡下人一样,直到抗战期间还把火车运行称为“洋房子搬家”。
走过这威风凛凛的铁桥,不久便到达我们长途跋涉的终点——襄垣小学。
我的老家实际上与面粉厂连成一体,不过工厂在最东头,住宅在最西头,中间隔着占地面积极大的百余号木质仓库与晒麦广场,所以家人感受不到粉尘污染,更听不见机器轰鸣。工厂连同住宅的外面有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东西南三面的外层建筑都是粮仓与公司办公楼,仿佛是城堡的外层,把我家与外面的世界隔开。
按照原来的设计,公司办公楼与住宅实际上也是一座连体建筑,都放在最东头,办公楼在外,住宅在内。进入公司大门便是大客厅与厅前的天井,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办公用房,其格局颇如北方的四合院。穿过客厅并以屏风遮掩,才是厂主私宅的大门,不过此门经常关闭。即使偶尔打开,也有另一座屏风遮隔,屏风上是父亲在红纸上书写的很大的福字,可能有福气不外泄的意思吧。住宅同样是四合院格局,主人住的是两层楼房,东西两侧都是平房,供仆人居住或是作储藏室。天井比公司办公楼更大,相当于一座篮球场。客人来我家,一般不走公司正门,而是从公司东西两个侧门绕道进来。因为住宅除直接面向办公楼的正门外,还有东西两个侧门。这并非出于什么礼仪考虑,而是因公司一进大门便是营业部,为顾客出入之所,员工也是来来往往,比较喧嚣嘈杂。听说特别尊贵的客人前来(如前两江总督周馥及府、县以上直接管辖的地方官员),公司便暂停营业部工作,让贵宾经由正门直接进入住宅客厅。不过,余生也晚,记忆中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盛况。
住宅也分东西两个单元,仿佛是连成一体的两座大四合院。祖父与姨太太及其子女住在东院,祖母与父母及我们兄弟姐妹住在西院。西院与公司大门及办公楼是原先的老式建筑,住宅全部是仓库改建的,地垄甚高,木质结构,高大然而阴暗。祖父虽然不在西院住,但楼上正厅供有历代祖先牌位与画像,显示出嫡系正房的身份。东院的地位虽然是侧室(不是住宅建筑群的主体),但却是一次火灾后重新修建的新式楼房,不仅采光甚好,而且装修更为讲究,宅前有宽大的草坪,两边有各色盆景与鱼池点缀,顶南头还有一座高大的花坛,四季都有鲜花盛开。祖父坐在办公桌边,透过大玻璃窗,满眼都是花草争妍,夏天青弋江涨水后还可以看见缓缓经过公司大门的帆船桅杆。
随同祖父住在东院的,还有庶出的小叔祖兆森(向荣)和他的养母(曾祖父的妾,蓄发在家修行,大家称之为“二老师太”),也许他们按传统礼俗以住侧室为宜。不过住东院与名分不大相称的,除作为一家之主的祖父外,还有他执意留在身边的我那大哥开平。他被安排与小叔祖向荣同住楼上一间卧室,由于年龄相近,和睦相处,往往被外人认为是兄弟,虽然两者之间相隔两辈。这样安排说明祖父还不是那么守旧刻板,但却引起我母亲的不满,因为剥夺了她亲自抚育长子的权利。
西院的主角当然是祖母,她独住坐北朝南的主卧室,隔壁房间则是三哥、五弟、六弟的集体宿舍。父母带着姐姐与我住在靠西边的两间卧室,中间与祖母相隔开的是一个大客厅,那是全家喜庆、祭祀、迎宾的中心地点,但平常则显得异常空旷冷清。大厅平时也是祖母、父母与我们兄弟姐妹的餐厅,中间摆一张很大的圆餐桌,可以容纳二十人同时进餐,但平时进餐者不超过十人,显得过分宽松。逢年过节祖父往往独自带着大哥过来与我们共进午餐或晚餐,这时就显露出明显的嫡庶之分。
西院的楼上没有住人,二楼正厅供奉众多祖宗牌位,他们的彩色画像平时收藏在壁柜里,只有每年春节前后才被“请”下楼正式供奉。所谓“请”祖宗,照例由父亲以长房长子身份,从楼上一摞一摞抱下来,然后按世代顺序,一张一张展开,再按既定的位置逐一挂在墙上。由于祖宗人数很多,墙壁几乎都挂满了。每逢“请”祖宗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帮助父亲展开祖宗的画轴。父亲紧握画轴站立不动,我们则是轮流上阵,手执画轴末端缓缓后退,直至画卷全部展开。但这种活只有男性亲属干,女性则严禁触摸,这是重男轻女的表征之一。祖宗画像几乎人人都是神气活现的官员,冠带袍服,正襟危坐,近似现今大官们的标准照。其实除十二世节文公及其子孙三代有五六人担任过知县、知州乃至道台等官职外,其余大多为没有任何功名的白丁,只是后世荣显循例申请朝廷赏以相应封典,所以连同糟糠之妻都变成官太太了,正所谓光宗耀祖是也。对于这些翎顶辉煌的画像,我们很感兴趣,往往看了又看,但无非是如同看京戏与连环画那样的好奇,并没有任何血脉上的归属感。
楼上左侧的两间房,是祖母念经拜佛之所,供有如来、观音之类菩萨,还有邪门歪道的“大仙”牌位。“大仙”与香港的“黄大仙”同出一源,其实就是狐狸、黄鼠狼之类的“妖异”,谁也没有真正见过,但总认为不能得罪,唯恐它降祸酿灾,至少是鸡犬不宁。楼上西边两间房,主要是供藏书与保存珍贵衣物之用。图书是清一色的樟木箱收藏,排列得整整齐齐,但自从曾祖父维藩公过世以后,似乎没有什么人上楼认真阅读。衣服则是用清一色的大牛皮箱分别收藏,也排列得整整齐齐,其中主要是皮毛冬衣。每逢春秋两季晴好天气,祖母必定督率仆妇取出挂在天井里晾晒,那形形色色的皮毛也增添了我们兄弟观赏的乐趣。在我稍为记事的时候,西院楼上似乎从来无人居住。大概是由于几位姑奶奶(祖父的妹妹或堂妹)出嫁外地,而二叔祖则全家迁居上海,所以这些卧室便空出来了,为我们童年嬉戏增添了若干空间。
楼下客厅正面靠墙摆着一张长长的供桌,上面置有玉如意、拂尘、香炉、烛台和铜磬等礼器。墙上挂着松鹤延年之类大幅国画,对联是晚清陆润庠写的,但不知为什么下联却有“书赠学海”字样。我父亲是戊戌以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当然不可能与这位资深状元公有什么交谊,大概是哪位长辈代为索求的。客厅东西两侧墙上挂满了三舅公(祖母之兄)亲笔书写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可能是作为祖父祖母新婚礼品送来的。他是前清举人,在南京财政部任秘书,所以书法是明显的馆阁体,方方正正,笔笔不苟,一如格言作者的精神风貌。当时我还很难理解格言深意,也从未有哪位长辈为我讲解过这么长篇大论的家训。只不过每到吃饭时间必定可以看到它,其中有些通俗话语逐渐留下印象,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此后都成为我身体力行的座右铭。只是朱老夫子说“三姑六婆,淫盗之媒”,祖母却视若无睹,经常与附近寺庙道观的尼姑、道姑来往,而且关起卧室房门亲密叙谈。我们也许是受朱老夫子影响,总觉得他们的行踪有些诡秘,因而就躲避得远远的。
西院正房楼下四间卧室,陈设都是大同小异。南面临窗摆一张红木方桌和四把椅子,两侧分别是梳妆台、书桌与书橱。里面靠墙是一张宁式雕花木床,床头置有五斗柜,对面则是一排大衣柜,床后有江南人家必备的红漆描金马桶,仿佛现今卧室的卫生间,同时又放若干杂物,兼具储藏室功能。我的卧室原来大概是父母结婚的新房,家具都是维藩公在城内创建的专业工厂制作,完全是宁波式样,衣柜一色黑漆雕花,而且都有很大的穿衣镜。我睡上床一眼便可看见这排穿衣镜,里面正好映现与其相对的五斗柜镜子,而五斗柜的镜内又映现穿衣镜……如此循环往复,常能引发我的童稚遐思,谈不上什么光学与哲学的原理,却逐渐形成模糊的“无限”概念。我小时候体弱多病,但不乏想象与思索,常常对着镜子发呆,久久注视着那镜中重重叠叠的“无限”。由于孩子太多,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痴迷,除非正好碰上吃饭时间,才有女仆喊我出去。
吃饭的时候祖母居中就座,父母和儿女围成一圈,如众星拱月。背后照例站着几位女仆,我们真是“饭来张口,茶来伸手”。但饭菜却单调之至,早餐照例一碟豆腐干,一碟豆腐乳,外加两碟腌菜,主食长年只有稀饭而无面点。这样的早餐对于正在发育成长的儿童显然不宜,特别是我消化能力较强,每到中餐前往往饿得大口吐清水。可能还是由于孩子太多,我又爱独自躲在偏僻角落玩耍,所以没有任何大人发现我的悲惨状况。中晚饭菜也是大同小异,都是从东院小厨房(公司另有大厨房)做好送来,照例是六菜一汤,数量虽然不少,但可口食品实在不多。荤菜几乎一年到头都是黄豆芽烧肉(肉只是点缀而已),能够吃点鱼就算是美食。所以我们这些男孩特别口馋,连苋菜的红色汤汁都当作美味争相用来拌饭。进餐时气氛非常沉闷,祖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孩子们埋头吃饭不敢有任何嬉笑。其实祖母患胃病,进餐无非虚应故事,她的床头一排大衣柜上,整整齐齐放着七八个青花瓷坛,里面装着各种零食供她“少吃多餐”。她最爱嗑瓜子,没事时一颗接一颗不断地嗑,神闲气定,优哉游哉,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她从不分给我们一点零食,我们也从未有过向她索取的念头。母亲评论说:“没有生过孩子的女人,大抵都是这样。”但当时我还不懂这话的含义。
由于是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房子,所以西院一切都显得比较陈旧,加上墙壁与天花板都漆成深褐色,雕花玻璃的采光很差,更显得有些阴暗。住宅周围都是人口稀少的田野,老鼠与黄鼠狼经常潜入乃至繁殖。楼上房间常年没有住人,晚间便成为这些小动物肆意游走的乐园,并且成群结队在楼板上跑出阵阵响声。祖母虽然养了好几只猫,然而由于过分娇养,太懒太胖,未能起任何震慑作用。祖母迷信而又胆小,竟把黄鼠狼当作狐仙,在楼上佛堂内供上不伦不类的“大仙”牌位,每逢初一、十五必定以水果糕点供奉。我们偶尔上楼游戏并偷食供品,她还感到非常欣慰,称赞“大仙真灵呀!”但我们也感到这楼上阴气太重,神秘而又阴森,只有白天才敢结伴上楼,晚上连黑洞洞的楼梯口都不敢进入。父母也严禁我们晚间上楼,唯恐孩子受惊生病。
但是西院的宽阔天井却是我们童年欢乐的泉源。天井主体地面用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笔直的纵横交错的石缝正好可供玩“跳房子”游戏,同时也是踢毽子、玩皮球、滚铁环的最佳场地。幸好天井特大,所以阴暗的老宅还拥有一大片明亮的天空。对于我们这些经常被关闭在阴暗老屋中的孩子来说,天空太可爱了,白昼可以看见蓝天白云,夜晚可以看见繁密星星。特别是在秋高气爽的季节,蓝天下有许多似烟似纱似絮的云朵不断游动,夜晚有灿烂的长长的银河横亘。夏季暴风雨前的天空,乌云翻滚,变幻莫测,展现多种多样的形状与色彩。及至倾盆大雨泼在青石板上溅起簇簇白雾,雨水顺着屋檐涌流而下,又仿佛许多小小的瀑布千姿百态。如果是严寒的冬天,融化的雪水又会在屋檐下结成一串串冰溜,在雪后放晴的阳光下辉映出绚丽的色彩。
天井东西两侧各有一块空地未铺石板,由于年深日久,泥土上已经长满青苔,却给这阴冷萧瑟的西院增添若干生命的鲜活。对于老宅中的孩子们来说,这两大片泥地简直是富饶的宝藏,捕捉蝴蝶、蜻蜓、金龟子,挖蚯蚓,都是百玩不厌的乐事。我最爱看蚂蚁搬家,一个个蚂蚁衔着食物,不疾不徐走成长长的行列,这进退有序的运输队伍连绵亘续,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偶尔还可以看蚁战,不同颜色与不同体型的蚁群相互咬斗,勇猛异常,往往可以吸引我蹲视大半天。
春天来了,母亲总爱为我们孵一大窝小鸡,母鸡带着小鸡到处啄啄扒扒,觅食中洋溢的亲情与生活气息,多少减退了这老屋的阴冷。天井南端左侧屋檐下,有木板制成的一大片鸽棚,栖息着上百只青灰与白色的鸽子。虽然夜晚那咕咕的鸣叫声扰人清梦,但白天看它们在屋顶上嬉戏、觅食,更多是在蓝天白云下盘旋翱翔,我们童稚的心灵仿佛也随之飞越这大院的樊篱。还有客厅天花板上靠近大吊灯底座的燕子窝,每年春天都有成双成对的燕子前来安居,不久便有啾啾鸣叫的雏燕出生,张开乳黄色的小嘴急不可待地争食老燕从远处叼来的虫蝇。此外还有那叽叽喳喳的麻雀,也常在屋顶瓦缝里筑巢繁衍,它们是不受怜惜的常客,也是唯一容许我们用弹弓射击的小动物。
但无论如何,对我们吸引力更大的毕竟还是高大厚实围墙外面的世界。除早晨上学、下午放学以外,祖父严禁我们私自出外,唯恐我们受到不良影响或被坏人伤害。但越是这样严控,我们就越想走出这阴暗刻板的老屋,有时便偷偷从西院侧门溜出去。门外河边是一大片晒场,每逢晴好天气,工人们便铺满篾席,从仓库搬出小麦翻晒,遍地金色灿烂,蔚为壮观。晒场前面是青弋江堤岸,江以水色清亮得名,乃长江一条支流。岸边有一行柳树,树干有粗大至难以合抱者,大概是维藩公那一代创业者种植。柳枝拂曳在水面上,引得游鱼群集,吮吸柳叶唧唧发声。我常爱坐在岸边树下,聆听游鱼细语,或看捕鱼人撒网扳罾。对岸(芜湖城里人称为河南)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每到春天,最耀眼的是菜花的遍地金黄。所以我在小学学画水彩,最爱用的就是嫩绿(柳叶)与金黄(菜花)二色。公司大门前有颇具气势的石砌码头,两侧有欧洲中世纪风格的路灯(不过已不用煤气,改为电灯),那是专为公司运送小麦、面粉的大木船设置的。
祖父三令五申不准我们下河玩水,母亲也唯恐孩子有所闪失,但那清亮的河水与美丽的南岸的吸引力实在太大。小叔祖与大哥等大孩子曾偷偷划小船到南岸(包括租界旧址)观光一次,引起全家巨大惊恐。我们这些小不点自然无此胆量,只有一个夏天,三哥约我偷偷溜到河边戏水,把内裤弄湿了。三哥住在祖母隔壁,老太太每天专心念经拜佛嗑瓜子,对孙辈不闻不问,所以从从容容回到了自己卧室更衣。我因为住在母亲隔壁,时刻处于监控之中,唯恐她用指甲在我腿上划出白痕(这是过去父母检查孩子是否偷偷游泳的简易方法),只好躲在一棵大柳树背后,把内裤晒干后才悄悄回家。
晒场西边是一大片简陋茅屋,那是部分面粉厂外来工人的住宅,也有少数邻近农民或手工业者杂居其间。这是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社区,与面粉厂的多层高楼及厂内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反差。不过大院围墙内的孩子们是寂寞的,茅屋区的儿童则可以成群结队尽情玩耍。一道无形的墙把我们彻底分隔开来,即使偶然相遇,彼此也互不理睬。我从未进入任何一座土坯茅屋,很难想象其中贫困情景。只有在天寒岁暮,年号(一种类似唢呐的乐器)声在北风中摇曳,时时又听见茅屋中人为患病儿童“叫魂”的呼唤,我才模模糊糊感受到茅屋区的若干悲凉,而逃难到四川进入乡下中学以后,这种感受又逐渐转化成为比较清晰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