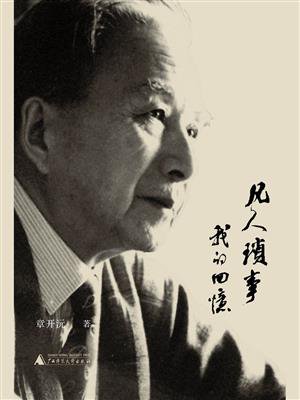小学
现今人们把上小学以前所受教育统称为学前教育。说来惭愧,我从未上过幼儿园,也未正式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但芜湖老家确实有过中西合璧的家塾,就设在曾祖父在世时接待外宾的那座小洋楼客厅的一侧,几位堂叔与大哥都曾在此就读。老师姓王,清末曾中举,因此颇有旧学根底,西学只能由他人任教。我四五岁时,父母让大哥带我去学认字,其时王老先生已经因病回家疗养,由他儿子代课,我们喊小王先生。小王先生学问如何,幼稚愚鲁如当时的我,自然不够资格评论,但他至少能够教我识字描红。但大孩子们都不喜欢他,说他比老王先生差得太远,实际上他们早已不甘就读于这种陈旧的家塾,渴望走出家门进新式学堂。很可能是由于某个大孩子的策划,我居然斗胆写了一张大逆不道的“反标”:“小王先生是乌龟。”“乌龟”两个字笔画多,我不会写,只好用类似原始象形文字涂鸦。小王先生发现后大发雷霆。不过毕竟已经是民国二十年(1931),虽是私塾也比过去文明得多,加上我的年龄太小,他不便使用戒尺敲打,便罚我跪在大厅正中“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前,直到父亲闻讯亲自前来反复道歉,才结束这场风波,幸好没有惊动祖父。这大概就是我出生后第一次参与“学潮”,在守旧老辈看来则是与生俱来的顽劣。
其实父亲早已不满这种落后的教育方式,因为他自己曾经深受其害,不愿弟弟们与长子继续耽误正常学业。二叔祖夫妇头脑较新,对此也担心已久,只是碍于传统伦理观念,不便直接批评乃兄而已。正好王老先生病危,小王先生急于回家照顾,父亲送他一笔丰厚礼金,然后征得祖父同意,写信把他辞退了。客观上家塾也难以为继,因为叔叔们先后都随自己父母迁往上海,而大哥和我也随父母前往武汉,从此已走的与未走的孩子都进入新式中小学。这就是芜湖章家来得太迟的“教育转型”。
我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武昌胭脂山小学。胭脂山是蛇山北麓的小山,以山岩呈丹霞色彩得名,离昙华林及阅马场不远,离我家更近,循青石板路走刻把钟就到了。姐姐读二年级,我读一年级,两人结伴而行。但因不在一个课室,进校后她就难以照顾我了。这个学校留给我的印象不大好,一是仍然盛行体罚,二是有些同学欺侮外地人。
与我同桌的是一个姓王的女生,她虽然娇小,但却非常刁蛮,总是不断扩张自己在课桌上的版图,侵占我应有的半边领地。如果稍有违抗,必定倒竖柳眉,圆瞪杏眼,继而便用尖利的指甲抓我的手背。因此我上课时只得紧缩躯体,以免惹她生气。本地男同学更厉害,一个个勇猛善斗,颇有三楚雄风。我是在旧式大家庭被管束得服服帖帖的孩子,加上发育不良,矮小瘦弱,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曾经在山坡上被猛推滚下来,好半天喘不出气,连右臂都扭伤了,很难穿套头毛衣。回家还不敢声张,因为母亲性情刚强,会骂我没有出息。
因为上课时总是惴惴不安,期中考试成绩欠佳,所以得不到老师的关爱。特别是教语文的女老师(姓凤),爱用教鞭敲击,且出手颇重。有次在课堂上写毛笔字,同桌女生故意用臂膀撞我,以致墨汁溅上大字本,有些字又写出格,显得非常难看。凤老师收作业时发现,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我的手就用教鞭敲打,只两鞭手心就红肿起来。我痛极也不敢出声,否则还得多挨几鞭。此后每逢天寒手冻,我便学习其他同学经验,上课前把手心在课桌边角上摩擦得热乎乎的,以免冷手挨重鞭更吃不消。不过,看见这位中年女老师特大的黑眼眶,还有那蜡黄而瘦削的脸,我内心只有同情而无怨恨,常常为作业差错甚多而愧疚。
第二学期时已逐渐适应这个陌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成绩有所提高,期末居然名列全年级第一。学校发给我奖状,姐姐也得到一张卫生模范奖状。姐弟高高兴兴结伴回家,不料竟引发少数同学的忌妒,一出校门他们就呼朋引类围着刁难我,幸好姐姐大我三岁,个头又较高大,赶紧护着我一路小跑回家。可能正是因为这些不愉快的遭遇,我对武汉颇有偏见,甚至有希望永不再来武汉的心结,但老天爷真会开玩笑,居然安排我在武汉工作一辈子。
1934年回到芜湖,随着姑姑、姐姐、三哥,还有五弟和六弟读城里襄垣小学,一共有七八个孩子,每天清晨出门,结伴成队,沿着青石板路徐徐行进。沿途田野广阔,有几个很大的池塘,岸边野草丛生,水蓼开着一簇簇白色或紫红色小花。据说溺水者多半是被这些野草藤蔓绞绊住手脚,因此花蕊里藏着死者的魂灵。我对生死一无所知,因此没有什么惧怕,路过时常摘几朵花放在书包里,希望这些无依的精灵能够与我结交作伴。路上还可看见许多趁早进城的行人,有的挑担,有的提篮,还有的推着吱吱呀呀的独轮车。离家走出一里多,要穿过几座巍峨的石头大牌坊,还有许多手工业者聚集的砻坊(磨米面)、榨坊(榨油)、染坊、踹坊(布匹染色后,以元宝形大石头压平),等等。偶尔也有一两家供应行人早点的乡村小店,刚出锅的油条喷出香气,但我们是不准在外面买零食吃的,身上又没有零用钱,只能咽着口水投以羡慕的眼光。不过我们还是把上学视为赏心乐事,因为可以走出老宅的围墙,进入一个新鲜的比较开阔的世界。上学的路虽然很长,但说说笑笑,东张西望,一点也不觉得疲累,虽冒风霜雨雪却其乐陶陶。
襄垣小学建在孔庙旁边,据说早先是贡院且有考棚。小学的校园与孔庙相联结,我们经常举行纪念周的大礼堂,就是孔庙的明伦堂,而且这个匾额一直挂着,因为每年祭孔时还得利用它作为主会场。襄垣是芜湖的古地名,小学师资力量较强,在当地颇有名气,所以祖父“择校”把我们都送去。小学不仅环境好,学风好,而且文艺活动非常出色。校长张学诗是艺专毕业的画家,大礼堂讲台上的超大孙中山画像就是他的作品。教导主任姓程,是科班出身的音乐老师,除用心开展群众歌咏活动外,还尝试把京戏改编为现代歌剧。他创作的《三国演义》折子戏,如《打黄盖》《蒋干盗书》《草船借箭》等,曾在明伦堂公开演出,引起极大轰动,其中周瑜与蒋干两个主要角色都由我们班上同学扮演。这个学校还比较注意改进教学方法,比如语文课讲到西门豹治邺,为破除迷信陋习把装神弄鬼的巫婆投入河中,就安排学生在课间作为小品演出。我理所当然地演巫婆,并非因为演技好,而是因为最瘦小抛起来很省力气。这些所谓小品,非常幼稚粗糙,但或多或少还能引起学习兴趣并加深印象。所以这篇课文我至今记忆犹新。
章家这群孩子,上课时分散在各个年级,各有自己相好的学友在课余嬉戏。中午经校方同意,集中在一个教室进餐并休息。因为离家太远,来回需两三个小时,午饭是由工人张师傅挑来,一头是菜和汤,一头是米饭。我们家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喜欢这位中年师傅,他身强体壮,行走如飞,虽然隔着好多里的路程,饭菜送来时竟然热气腾腾。我们吃得很香,当然菜比我们西院的平常午餐略好一些,这多少也体现了祖父对上学孩子的关怀。我们吃饭的时候,师傅坐在一边,叼着烟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据父母说,他在曾祖父生前就来我们家工作,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张南轩,可能就是维藩公为他取的,因为老爷子好像有为人取名的习惯。他是芜湖人,家在工厂附近农村。我们全家老小都直呼其名,他丝毫也不见怪,总是乐呵呵地埋头干活,偶尔也哼几句芜湖民间小曲——南音。
他应是属于马拉松类型的长跑选手,据说轻轻松松便能日行一百多里,颇似《水浒》神行太保戴宗。但戴宗需要乞灵于神符,他却全凭苦练出来两条神腿。他曾让我们观看并抚摸这双腿,肌肉坚实,青筋凸露,确实非同凡品;加上浓眉大眼,漆黑络腮胡,又很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他在我家身兼数职,除买菜、做饭、送饭外,还要用手工轧面机制作挂面,有时又为祖父到较远的地方递送急信,仿佛现今的特快专递,迅速而且可靠。他除了患腿部静脉曲张以外,别无其他疾病,加之性格温和开朗,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为改组后面粉厂留用的最老工人,并很快被提拔为干部,与在北京从事面粉工艺研究的学澄叔仍然保持密切联系,据说还经常挂念已分散到各地的章家孩子。
由于学校环境良性变化,我已不再把上学视为畏途,但也只平平顺顺读了一年,学校内部便发生一场风波。原因是张校长惜才,颇为重用四位刚从大学毕业的新教师。他们很想有所作为,思想也比较激进,因此引起若干原有资深教师的妒忌。后者人数不多,但都是教学骨干,且个别人与县政府或党部官员声息相通,给张校长带来较大压力乃至冲击。我们这些小学生当然不会也不想了解这场风波的内幕,但父亲却非常尊重并关心张校长。也可能是因为校长名张学诗,自己名章学海吧?一向小心谨慎的父亲,居然说服了明哲保身的祖父,把正在风口浪尖的张校长请来任专职家教。想当年小学校长在县城里是有头有脸的人,但张校长正好可以借此辞去学校职务,摆脱各种无聊纷争,退居乡野韬光养晦,所以立即接受了父亲的盛情邀请。
教室仍然在小洋楼二楼正厅,右侧的西式大餐桌正好坐得下老师与七八个学生,便于进行不同程度的复式教学,宽阔的大厅及走廊有足够的空间让学生轮流听课、作业与游戏。客厅的左侧是一个很大的套间,外间是办公室,里间是卧室。张校长教学非常认真,除星期天回城里的家休息以外,每天从早到晚都为我们讲课并批改作业。一日三餐由厨房做好送来,无非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天冷则把汤改成火锅。父亲唯恐老师独自吃饭感到寂寞,特命三哥与我陪同共进午餐。午餐送来往往较迟,早上的稀饭就咸菜毫不顶事,我经常饿得大口直吐清水;加上张校长沉默寡言,不苟言笑,我更把共进午餐的美差当作苦难。
张校长可能不了解我的苦衷,他好些年来最喜欢开诚这个好学生,据父亲说他之所以屈就家教,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开诚。尽管当时已不兴包办婚姻,三哥又不到谈婚事的年龄,但校长还是向父亲表露了真诚的心愿。我不知道大我两岁的三哥是否已懂情爱,只知道他以后确曾与张校长有书信往来,长期保持亲密的师生情谊。但由于全面抗战爆发,颠沛流离,彼此相距甚远,终究未能成为校长的乘龙快婿。
张校长虽然是学艺术出身,但却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浪漫而不拘形迹,平常总是衣冠整洁,穿一身合体西服,上课必系领带,颇有彬彬儒雅的绅士风度。讲课也是柔声细语,从不责骂学生,顶多只作委婉的规劝,但这种真挚的规劝往往比打骂更能深入人心。有次三哥写作文时把“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之类套语改成“时间比欧文思跑得还要快”,备受校长称赞。欧文思是当时美国黑人短跑健将,多次打破世界纪录,因而成为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偶像。我特别羡慕三哥的神来之笔,每逢作文写到时间都照搬兄长名言。张校长深不以为然,皱着眉头规劝:“西方人有句话,第一个把漂亮女人比作月亮的是天才,第二个则是白痴。”至今我仍然找不到此语出处,但当时就感觉这句话分量很重,仿佛禅宗的当头棒喝,因此印象很深,终生难忘。我记不清张校长为我讲过哪些课,但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即必须努力发明创造,模仿抄袭是没有出息的。
张校长在我家只教了一个学期,据三哥说是应聘到桂林一所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去了,从此我们再未能相遇。
在小洋楼读书期间,还有一位老人给我印象很深。他不是一般工人,而是相当于这栋楼房的管家,我们都尊敬地称“杨老爷”。他原来是曾祖父当地方官时的部属,曾带过一艘小兵船(炮艇之类)。曾祖父辞官下海,他因仕途无望,也跟着来到芜湖,从一开始就负责管理这幢小楼,照料重要客人的饮食起居,相当于现时的小型“外招”。曾祖父死后他不忍离去,反正自己儿女均已成家立业,没有任何牵挂。他仍然管理这座小楼,尽管其功能已经多次变更。早先手下还有几个工人分头任事,及至改为家塾以后,由于接待任务很少,只剩下他一人照管。附近有座小花园,另有公司员工管理,无需他操心。尽管职权范围缩小,但依然极端认真,窗明几净,陈设井然有序,一如曾祖父生前。他比祖父年龄略长,所以大家喊他杨老爷,他也坦然应之,并不感觉是什么抬举。他是桐城人,由于长期在江上工作,皮肤呈古铜色,躯干魁梧,长方脸,八字胡,颇有几分武官气概。但又毫无架子,事必躬亲,勤勤恳恳,整座楼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连地毯都是历久如新。他也有生活情趣,忙里偷闲,养了一只花猫与几只黄雀,是他朝夕的伴侣,也是我们喜爱的宠物。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连豆腐乳都省着吃。他的筷子是特制的,筷头削得极尖,很像日本人家常用的筷子,以免吃豆腐乳时夹得太多。我最欢喜坐在旁边看他吃饭,他也不以为忤,仍然吃得很香,偶尔对我点头示意而已。他的待遇比较丰厚,听说钱都节省下来寄回家买地盖屋去了。
二楼有间很大的储藏室,收藏很多过时报刊,以及其他来往信札、照相底片等,可能都是曾祖父在世时交他保管的。因为是老上级的遗物,他看得非常珍贵。十几年的各种报纸都按月装订成册,并且依照年代顺序置放,很便于查找。我曾经征得他的同意进去参观,记得数量最多的是《申报》,因为曾祖父死后,祖父仍然继续订阅,每天阅毕仍交他保管。我最感兴趣的是好多木箱装的玻璃照相底片和若干亲友来往信函,其中有些是五爷爷出国考察寄回的明信片,上面有许多国家的风景,文字后来记不得了,只记得那时把“纽约”写成“牛约”。现在想起来,这一屋子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可惜卖厂之后,家人搬得过于匆促,后来我到处打听都没找到这批文物的下落。
我是杨老爷比较宠爱的孩子,只要有空我就会溜进去看那些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兴趣盎然,流连忘返。老人家对我非常宽容,好像为我还能看祖上的遗物而感到欣慰。但他管理非常严格,绝不容许乱翻乱放,更不能容忍有任何污损。回想起来,是杨老爷最先培养我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我一辈子进中外图书馆或档案馆时,都是恪守规则,严于律己,小心翼翼,唯恐对馆藏书刊文献有所污损。
小洋楼东侧有座小花园,把它与厂区隔开。本来是供寄宿宾客休息之用,但已安排有专职花匠经管,无需老人家亲自操劳。我们在小洋楼读书时,花园大体上仍保持原有格局,有稀疏的树木和大片草坪,花圃种有不同季节开放的花儿。我最感兴趣的是那长长的紫藤架,每逢春天就吊满一串串紫色的和白色的花朵。我们喜欢坐在那粗壮的藤蔓上,当作秋千摇摇晃晃,顺便还可以带回几串刚开不久的紫藤花,央求母亲用鸡蛋、面粉调拌,蒸着或油炸着吃,那清香可口的滋味至今仍使我留恋。
杨老爷独居小楼,很少出外与人交往,但也有两位偶尔前来叙旧的挚友,系曾祖父以前的部属,不过都是幕僚之类的文士。他俩一人姓金,一人姓钱,都是随着曾祖父到芜湖的,曾经在面粉厂做过文员。曾祖父死后,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但没有回家养老,也许本来就无家可回,便结伴仍然留在芜湖。他们住在我家后面石板路边一座小屋里,好像公司定期给予若干生活补贴。他们为消磨时间,也可能是想多挣点钱,常在房前摆着桌椅,为过往行人代写书信、契约乃至讼状,附带也干些算命看相之类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儿。芜湖当年没有可通汽车的马路,这连贯城乡的漫长石板路便号称“十里长街”,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而附近不识字的农民又居多数,所以他们的生意不错,更加决心终老于此地。他们晚上得空时偶尔会来探望杨老爷,这三人有长期同僚之雅,许多往事可以共同回忆,所以友情老而弥笃。不过文人与武人在性格上有所差异,每逢旧历大年初一,金、钱两位必定抢在众人前面来我家拜年,以姓氏显示吉利的寓意,使我们全家老小为之高兴不已。由于他们是曾祖父用过的老人,所以祖父必定赶来西院亲自迎接,并且赠给厚重的红包,父亲也随侍在侧。我们小孩只能躲在房门边观礼,因为如果出去就要向他们磕头拜年,两老还得破费给我们压岁钱。相较之下杨老爷较少客套,平时很少来内宅,拜年也是选在末尾,匆匆赶来与祖父相互作揖而已。有些亲友认为他太呆板,不够殷勤热情,但祖父和父亲对他倒是更为尊敬。
直到抗战爆发,杨老爷始终留在我家。及至1946年我复员回家,已经看不见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听父母说是在芜湖沦陷前被子女接回桐城老家,以后就再未回过芜湖。
张校长离去以后,我又回襄垣小学,但却莫名其妙地跳了一级,与姑姑、姐姐、三哥一起读五年级。其实我的成绩并不好,除语文还差强人意外,数学几乎跟不上班。不过班主任冉老师对我颇为关怀,无非是因我在班上年龄最小。班上最大的同学20岁,比我大整整十岁,且已结婚生子,是一家商店老板的儿子,芜湖人称为“小开”,我们也都喊他“小开”。“小开”像大哥哥一样,对我们非常宽容,从不生气打斗,而且学习非常认真。冉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好像还没有毕业就随着华北学生救亡团体南下请愿并宣传抗日,于是留在芜湖教书。他家在河北农村,读的又是师范学校,不像有些南方年轻教师那样讲究穿着,一年到头都是那件旧蓝布长衫。不过课讲得确实很好,教学方法颇多创新,特别是充满爱国激情,作文题目经常跟抗日救亡有关,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向华北抗战前线战士致敬信》之类。正是由于这些年轻老师注入新的活力,校园才充满爱国救亡气氛。记得有一次在明伦堂讲坛上演出一个街道剧,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到医院慰问抗战伤兵的场面。这次我算是正式登上舞台,不过是演一个护士,没有任何台词,无非跟着大家高喊抗日口号而已。我们这些群众演员都很兴奋,仿佛当真在为抗战出力。但冉老师并非只热衷于做抗日宣传,他对我们的学业基础与品德修养也非常重视。他经常夸奖我的作文,记得有次我模仿某个作家写了一篇《马的故事》,冉老师竟推荐到《皖江日报》上发表。这或许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尽管是那么幼稚而又简短,但家里人都很高兴。唯独父亲不以为然,认为这无非是照葫芦画瓢,与张校长批评我滥用“时间比欧文思跑得还快”一样,因此我在家中没有得到任何犒赏。
我的另外一篇作文虽属独自创作,并且再次得到冉老师的好评,却几乎引起一场家庭风波。作文题目是《我的爷爷》,大意说我们这个大家庭原本非常和睦美满,自从祖父娶了姨太太以后,人际关系变得很复杂,亲情反而变得疏远了。冉老师又推荐给《皖江日报》,母亲大为高兴,认为我是她的代言人,但父亲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被祖父看见大发雷霆,立即跑到报纸编辑部把这篇作文要回来了。热心推动社会进步的冉老师当然有些失望,但也能理解父亲的难处,他鼓励我继续学习鲁迅,关心现实,批评邪恶,伸张正义。
由于子女过多而又忙于公司事务,父亲一般对我们的学习未作具体干预,至少是在客观上容许我们自由发展,特别是大哥,简直随心所欲。他爱画国画,就买上好宣纸和毛笔;他爱练武,就请师父并锻造武器;后来想考空军,也未遭任何阻挠。他对我们这些小萝卜头,表面似乎有点马虎,但绝非漠不关心。父母为我们订阅《小朋友》杂志,还买了很多开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如冰心的许多作品,乃至《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爱的教育》的中译本,让我们幼小的心灵得到爱、善、美的滋育。我由于住在父母隔壁,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他们卧室书橱上的休闲书籍全部都翻阅一遍。最感兴趣的是林纾译述的外国小说,如《三剑客》《茶花女》等等,虽然不能全懂,但许多情节都使我入迷。鲁迅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我看过好多遍,对我此后的性格、文风都有些影响。当然,坦率地说,我最入迷的还是小爷爷与大哥的私下藏书,他们两人住在东院楼上,享有更大的空间。爷爷从不上楼,父亲也懒得去,所以他们可以买许多武侠、神话书籍,如《彭公案》《施公案》《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火烧红莲寺》《封神榜》《西游记》等等,这些我都曾借来独自阅读,尽管也是似懂非懂。有段时间我经常沉溺于幻想之中,羡慕土行孙的土遁,更羡慕剑侠们的剑遁,一道白光就可以来去自如,上天入地,到任何自己乐意去的地方而不被家人发觉。当然最好是拥有孙悟空那样的筋斗云,一个跟头可以飞十万八千里。我也曾暗中“修炼”,干过一些荒诞不经的傻事,如磨碎铅笔成粉吞服“炼丹”,以为炼成以后可以口吐红光随风飘游;也曾把橄榄核含在口中睡觉,幻想能练成什么克敌制胜的神秘武器。幸好这些傻事没有酿成任何恶果,否则真会使父母遗憾终身。
相较之下,母亲尽管体弱多病,但对我学习的关心比父亲多一些,因为她与我在一起的时间多些。只要她的精神较好,就会教我练习写字或诵读一些浅显的诗词,如“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之类。到我年岁渐长,她就指导我背诵一些深一点的诗词,如杜甫、李白的诗,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我练字的字帖名《星录小楷》,全部是赵体,这是章氏家人的故乡情结,上面写的都是流传甚广的词,如李后主、李清照比较深沉委婉的作品,经过反复接触,也就自然而然地浸润于心灵。母亲有便秘的毛病,每逢坐马桶太久觉得无聊,就把我喊去背诵古典诗词,所以我暗中取笑为“马桶边的文化休闲”。但有些诗词就是这样逐渐融化成为我早年的文化积淀,尽管是那么浅薄。
小学时期,我是个非常内向的儿童,并且在文体活动方面显得十分低能。荡秋千我有惧高症,荡到半截就慌忙下来;毽子顶多只能踢十几个,不像哥哥姐姐那样偷、跳、环、剪,灵活自如,变化多端。其他如赛跑、跳高等,都比同龄人相差甚远,所以便逐渐失去应有的自信,产生比较严重的自卑感,而这种失落却在许多美梦中得到虚幻的弥补。这种病态的心理围绕我很久,直到成年以后还有若干潜在的影响。
三哥开诚虽然只比我大一岁多,却显得比较自信也懂事得多,并且还有一定的交际才能。我们同上六年级时,他居然与十来个同学自发地组织一个读书会,每隔两三周必在我家聚会,交流读书心得,地点仍是那座小洋楼的大餐间。他们慷慨地让我忝陪末座,但我总是耽溺在自己荒诞的幻想之中,已记不清他们究竟讨论什么问题。只记得最后一次聚会时,作为主席的老大哥程懋勤——那位扮演周瑜出尽风头的小帅哥,黯然神伤地说:“毕业以后,你们马上就要读中学,我却只能到商店当学徒。”原因很简单,家庭贫寒,难以供应孩子继续升学。他是多么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是襄垣小学的骄傲,也是我心目中的偶像,竟没有升读中学的机会。大家都为之惋惜,会场顿时陷于沉寂。我由此隐隐约约感到贫富差别,以及世道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