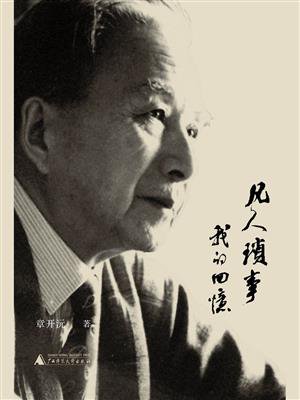逃难四川
“七七”事变以后,我与开诚顺利进入私立萃文中学。这是一所知名的教会中学,建立在风景如画的凤凰山上。由于离家较远,祖父又不让住读,便雇了一辆包月黄包车每天送接,过去那种上学边走边玩的乐趣一去不返。我非常羡慕小爷爷与大哥一人一辆自行车来去自如,但又拗不过祖父之命,只有规规矩矩与三哥并排坐在人力车上,被路人看得很不自在。后来淞沪战事迅速逆转,我们中途辍学,才从黄包车上解放出来,不必每天在大街上被过路人指指点点。
1937年秋冬之间,离开芜湖以前,父亲一定曾与祖父多次磋商,并且征求过上海二叔祖的意见。我记得全家做最后决定的那天下午,祖父端端正正坐在祖母卧室的床上,祖母也神情肃穆地坐在他身边。父母带领我们兄弟姐妹整整齐齐站成一排,恳求祖父母与我们一起迁往四川。但祖父执意留在芜湖,凛然而又略显悲凉地说:“国难当头,守住祖业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你们年轻,来日方长,应该为章家保留根苗。”父亲惶急之下,扑通跪在床前,我们不约而同一起跪下,再三恳求祖父母同行。但祖父早已拿定主意,断然宣布最后决定:全家分为三批,小爷爷与大哥都已成年,由凹山铁矿的文矿师带往贵阳(他的老家),继续求学或就业;父母带领高龄外婆及我们其他兄弟姐妹,前往四川重庆避难;祖父母、姨太太及其两个女儿暂时留在芜湖,如形势实在危急,再设法迁居上海法租界,由二叔祖事先代租住宅。
平时冷冷清清索然寡味的祖母卧室,突然显得温馨起来,增添了怜爱的亲情,也增添了恳挚的依恋,而这正是老宅过去所缺乏的思想与情感的坦率交流。国破家亡,生离死别,仿佛永远定格在这间房里。
章家两个成年壮丁最先离开这座老宅。文矿师曾留学日本,在凹山铁矿工作多年,与父亲已有深厚交谊,加之为人忠厚老实,所以长辈们对他都很放心。到达贵州以后,两人都继续读书,小爷爷后来就读于西南联大,大哥按自己的兴趣进了国立艺专。
接着是我们一家八口大队伍出发,先乘公司大木船,循青弋江直接驶往长江边的太古码头。逃难的人已经与日俱增,我们动手太迟,所以买不到正式舱位,只好通过轮船公司买办设法安排在头等舱的大餐厅,因为我们人数较多,携带的行李杂物更多,只能这样权宜处理。
到达码头后,只见人山人海,我们行李太多,几乎无法上船。幸好送行的技工郑怀德(绰号小侉子)武功高强,敏捷灵活,一手携物,一手攀援,不断从木船上把大小十几件行李全部送上轮船顶层的大餐间,然后又帮助我们全家老小从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挣扎出来,安全登上轮船。如果没有这样得力的送行者,我们肯定挤不上轮船。
“小侉子”其实不小,他与我父亲恰好同龄,原本是被父母遗弃的婴儿,也可能与父母在逃荒或战乱中离散,被我曾祖父在山东出差途中发现并收养。维藩公见他孤苦无依,饥寒交迫,即使在贫困中仍然显出几分聪慧,便带回来与当时也在童年的父亲做伴。父亲是独生子,两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都喊他“小侉子”,其实他姓郑,曾祖父为他取名怀德。长大后到上海机械厂做学徒,学习认真,接受能力很强,简直是学一行会一行,回芜湖后成为面粉厂的顶尖技工,拿得下许多工种,已经达到技术员水平。他在业余还练就一身武功,能同时对付三五个人的攻击。大哥对他仰慕之至,执意向他学武。虽然没有正式师徒名分,他却尽心尽力传授,除几套拳法外,还教铁砂掌以及轻功等等,使大哥终身受益无穷。“小侉子”这身过硬武功,在送我们上船之际正好发挥作用。临别时父亲感激不已,两人执手叙谈,怀德满口答应代为侍奉“老爷”(指祖父),保证家人健康与安全,随即匆匆告别上岸,因为他也要照顾自己的小家。
客轮起碇后,缓缓行驶在宽阔的江上。由于已是深秋,江水由昏黄变为清亮,倒映着蓝天白云,江鸥时时成群掠过,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众多旅客拥挤在栏杆旁边,恋恋不舍眺望着逐渐变得模糊的芜湖码头。大人们感慨万千,不知何时才能返回故乡,而前途则是异常渺茫。小孩倒是无忧无虑,尽情在甲板上追逐游戏。我素来不爱热闹,又不大合群,独自凭栏远眺,沉浸在各种稀奇古怪的幻想之中。紧挨着我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好像是情侣,也可能就是新婚夫妇,伏在栏杆上悄悄絮语。他们是从上海上船,衣着入时,谈吐文雅。那女士的长发随风轻拂着我的脸,我好像又回到母亲与奶妈爱抚的童稚时期。我丝毫没有注意他们在谈些什么,他们也似乎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但不知为什么,那女的一句话却久久留在我的模糊记忆中。她轻轻叹息说:“我们总算经过人生大事了,就算死了也没有什么。”我不懂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因为当时还不具备理解成人感悟的认知能力。但我以后常常想,难道这就是这对时髦青年的人生观或爱情观吗?在那烽火漫天硝烟遍地的岁月,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身边这个傻乎乎的孩子竟为他们的一句话而苦苦思索。
从上海出发的大客轮到达汉口就停泊了,因为长江上游水浅,不能继续前行。我们寄住在祖父原先住过的萃仁旅馆,仍然是益新公司常年包租的那个大套间,正好可以容纳八口人。环境倒也闹中有静,早餐由茶房从外面买回,中晚餐则是附近餐馆送来的“合饭”,即必须预订的四菜一汤套餐。由于是多年老客户,饭菜味美可口,比老家那种多年如一的单调伙食强得多。我们小孩依然嬉戏如常,但父母却因为买不到去川船票而日益焦急。平素极为温和的父亲竟变得暴躁起来,害得笨嘴拙舌的五弟只因为讲错一句话,就莫名其妙地挨了一巴掌,这是我们家极为罕见的事例。当然也可以理解,一家八口每天食宿开销甚大,如果老是滞留武汉,坐吃山空不知如何了局。母亲经常劝慰父亲,口头禅仍然是那句话:“天无绝人之路。”
可能上天受到感动,母亲的话果真验证了。父亲有天在街上竟然与贾伯涛不期而遇,难兄难弟久别重逢,分外高兴。贾伯涛以抗战为重,又复归军旅,虽然不算是春风得意,但仍不失儒将风度。听说我们买不到去川船票,立即答应设法代购,并且请我们全家在萃仁旅馆附近的璇宫饭店吃大餐(西餐)。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不知如何摆弄刀叉,只好用汤匙舀着或干脆用手抓着吃。贾伯涛与父亲有谈不完的话,他现在还没有什么正经差使,所以有足够的时间与好友畅聊。但他确实有点门路,不久便派人送来8张船票,是民生公司“民贵轮”三等舱的一间包房。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尽管这间房只有6张床,小孩只能挤着睡。
不知道父亲是怎样把那十几件大小行李送上船的,也可能是贾伯涛派士兵事先搬上去的,反正我们都是空着手上船,而且不像芜湖出发时那么拥挤,因为毕竟是小船,乘客少得多。开船以后一路平安无事,没有碰上日本飞机轰炸,也没有发生触礁搁浅之类事故。只是船小人多非常拥挤,连甲板上都睡满人。我们只好整天枯坐在房间里,连看看三峡风景也难,只能听听外婆与母亲讲些过去旅川故事。轮船曾在万县停泊一晚,母亲执意要上岸逛逛,可能这也是她童年到过的地方吧。除外婆留下看守行李,父母带领我们匆匆上岸,就近在临江大街上闲逛。没想到上岸乘客甚多,加上又有大量难民滞留万县,所以夜市非常热闹,来往游客把大街挤得水泄不通。父亲唯恐儿女有所闪失,不时叮嘱我们互相牵手紧随。大家玩得非常高兴,不料母亲却走散了,直到要回船时才发觉。父亲连声直呼“毓青”,我们也齐声大叫妈妈,但找来找去始终未见母亲踪影。直至催客回船的汽笛响了几遍,我们才凄凄惶惶踏上趸船与轮船之间的跳板。不料一推房门,母亲正坐着与外婆谈笑风生呢!我们还以为是做梦,一起向她扑去。母亲与外婆看到我们进房那种狼狈样子,不禁都大笑起来。原来我们在街上寻找她的时候,她也正在寻找我们,只是由于游人太多,声音嘈杂,彼此都错过了相遇的机会。母亲当时已怀孕临产,唯恐被行人或车辆撞倒,好在还会说四川话,便叫来一个滑竿,径直返回轮船舱房,没想到却比我们先回来了。母亲嗔怪父亲说:“我说过天无绝人之路吧,这一带我很熟悉,要你急什么?”
但就在这天深夜,母亲生产了,我们在睡梦中一点都不知道。因为船长非常热心,临时让出一间船员卧室作为产房,还物色一位医护人员照顾母亲分娩。分娩出乎意料地顺利,生出的是个模样可爱的男孩,按排行应该是八宝(七宝已在抗战前夭折)。船长笑着说:“就以船名作为名字吧!以后再坐我们的船,永远可以免票。”大家一致同意,喜笑颜开,只有父亲依然皱着眉头,不知道到重庆后如何安排这九口之家的生计。
船到重庆朝天门码头时,五姨爹已带人在码头迎接。他与姨妈在抗战前一年奉命来到重庆,在委员长行辕挂了一个少将参议的军衔,但他无需天天上班,也从来不穿军服,主要还是靠行医(中医)维持比较优裕的生活。姨妈也在妇女委员会挂个委员名号,不过每月只能领一点车马费,主要工作还是主持家务并照管两个小表弟的生活与学习。他们事先已为我们在城里租好住宅,有两间卧室与一个堂屋(客厅),这就比那些在四川无亲无故的逃难者强得多。姨父母自己租住的是一栋两层楼房,相当宽敞而且还有天井,但外婆嫌他们每天客来客往,无谓应酬太多,执意与我们挤在一起,结果她只能住在临近大门的堂屋里,因为里面两间卧室实在太狭窄。不过老人家毕竟习惯了清苦生活,像这样能够有自己的空间,并且离两个女儿住处很近,经常可以相互走动,还有八个孙儿女可以绕膝承欢,是战乱期间难得的平顺晚景。她得闲偶尔喝点小酒,无需另备酒菜,也不要他人作陪,无非是独自小酌消闲而已。这是她在外公逝世后养成的生活习惯,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重庆是一个风景雄奇秀美的山城,又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埠,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机会出去逛逛,只能在住宅院内玩耍。为了维持全家生计,五姨爹为父亲在师管区补充团谋了一个上尉军需差使,薪津微薄,工作却相当繁重,经常要随同输送稍经训练的新兵前往前线部队。当时重庆求职难民极多,能够有这份工作,全家已经够满足了。但没过多久,一系列灾难就突然袭来。首先是我与六弟开运同时病倒,为了节省医药费,五姨爹亲自前来诊治,断定为副伤寒,立即精心开方配制中药。我连吃几副以后迅速好转,但六弟却没有起色,加上又缺少必要营养,瘦成皮包骨,没几天便凄然逝去,死时还不满八岁。开运从小就很可爱,他属龙且有异禀,从不食荤腥,即所谓胎里素,但却长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浓眉大眼,所以稍知星相的亲友,都说这孩子将来可能成大富贵。但我俩同时生病他却先死了,姐姐不知听谁说过,他属龙,我属虎,龙虎相克,我的命强,所以侥幸活下来了。虽然母亲斥之为胡说八道,但却从此在我的心中留下阴影,弟弟的死常使我暗中愧疚——他那么善良可爱竟然夭折,我这样其貌不扬而又性格乖僻,却偏偏存活下来。
把六弟用薄木棺埋葬以后,没有多久外婆又猝然病逝。原来就在我与开运同时病倒期间,外婆也因为心血管毛病中风瘫痪。虽然还能说话,但已日见昏聩,并且只能整日卧床。五姨爹虽然潜心治疗,但始终没有起色。家中一老二小三个病人,产后不久的母亲之操劳辛苦可想而知,幸好姐姐、三哥比较懂事,能够帮点小忙。外婆死后,父亲从外地赶回,与五姨爹共同操办丧事。国难期间,一切从简,所以并未惊动在渝任何亲友。五姨爹颇有军人的豪爽,父亲写灵牌时,因记不清外婆的封典是从一品还是二品,五姨爹竟拿过笔来,疾书“前清一品夫人”,当然不会有任何人注意这一细节。整个丧事也很草草,无非请两位僧人诵经祈求冥福。外婆年逾八十,已属高寿兼全福,所以大家并非十分悲痛。但是外婆那慈祥而又随和的形象,却深深留在我们心中。
记得外婆是1936年迁居芜湖的,此前一直在南京,住在五姨妈家,两个表弟都是她一手带大。那年姨爹奉命,全家进川,外婆因年事已高便来我家奉养。祖父对这位年长的亲家母非常敬重,把她安排在“小公馆”独自颐养,并派得力女仆照料日常生活。其实外婆身体相当健壮,生活能够自理,有时还送些可口菜肴给我们解馋。据说安庆人善于卤菜,女儿出嫁都以用过多年的卤锅作为随身陪嫁。外婆的卤艺堪称一绝,无论什么鸡杂鸭杂乃至翅爪,经她一卤都特别香烂鲜美。她每天都免不了自斟自酌,所以经常要卤点下酒小菜。我们为她补充卤菜原料,时时掏出鸽蛋送去。有次大哥居然乘黑夜爬上鸽棚,抓了几只鸽子送给外婆。外婆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从来不问这些“猎品”是从哪里得来。倒是母亲害怕祖父生气,又怕有损娘家面子,坚决制止我们的不良行为,另托厨工代购卤菜原料送去。
外婆身材高大,面貌端庄而又略显清奇,高鼻梁,凹眼眶,皮肤白中透红,有点像西方人。她虽然也裹过脚,但不算很小,所以来去自如,行动敏捷,不需别人搀扶。她性格爽朗,快人快语,直来直去,成天乐呵呵的,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夸奖亲家老太有人缘。其实她亦曾多遇不幸,丈夫过早去世,又未留下多少遗产,孤儿寡母,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把四个小儿女带大。不料本应成为家庭顶梁柱的长子突然疯了,媳妇携二子返回苏州娘家,幸好两个女儿出嫁后经济状况较佳。大舅由我祖父慨然承诺收养。八舅(次子)品学兼优,全靠自己挣点稿费在大学深造。外婆自己常年住在南京五姨妈家,共享天伦之乐。虽然经济上无从自立,但她始终保持大家风范,不卑不亢,慈祥谦和,绝不巴结他人,毫无寄人篱下之感。她原本很器重五姨爹,因为他年轻时曾经参与国民革命,颇思有所进取。但自从国民党定都南京之后,高官厚禄使他逐渐蜕变,沾染许多官场恶习,从而丈母娘与女婿之间感情逐渐疏隔,所以她宁愿与我们同甘共苦,安于贫寒。虽然外婆未能与我们一同度过抗战的艰难岁月,但她的慈爱与风范却随时随地滋润着我们这些浪迹天涯的赤子之心。
刚把外婆的丧事料理完毕,我突然患了俗称“走马牙疳”的恶疾。所谓“走马”就是形容其来势凶猛,足以致人于死,其实就是医学书籍上的急性牙周炎或牙窦炎。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所以突然恶性发作,脸的左边肿胀得像熟透的柿子,红透发亮,热烫疼痛,连左眼都无法睁开。幸好父亲尚未出差,赶紧送我到朝天门一家私人牙科诊所医治,并且就在附近小旅馆租间房,让姐姐陪我就近治疗。随后,他就把全家搬到重庆乡下去了,因为城内房租太贵,生活费用高昂,只有住在乡下才能勉强维持全家生计。
为我治牙的小诊所,也是逃难的下江人开的。院长姓陈,是上海人。给我治牙的医生姓孙,是南京人,亦即院长的至亲妻弟。孙医生温文尔雅,不仅治疗的手法轻柔,温言慰解,还主动借给我几本公案小说,让我闲阅解闷,耐心就医。但未隔多久,他就猝然病故,听说是半夜心肌梗死,可能是工作过于繁重所致。于是院长只好亲自为我治疗。他是个水平很高的资深大夫,身躯高大壮实,手术时几乎是压在我的身上操作,使我憋得几乎出不了气。我的牙病由于就医过迟,牙龈内部乃至左腮边角都已灌脓,所以必须开刀,从外而内彻底清除已经腐烂的牙根残株。手术相当复杂而又耗费时间,虽已注射麻醉剂,但仍疼痛难熬。我自幼习惯于忍耐,咬紧牙关,默不出声。院长劝我叫嚷,至少也要哼唧几声,因为我的脸已经涨成猪肝色,显得异常可怕。其实他自己也精疲力竭,每次做完手术都是大汗淋漓,瘫坐在靠椅上,可见其用力之多且不敢有任何闪失。院长太忙了,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得亲自照料,不像孙医生那样从容不迫,和蔼可亲,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关怀。病友们都盛赞他的医术高明,这当然是我的运气好,否则“走马牙疳”早就把我这条小命了结了。当时的医疗设备和药物的缺乏,是现今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寄宿旅舍是我首次独自接触社会。姐姐本来想一直陪护,但却为一件小事舍我而去。当时旅馆来往客人确实很复杂,多数是逃难寄居的,也有经商、求职的,乃至赌博、嫖妓的,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天我看病回来经过大厅,突然被一个年轻军官叫住。他自称是某补充团的连长,送新兵上前线回来,临时在这里休整两天。因为觉得我天真可爱,所以找来聊聊。我不知道他想谈什么,只好随意应对,不料他很快就塞给我一包糖,并将一张叠成方胜状的信纸托我交给姐姐。我高高兴兴回房把信交给姐姐,她打开看了一下气得满脸通红,大声斥责我:“就是嘴馋,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并且把信纸撕得粉碎,又夺过那包糖摔到窗外。这是她第一次向我发那么大的脾气,平时对我一句重话也未说过。我知道自己犯了大错,不该接过那封信与那包糖,但究竟错在哪里还是不明白。姐姐已经有十四五岁,她知道如何护卫自己的人身安全,但又不愿对我明说,因为说了我也不懂,所以为我稍作安排就回家去了。此后,我只好每天独自去诊所看病换药,回来就关起门来看孙医生借给我的那几本公案小说,再也不敢出去闲逛,更不敢与陌生人交谈,唯恐又惹来什么预料不到的灾难。不过手术很成功,伤口脓血逐渐减少,疼痛也减退很多,所以我内心还是很平静的。
当时旅馆长住客人习惯“包伙”,因为比较省钱又省事。但进餐没有固定座位,凑足八个人便可开始吃饭。最初我是随意加入一桌,反正吃饱了事。没想到已有好心人士暗中注意到我这孤零零的病孩。不久,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旅客主动找我攀谈,因为听我说话有芜湖口音,而她也是从芜湖逃难来的。看到她那善良而又略带凄楚的神情,而且还带着比我略小的一对儿女,我立刻把姐姐临走的训示忘在一边,很自然地与她交谈起来。她问我是哪家的孩子,听说我父亲叫章学海,她竟惊叫起来:“我们还有亲戚关系呢!”原来我们章家同族有房亲戚住在芜湖城里,名字叫作章增辉(字子明),他的父亲(乃振)是维藩公在新疆平叛时解救出来的被俘幼童,后来随同我家来到芜湖,成年后在城内安家立业。增辉辈分比我父亲高,但年相若也,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以后虽然自立门户,但仍往来频繁,情同一家。增辉的夫人叫谢瑶芝,是芜湖本地人,就是眼前这位热心女士的表姐。她自报姓名为李玉屏,原来在芜湖教中学,丈夫死得早,所以独自带两个孩子逃难来渝,暂时在这个旅馆寄宿。举目无亲的她,意外地遇见我非常高兴,从此一日三餐必与我同坐一桌,我也因为有一个同乡长辈的就近关照而欢喜。两个孩子年龄又与我相近,只是男孩似乎不大乐意与我同桌吃饭,也不与我搭讪,可能是因为我脸上贴了一大块纱布,模样有点古怪,也可能不愿与我分享他的母爱。但小妹对我毫无嫌弃,吃饭总要挨着我坐,并且常邀请我到她们房间玩,这样便化解了我独居旅舍的孤寂,甚至或多或少还感受到若干家庭的温馨。
晚餐后无处可去,因为地处朝天门码头,情况复杂,治安很差,我们往往只有围坐叙谈芜湖往事。我在老家礼教规矩很严,每逢她们母女洗脚,必定立即告辞。李老师视我如家人,笑着说:“小孩无需避讳。”有时还夸奖我:“到底是大户人家的孩子,自幼知书达礼。”我不禁心中暗笑,因为叔祖母与母亲老是批评章家门风不好。当时我还不懂礼仪与门风并不是一回事。
没过几天,李老师喜滋滋地告诉我一个大好消息。教育部决定在离重庆很近的江津建立国立第九中学,主要是招收安徽沦陷区的难民学生。她已经应聘担任第九中学教务处注册组职员,即将参与正式招生工作,并且要我尽快告诉父母,让兄弟姐妹都来报考九中,她可以负责代为办理一切手续。由于家中经济困窘,到重庆以后,我们一直处于失学状态,连升学的愿望都很淡薄。现在遇此良机,自然不会错过,我连忙答应一定到九中读书。李老师随即带着儿女前往江津,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她们一家走后,我更感觉冷清,幸好伤口已基本愈合,无需天天到诊所治疗。姨妈闻讯,立即把我接到她家,既节省旅馆费用,又可以亲切照顾。加上还有两个表弟做伴,我心情更加愉快。到诊所换过几次纱布以后,伤口迅速愈合,再无任何脓血渗出,姨妈这才放心让我回家。由于有二十多里路程,还为我雇了一匹川马,请马夫送我前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骑马远行,好在川马矮壮温驯,特别善于行走山路,骑在马背上非常平稳安全。那天风和日丽,缓缓行在群山丛林溪流之间,又有能说会道的马夫逗笑,真是其乐融融,不知不觉就到了我家所在的曾家花园。这是一家大绅粮
 的府第,主人早已迁入重庆市内,师管区补充团租来作为家属宿舍,住户多是下江逃难来川者。
的府第,主人早已迁入重庆市内,师管区补充团租来作为家属宿舍,住户多是下江逃难来川者。
母亲看见我病愈平安归来,自然非常高兴,但又不禁苦笑说:“伯伯(指父亲)这个月的薪水被你一个人花光了。”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不知如何回应,内心感到异常歉疚。幸好小弟弟非常可爱,我常爱抱着他东走西逛,邻居们也喜欢他,一逗他就甜甜地笑。他的存在为全家的贫寒生活带来幸福与希望,并且以童真的笑颜装点着这荒野破败的整个大院。但不幸的是,我回来才几天,这个幼小的生命便匆匆结束了。
那是一个初秋的傍晚,母亲因为产后一直劳累并且缺乏营养,躺在床上稍作休息。姐姐与开诚、开永忙于拾柴火做饭,让我抱小弟随意走走。由于我刚回来,对大院环境不熟,偶然走进房东供祖宗牌位的后厅。庭院里林木茂盛,室内又极为阴暗,小弟惊恐大哭起来。我急忙抱他回家,母亲抚慰甚久才让婴儿睡着。但晚饭后母亲发现他的小脸烧得通红,喂了点阿司匹林仍未见退烧。有些邻居说,可能后院无人住,阴气太重,让婴儿受了惊吓,应该赶快“叫魂”。我们虽知这是迷信,但也无可奈何地大声叫喊:“民贵回来呀!”“民贵回来了!”但民贵的病情愈来愈糟,呼吸困难,双眼紧闭,嘴唇发紫,口角不断溢出白沫。后来,我们孩子们都困极睡着了,只有母亲抱着小弟坐在床上,默默承受着全部焦急与凄苦。
次日凌晨,我们被母亲哭声惊醒,原来小弟已经咽气了。这荒郊野外哪里找得到医生;父亲出差在外,即使有电话也无从联系,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幼小者最终死亡。母亲强忍哭泣,用一件尚未穿过的绸棉袄把小弟包得严严实实。我们都围着她坐下,大家都没有哭也没有流泪,这就是我们为小弟的最后送别。
天亮了,母亲托邻居买来简易单薄木匣,把小弟草草埋葬在附近山坡上。我的内心充满自责,如果我没有回家,没有把小弟抱到后院无人大厅,也许他不会这样夭折。但我始终缄口无言,因为全家都沉浸在深沉悲痛之中,谁也不愿意讲话。母亲找来一块平滑的木板,在上面贴了张白纸,用颤抖的手写下“亡人章民贵之位”七个字,放在后院大厅曾氏亡灵牌位之间。我们轮流上香并鞠躬,抒发无尽的哀思。民贵啊,民贵,那“民贵”号轮船还等待着你上船哪!
家中已近乎山穷水尽。没过几天,父亲匆匆赶回,也只能叹息摇头而已。他肯定比我更加自责,因为是一家之长,全家九口(船上增加一口,即民贵)不过半年即先后死去三口,如今只剩六人(大哥在贵州,不算在内),怎能不悲痛万分。不过当我转告国立九中招生消息时,父亲的眼睛突然一亮,紧锁的眉头也略显舒展。他在芜湖宗亲章子明家见过李玉屏,认为她为人正派,厚道可靠。九中招生对我们来说,再一次证实妈妈的口头禅:“天无绝人之路”,夸大一点说真是如同绝处逢生。把孩子们全部送到江津读书,几乎无需再作任何考量,因为这是我们全家的唯一出路。
没过几天,母亲为我们收拾好全部行李,父亲亲自送我们乘小轮到江津,然后又换乘木船过江到德感坝九中校部,把我们交托给李玉屏。千叮万嘱之后便匆匆回重庆去了,因为又要送新兵上前线。
这是我们独自在外地读书与生活的开始,从此不仅离别了老家,而且离别了关系最为亲密的父母。就我个人而言,从此整整八年未能再与父母见面。因为父亲回重庆不久接到时任赣南师管区司令贾伯涛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担任军需主任,此后父母很快就离开四川前往江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