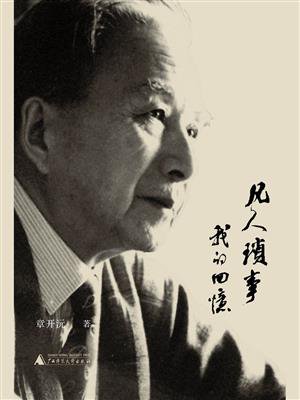国立九中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已经估计到战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学校布局上也有相应安排。对大学采取整体西迁方针,对中等学校则是在后方安全区建立三十余所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大批流亡学生,并全部实行“贷金”资助,使之不致长期辍学。当时,主要收容安徽沦陷区流亡学生的有两所,一是设于湖南的国立八中,一是设于四川的国立九中。唐德刚常说我是他的老同学,其实他在八中,我在九中,应属国立中学安徽学生的泛指。他读高中时我还在读初中,所以我尊称他为“大学长”。
据九中校友李洪山《西渡漫记》忆述:“(1938年)9月26日,陈访先就任国立安徽二中(后改名“九中”)校长,勘定江津县德感坝为校址。全校分设高中、初中、师范、女中四部,共42个班,计有学生一千六百余人。复设校本部统筹学校行政事宜。此外,设附属小学一所,以为师范生实习之用。”其实,陈访先只是挂名校长,因为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主要工作地点在重庆。真正主持全盘校务的是校本部教务主任兼高中分部主任邓季宣,他在第二年就正式接任校长。
我与二姐开明、三哥开诚就属于这一千六百余第一批九中学生。五弟开永先读附小,然后才升入初中部。不过由于入学测试编班,姐姐与三哥分在初一上班,我分在初一下班,此后只能分别独立上学了。当时,像我们这样兄弟姐妹成批进入九中的很多,仅与我同年级的就有杨怀谦、杨怀让,潘祖舜、潘祖禹(长兄潘祖尧读高中),周承超、周承铮,汪积畬、汪积威等。据说兄弟姐妹同时进入九中为数最多的,是安庆老字号胡玉美酱园的庆字辈学生。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庆燕,他以反串《雷雨》女主角繁漪而出名,其余兄弟以后亦多为演艺界名人。
德感坝在江津县城对面(北岸),隔着一段水流湍急的长江(当地称川江),靠小木船摆渡来往。川东多山,山间平地称坝。德感坝是面积较大的一块平地,而德感场则是此坝的中心集镇。它与二沱渡船码头相对,在汛期亦成季节性渡口。《西渡漫记》云:“德感场主街呈丁字状,横长的是德感街,直短的是斗套街。人们下船后跋涉一段沙滩,通过沿江的牌坊街拐进斗套街。由斗套街穿过东头的石牌坊走到西头,即与德感街垂直交接。按照国立九中1945年秋季机构调整后的布局,从这个丁字口向南数过去,依次是附小、校本部、女中分校、高二分校、初中分校(偏向西南),向北只有高一分校。”作者入学很迟,据我自己回忆,九中从建校开始,总体布局大体就是如此。不过当时初中分校一分为三,分别设在不同地点的三个祠堂,我最初进的是初二分校,设在云庄祠。三哥开诚原来与我同一分校,后来升高中后我直接搬进高一分校,开诚却进入黄荆街三分校,而开明则始终住在条件最好的女子分部。校本部与女子分校都在德感场镇上,离人口比较密集的德感街最近,借用的是当地士绅兴建已久的至善图书馆。该馆原来是一座颇具规模的道观,为了纪念道观的创始者贾至善(绵阳人,法号太玄),图书馆遂以“至善”命名,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与地名“德感”相呼应。此馆占地五百平方米,四面均有围墙环绕,建筑格局合理,园林景观清幽,是比较理想的办学地点。当年本地士绅能够集资购书,利用道观建立大型公共图书馆,现今又能以大局为重,慷慨大度地将此馆借给国立九中无偿使用,可见当地精英人士的见识非凡,亦可见江津文风之盛。离德感坝不远,就是当年著名诗人吴芳吉的故居,早已建成纪念馆,尤可说明当地民众对文化知识与优秀人才的尊重。九中能择地于此,实在是我们这些学生的福气。
关于初二分校的校址,《西渡漫记》亦有所描述:“云庄祠高高耸立在官山坡上,进祠堂要爬上一段陡石阶,它的内外两道大门都是朝南。祠堂作为办公室与宿舍用。祠堂西有面积不算小的操场,比周围建筑群低一至三米,是同学们使用原始工具一锄一锄挖出来的。通过操场拐北拾级而上,有马蹄形呈梯状排列的一组茅草棚屋。马蹄的中部是教室,教室尽西头有小号兵住房,西部是理化实验室。教室之东有几间也是草棚的厨房和食堂。”把慎终怀远供奉列祖列宗的祠堂提供给外省沦陷区流亡学生办学,这是四川人的宽厚仁慈,对我们这些小难民来说则是大恩大德。九中其他几处分校,除女生分部外,情况大多也是如此,这要涉及当地多少宗族成员,特别是其上层人物的理解与承诺,所以我至今仍把四川视为第二故乡,对四川广大父老乡亲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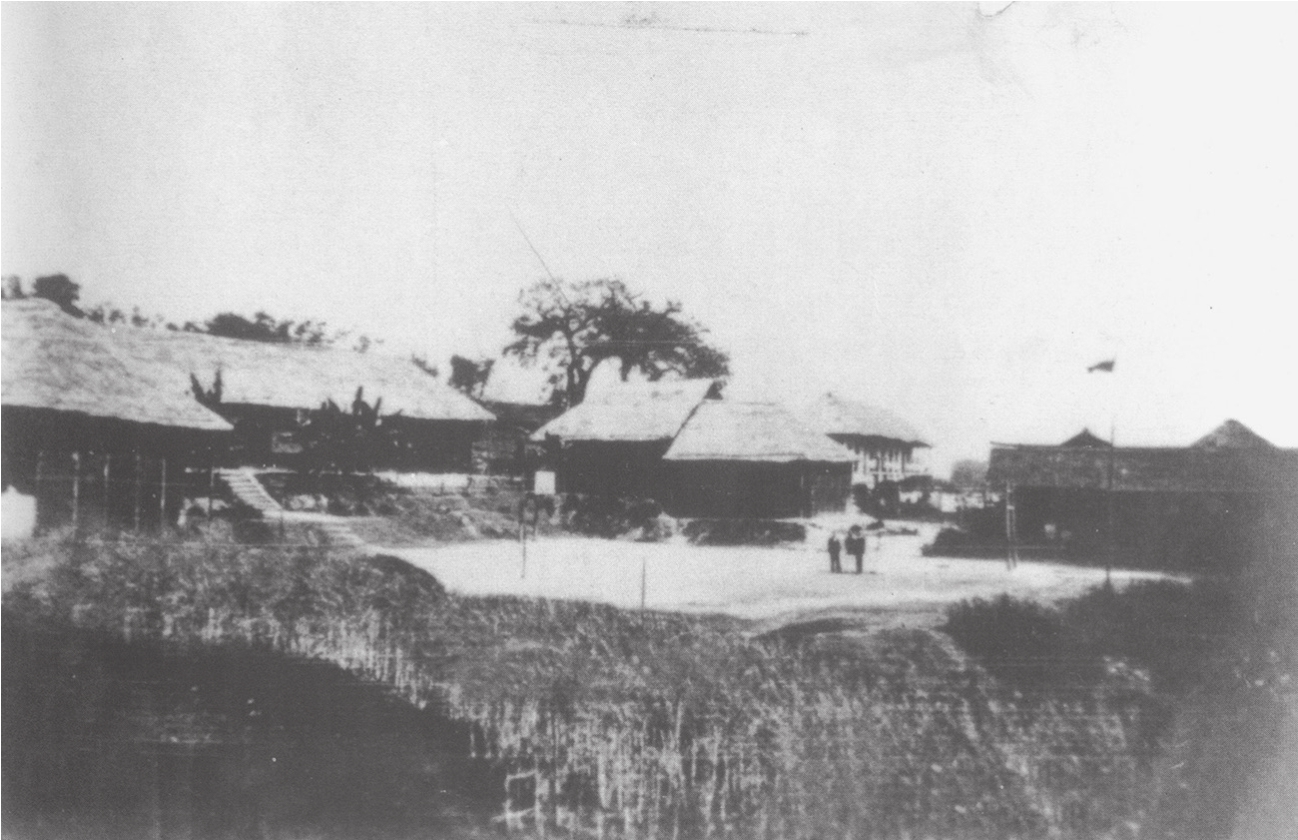
图7 1938—1940年间曾学习与住宿的云庄祠
我在云庄祠生活两年半,从初一读到初中毕业,都是住在祠堂里面。对于《西渡漫记》所说的“旧屋窳败,时虞倾圮,透雨漏风”等“窘境”,我却了无印象。可能是作者1945年以后才转学到九中,老宅难免有所损坏。作为这些祠堂的第一批住读生,我的感觉倒是这些祠堂建筑相当宏伟坚固。两年半中我的卧室曾有多次搬迁,楼上楼下、门边后进都曾住过,从未发现“透风漏雨”。当然我并不欢喜这种居住环境,因为很容易想起老家那大而无当的阴暗老屋。但比起那些到处漂泊风餐露宿的流浪者,已经是太幸福了。作为教室的茅棚,诚然简陋,但毕竟是新盖的整洁竹篱茅舍,不仅散发出谷草与泥土的清香,而且明亮通风,课桌板凳也是崭新的。在那烽火连天的苦难岁月,简直如同世外桃源,使我乐而不思离蜀。
不过睡在祠堂的房屋里,晚上确实有阴森森的感觉。关于云庄祠所在的官山坡,《西渡漫记》也有一段《聊斋》体的文字记述:“官山坡本是无主的乱葬岗,伤兵医院在祠堂的附近,有官兵死亡便抬来埋在坡上。夜间阴风阵阵,磷火点点。胆小的同学因怕鬼而憋尿,翌日翻晒被褥而遭人嘲弄,不算是新闻。”“官山”原名可能就是“棺山”,祠堂周围,特别是大门对面的山坡,到处是体量不等的荒坟。就我回忆所及,1940年以前,也就是我离开云庄祠以前,还看不到牺牲士兵的坟。也许到抗战后期,日军不断进逼,战线离重庆越来越近,国民党军队伤亡日众,这才出现伤兵死亡就地安葬的情况。
我们虽然与荒坟为邻,却丝毫没有人鬼杂处之感。我们常在课余或假日躺在野草丛生的坟堆上晒太阳,抓虫斗草或聊天。特别是在冬天,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新鲜的空气里散发着缕缕草叶芳香,那种舒适的感觉可能胜过现今冬天到夏威夷或三亚晒太阳。不过夕阳西下我们必定匆匆回到卧室,因为户外过于荒凉,寒气犹如阴气,确实令人皮肤紧缩。至于《西渡漫记》说有同学因怕鬼憋尿而弄湿被褥,以致被同学嘲弄,那恐怕也是1945年以后的情况。其实读初一下时,我也曾多次尿湿被褥并被同学发现,但那并非怕鬼,而是本来就有尿床毛病。同学发现后,不仅没有嘲笑,反而帮助我翻晒,并且告诉开明,让她用土方(猪尿泡塞糯米煨汤)为我治疗。说也奇怪,不久我的尿床毛病就断根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同学对我更多的是关切与帮助,危难艰困之际往往更显示出人性的温暖。最近,我在云庄祠的同窗好友汪耕(即汪积威)院士来信说我俩“情胜手足”,当时情况确实如此。因为他与哥哥积畬,我与哥哥开诚,亲密程度都赶不上我们这种异姓兄弟,朝夕相处,相依为命。
从深宅大院到竹篱茅舍,从父母呵护到孤身流离,真是早年人生的巨变!但由于年龄尚小而可塑性比较大,所以这一巨变并未引发我多少情感波涛,也没有造成任何心灵创伤。谢天谢地,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贫困、闭塞但却充满人性温暖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