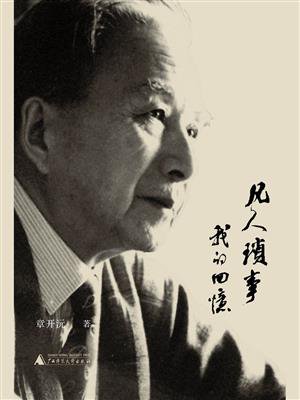再次开除
学校没有对此次武斗作任何处理,仿佛是装聋作哑,而最终受到严厉处分的,竟然又是我这个循规蹈矩,从来不爱惹是生非的弱者。此事我至今仍然难以索解。
故事可能要从我与杨教官之间的关系说起。他是江苏人,出于地域情结,曾对我这个来自江南的幼稚学生给予关切,平时主动找我说说笑笑。有次上世界经济史课,刚下课他就跑进来拿起我的笔记本,当着杨荣国老师的面,表扬我听课最为认真,笔记详尽而且工整,号召全班向我学习。我最害怕被表扬,因为从来不愿成为众人目光关注的焦点。我低头保持沉默,唯恐他逐页翻阅我的笔记本。因为我听课并非十分专心,有时爱在课堂上画点漫画,其中就有杨老师的肖像,寥寥几笔,特征俱显,颇为传神。幸好教官随手就将笔记本交还,并且又着实夸奖一番,真使我受宠若惊,内心有愧。
但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因为他每天早晨催我们起床,总是从女生宿舍开始,一边吹哨子,一边掀被子。有好事者通过几位女同学了解到,他最爱掀的就是一个江浙籍女生的被子,而且还有若干不雅言行。女生都讨厌他,但又不敢公开揭露。男生中间很快就传播开来,大家对他原来的好感顿时消失,认为他既是军人又是老师,品行却如此低劣。此事本来与我无关,因为自己情商发育较迟,尚不知恋爱究竟为何事,当然也不愿得罪直接管理学生的杨教官。但不知什么原因,也可能获知我在国立九中曾有前科,他对我的态度陡然转变,经常挑剔我的“毛病”。有次上早操,他巡视我们立正姿势,认为我双腿不够挺直,猛地从背后踹我一脚,用力很大,我毫无防备,几乎被踢倒在地。我极为愤怒,大骂他粗野蛮横,他又挥拳想打我,但被好些同学厉声喝止。我在气急之下公开指责他行为不端,根本不够教官资格。闻刚等好友也为我助威。双方愈吵愈烈,校方行政人员只能出面缓和紧张形势,草草结束早操。
此后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校方找我谈话,大家都以为此次事件已经不了了之,我仍然充分享受课余阅读、遨游之乐。但在五月中旬的某一天上午,大家都去上课,党、杨二位教官却把我留在寝室。等到只剩下我们三人时,党教官很严肃地向我宣布:“学校领导已经正式决定,开除你的学籍并且马上离开学校。”我问为什么要开除,他与杨教官同声回答:“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外面派来的军事教官,只负责执行上级决定。”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可笑,我当时担心的并非开除学籍,而是离开学校马上就没有饭吃,真是无颜再见总是被我拖累的大哥。我试探性地问党教官:“听说王家坪有一个训练班,由叶青负责,是否可以把我转学到那里去?”我的回答出乎他们意料,原来他们最怕的是我赖着不走,等到下课同学们回来又会引发愤怒抗争,却未想到我竟这样爽快地答应离校,因此紧张的空气顿时松弛下来。党教官冷笑说:“你知道那是什么班吗?叶青是什么人?那就是集中营,不是你想去就可以去的。”杨教官还卖好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真把你送进去就出不来了。”并且催促我抓紧收拾几件换洗衣服,趁太阳没有落山回重庆投靠亲友,其他被褥、冬衣以后会派同学送来。我环顾四周,无其他人在场,知道两个教官是有备而来,反抗已无任何可能,只有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大步下山。
从青木关到重庆的途中,我在车上就打好主意,不能再回歌乐山麻烦大哥,只有去找九中要好同学帮忙。下车后我按照以前保留的几个地址,首先找到刘忠诚。他在九中毕业后,在重庆一个税务局担任基层工作,由于机关没有宿舍,暂时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住的是双人间,正好有一张空床。他问明我的来意后,非常高兴,大声说:“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咱兄弟俩正好团聚些日子,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暂时有了落脚地方,我心里就踏实一些,这些同学都是情同手足啊!过了几天,闻刚与秦邦文又专程送来我的被褥与衣物,同时还交给我十几块钱,说是同学们都很同情我的遭遇,自发为我捐献点生活费。这笔钱很多都是一角、两角钞票。同学们自己也很穷困啊!我从心底感到一股暖流正在汹涌。
虽然吃住稍有着落,但毕竟前途茫茫,忠诚独自从东北流亡入关,没有任何亲友可以求助,我实在不忍心老拖累他。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大哥突然闻讯找来了,他对我没有任何责备,只是为我今后的前途发愁。经过与忠诚短暂商议后,决定暂时仍住在这里,因为药专已经没有空床可以睡了,食堂管理更加严格,蹭饭也难以实现。大哥要我继续报考升学,并且留下两元钞票供我零用。其实,我既无中学教材可以复习,又没有任何学历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等于是白费力气。但由于实在没有其他出路,也只有硬着头皮再试一次。正好闻刚与秦邦文也不愿在计政班继续学习,他们找到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工作的同乡,邀我一起报考该校经济系。但因我不是三青团员,又无正式学历证书,未能报考。闻刚与秦邦文是用计政班肄业证书报的,那个熟人还给他们办了一个临时三青团员证明,其实他们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的任何活动。发榜结果,只有秦邦文被录取,闻刚只有回计政班读到毕业。几个最亲密的朋友就这样各奔前程,但我们的友谊是终生的,虽然曾经相互隔绝将近半个世纪,但是终于在晚年亲密交往如故。
正是在盲目报考的过程中,我又出现一次很大的差错。记得是在一个酷热的夏日,我独自参加重庆一个高校的招生考试。考场拥挤不堪,又无任何饮水供应,我又干又渴,简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完成考试程序的。下午出了考场,人也轻松半截。正好那学校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水非常干净,又是免费开放,大家争先恐后地跳下泳池,我干脆独自到深水区尽情享受游泳的愉悦。自从离开计政班以后,一直没有游泳的机会,也没有寻找游泳场所的心情。这时我一下水就忘记了其他,游泳就是我的一切。不知不觉太阳就落山了,游泳池也只剩下两三个人,我这才想起外衣还留在更衣室,赶紧上岸去更衣室。这才发现更衣室已经是空空荡荡,我的唯一短裤也被人拿走了,荷包里还有大哥留给我的两元钱。我顿时感到天昏地黑,不知如何是好。回到旅舍,忠诚仍然一如既往,劝我想开一些,不要急坏身体,或者又出什么新的意外差错。晚上睡了一觉之后,我逐渐冷静下来,对忠诚说:“这旅舍我不能再住了,我怕大哥又来找我,因为他正在赶写毕业论文,我应该自己寻找出路。”随后,我就告别忠诚,去找我在九中最亲密的好友周承超。承超在1943年暑假与我同时被开除,但由于冯玉祥到国立九中讲演为前方将士募捐,并且顺便对校方说了几句为承超求情的好话(这可能是受承超叔父之托),学校随即取消了开除的决定。但承超去意已决,他在九中拿到了高三肄业证书,而且就在这年暑假考取了中央大学中文系。承超一直关心我,有空就来看我,知道我再次被开除以后,多次邀我到他家寄住。他的叔父周彦龙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机要秘书,必须随时协助首长处理紧要公务,因此便经常住在机关里,妻子也陪同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他租住的一幢楼房只有承超与堂弟承铮同住,叔父还留下一袋米、一袋面和一笔菜钱,让他们暑假闭门读书,一日三餐也由他们自理。
我很快就找到周宅,弟兄俩一见我便非常高兴,因为他们早已知道我的处境狼狈不堪。他们满口承诺让我与他们一起食宿,我也坦然接受他们的慷慨援助。于是我们又像当年在“爰居”那样,每天读书、练字、交流学习心得。承超在中文系得到章黄学派大师们的教诲,自然可谈许多学问之道,但我却难以消除前途茫然之感。时间一天又一天过去,那一袋米、一袋面眼看就要吃完了,而那一笔菜钱由于临时增加一个人也所剩无几。更为现实的问题是,暑假即将结束,周氏兄弟必须分别前往沙坪坝与江津上学,我自己将何去何从?
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母亲的话似乎永远与我相伴。正在我愁眉不展之际,九中另一要好同学马肇新突然来访,听说我正在为生计谋划,慨然允诺设法找朋友帮忙。肇新缺少承超那样的接待条件,但却同样真诚助人,热心快肠,而且口才与交际能力比承超有过之无不及。他从九中毕业以后,在社会上确实结交不少朋友,其中也不乏乐于为他人排难解忧的侠义之士。没过几天,他就带我到朝天门码头会见一位粮船押运员,此人正要率领两条大木船把粮食运往泸州仓库,便让我在船上打杂并协助看管粮食。押运员是湖北人,身高体壮,性格豪爽。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不仅及时收容我,还给予温言慰解,劝我想开一些,安心在船上干活,慢慢等待升学或正式就业的机会。
我就这样上了粮船,这是我此生进入社会并自谋生计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