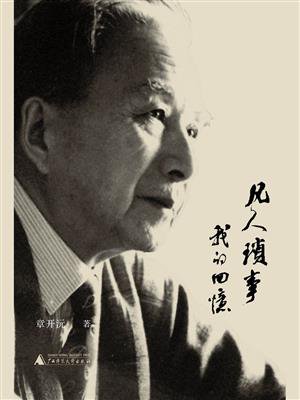学潮发端
1941年,对中国,对九中,都是一个并非吉祥的年头。打从一开年,“皖南事变”就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留下一道创痛巨深的裂痕,从此大大小小的摩擦甚多,大后方的政治形势迅速逆转,反共暗流也直接或间接地袭入相对封闭而平静的德感坝。至今回忆起来,1941年以前的九中仿佛是田园牧歌,而1941年以后却连续不断出现许多怪异事端。
从社会评价来说,高一分校是九中的骄傲,但在某些保守分子看来,则是九中的“乱源”。客观地来说,应是青少年发育期富有活力且多浮躁心理,而知识渐多理想愈高,更易与现实环境发生冲突。
邓校长主持工作期间,由于办学经验丰富而且作风稳健,全面引导我们好学向上,并未认真贯彻国民党政府钳制学生思想的高压方针。在那些年,九中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宽松自在,至少是党治色彩比较淡薄,虽然也有国父纪念周等例行大型集会,但很少借此宣讲三民主义与总裁言论,大多是在学言学,教育学生如何读书做人,乃至严格教学、生活管理制度之类。邓校长本身就有“五四”进步传统,同时兼受西方学术自由影响,他往往以总理纪念周名义,邀请若干文化名人前来演讲。这些主讲者多半是纯正学者,或是具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间或亦有左翼作家如魏猛克,以后干脆留在九中教书。魏老师当时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做宣传教育工作,他的报告热情奔放,纵论战局,抨击时政,深受众多学生欢迎。但邓校长自己和校内老师,顶多只是全心全意的“教育救国”论者,课堂内外极少谈论党派斗争,特别小心翼翼,缄口不谈极为敏感的国共关系。当然他们自己对国内政局也有相当认识,无非是保持若干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超脱,但其结果却是造成许多学生在政治上的无知与幼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龄较小且昧于世事的学生,几乎完全不知道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哪些区别与冲突,只是抽象地追求光明与摒弃黑暗。
因此,高一分校的学潮一般都是自发的,而且主要是对于生活与教育缺陷的不满乃至过激抗议,很少有什么政治色彩。最早一次学潮发生在1939年,距九中创校还不到一年。高一分校学生会主席潘祖尧(潘氏三兄弟的大哥),带头抗议伙食质量下降,怀疑庶务人员贪污,要求清查账目,引发一场风波,听说在校本部总务处工作的陈独秀儿子(松年)还挨了打。我当时在初二分校,未能看到现场情况,事后听同班的祖舜、祖禹说,祖尧与另外两位学生会职员都因此受到开除处分。
1940年女生宿舍发生失窃事件,一位女同学因被怀疑深感羞辱,愤而疾奔投江自杀。高一分校部分同学闻讯反应激烈,又一次集合前往校本部,抗议校方任意侵犯人权。此次风波由邓校长亲自出面应对,坦然承担一切责任,并与迅速赶来的高一分校老师耐心疏解,终于把示威学生劝回分校。
但是1942年5月一次风波的结局却非常不幸,当时我已经进入高一分校,所以自始至终都目睹了现场情景。起因是一位新来的年轻数学老师因为缺乏经验,教学效果极差,令该班学生非常不满意,除要求更换教师外,还以漫画讽刺这位老师。新来老师年轻气盛,愤而投诉至分校校长刘剑如,要求严厉处分肇事学生。刘剑如本来是一位优秀的富有经验的英语教师,我们对他都很崇敬,但他却缺乏必要的行政管理经验与应变能力。他听信一面之词,未经充分调查便责令班长交出漫画作者。班长思想不通,始终保持沉默,刘老师便动员全班同学揭发,结果没有一人起来揭发。他在盛怒之下当场宣布:“全班同学各记大过一次。”这就使全班学生更为激愤,立即结队前往校本部要求讨回公道。适逢邓校长外出办事,大家只有失望而归。刘老师本应冷静下来,乘机设法沟通缓解矛盾,但却一错再错,迅速以“不假外出”为由,再次给全班同学各记大过一次。这就把该班全体同学逼到死角,无路可退,同时更引起全分校众多同学的公愤,纷纷赶来支援。当晚,抗议学生派出代表与分校当局谈判,刘老师的态度仍然极为冷漠,使围观的学生怒火中烧。混乱中不知是谁有意把油灯弄熄,一大群学生冲进办公室,个别同学乘乱打了刘老师几拳,使事态更趋激化。幸好高一分校老师平时大多与学生关系比较融洽,姚述隐、翟光炽等好几位威信甚高的老师出面调解,两位军训教官也耐心温语开导学生,刘剑如老师才得以安全离开。但事态仍然继续蔓延,高一分校学生全体罢课,教育部派专人前来驻校督查,江津师管区亦派兵前来弹压。邓校长本来想和平了结,曾派深受学生爱戴的资深老师劝说学生复课,并且公开保证绝不会开除学生。但事与愿违,在外力干预下竟有16位同学被开除或停学,其中也有与我同班的潘家老二祖禹。他平时沉静好学,从不多嘴惹事,此次却出于激愤仗义执言,以致成为学潮的牺牲品。
我是此次学潮的目击者,并且参加罢课以示支援,但事发当晚心情却比较复杂。我对高一分校领导逐步转向压制管理也是不满已久,特别是对刘剑如老师不顾学生健康盲目增加课业负担更为反感,所以曾经在墙报上以漫画给以讽刺。但我内心始终尊敬刘老师,因为他确实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业进步,而且英语教学效果有目共睹。看到他被打后,在体育老师扶持下勉强走出办公室,眼镜已经跌落,满脸惊惶且有泪痕。想到刘老师家贫且子女较多,落到如此境况,回家后与师母抱头痛哭,我的内心竟然涌现若干痛楚,说不清是怜悯还是同情,因为他毕竟是与我父亲同一辈的人啊!我能够理解他回家后的羞愧、委屈与悲愤。同时那位军训主任教官(姓李)也曾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位年龄偏大的职业军人,虽有少校军衔,但因没有任何党政背景,似无晋升之望。他身材瘦长,脸色蜡黄,听说曾患肺病并咯血。可能正是因为病弱已不适应军旅生活,所以才安于利用学校这个闲散差使在乡间疗养。我已记不清他对我们曾经进行过哪些军事训练,甚至从来也没有听过他的什么训话。倒是常常记得他总是傍晚伫立在山坡大树下,默默地向远方眺望,好像是在等待什么人,又似乎是在寻找什么人,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陷于深沉的忧郁与茫然。夕阳逐渐落山,他的身躯慢慢形成灰暗的影像,仍然孤零零地伫立在山坡上。但是在学生围攻刘老师的那天晚上,他倒是显示出职业军人的忠于职守,及时出现在办公室,但没有任何愤怒的训斥,只是低声细语耐心劝说,在我看起来简直就是乞求。直到刘老师安全走出办公室,他才独自喘着粗气蹒跚回家。
混乱之际,个别激进分子还把刘老师的蚊帐、被褥丢进祠堂附近的粪坑,听说还有人乘机把点名册与试卷都撕毁了。对于这些行为,我都难以附和,甚至怀疑这些人是否学习成绩太差,借此消灭不良记录。但我毕竟是个幼稚的学生,而且属于一个不起眼的弱势群体,不敢公开而鲜明地表白自己的观点;也可能那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明确观点,无非是随波逐流而已。因为思想有所保留,行动比较节制,所以这次风潮以后我倒没有受到任何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