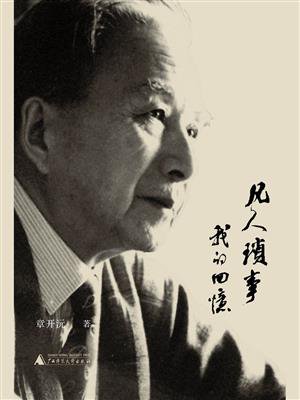勒令退学
我一向安分守己勤奋好学,从来不爱出头露面,更缺乏聚众闹事的勇气与本领。虽然已感到校园氛围发生变化,但仍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习惯学习与生活。1943年元旦的风波平息以后,我更加沉溺于阅读课外书籍。图书馆有一整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在学生中间我可能借阅得最多,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直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漫无边际,任意选阅。尽管是生吞活剥,似懂非懂,有些甚至是一窍不通,我也乐此不疲。课余最大的爱好仍然是爬山和游泳,但成群结队嬉闹乱跑已大为减少,倒是更爱独行侠似的漫游,躺在林间或仰卧江面胡思乱想,在虚幻世界尽情享受超越世俗的乐趣。我自以为与世无争,自得其乐,但在书籍中接受的某些美好理念,却难免与现实环境相冲突。我没有把这些冲突表现于语言,却往往不知不觉地形诸文字。其实文字比语言更容易被权势者抓住把柄,乃至作为罗织成罪的“真凭实据”。这是自古以来早已产生的约定俗成,可惜我当时对这样浅显的道理一无所知。
邓校长在职期间,提倡学生组织社团开展课外活动并出墙报,而且是自行结合,并非限于同一班级。我由于爱写点小文章,便被高年级同学拉去为他们的墙报写稿并画点漫画,即使在邓校长去职与毒药案发生以后,这个墙报仍然定期刊布,而我继续充当他们的自由撰稿人。其实这个墙报一共也只出了不到十期,而我的投稿更是寥寥无几。我的文字稿属科普性质,由于是亲身观察检测,再加上文字简洁清新,尚能引起若干同学兴味,也未触犯任何校方禁忌。倒是两幅漫画引发了邵华一伙的恼怒:一幅是许多学生围着一个高大的木桶抢稀饭,有一位竟然头朝下脚朝上掉进木桶内;另一幅是一位威风凛凛的老师,把一摞摞书抛在一个瘦骨伶仃的学生身上,表达我们对学业负担过重的不满。墙报贴在大食堂旁边的墙上,正对着分校办公室的门。同学们饭后围观者甚多,特别是那幅抢稀饭漫画更有吸引力。
其实漫画并无任何政治动机,更谈不上什么深刻的寓意,我只不过是模仿从小就喜欢的缘缘堂主人(丰子恺),以质朴的笔墨于平凡事态中表现若干生活情趣。但我却没有想到,学业问题已经在高一分校引发过一次学潮,而伙食克扣问题业已成为当时较为敏感的学潮导火线之一,特别是紧接着毒药案而刊出此类漫画,简直是自己引火上身。
平心而论,1940年以前,九中的伙食还过得去,至少是一日三餐还吃得饱,尽管每天的菜谱都是炒胡豆、牛皮菜之类,但每隔三五天总还可以吃到杂菌烩豆腐。杂菌非常便宜,几角钱就可以买一大堆(干菌),与豆腐烧在一起,十分鲜美可口。早先每月初一、十五还可以打一次牙祭,多半是中餐每桌加一大碗红烧肉。有次打牙祭正好轮着我帮厨(实际上是伙委会派出的监厨),主动帮助做点择菜洗碗之类杂事。厨师看我比较勤快,给我单独盛了一碗红烧肉作为奖励,使同学们都羡慕不已。但这样幸福的时光很快就一去不复返。1940年以后抗战进入更为艰苦的阶段,大后方粮食紧缺,物价飞涨,政府官员贪污中饱,教育经费层层克扣,学生伙食水平迅速下降。原来每天两干一稀改为一干两稀,早晚两餐都吃粥。米的质量更为下降,除霉变外,还夹杂沙粒、碎石、稗子、糠壳、米虫乃至老鼠屎等等,当时称之为“八宝饭”。米饭本来是食堂摆几个大桶敞开供应,最初尚能保证定量,没有争抢之事,其后粮食定量日渐减少,学生唯恐吃不饱,往往是第一碗略微少盛,几口吞完后再满满添一大碗。这种策略一经普及便出现争抢,有些动作迟缓或身体瘦小的同学便难免吃亏。于是伙委会改为每桌发一桶饭,八人自行平均分配。但这只限于午餐的干饭,早晚的稀饭仍然以大木桶装盛,所以许多人围着粥桶争刮剩粥的尴尬场面依然如故。蔬菜也愈来愈少,大家主要是靠有限的炒胡豆下饭。四川乡间炒胡豆的方法颇有特点,即先把干胡豆炒香,随即加水泡胀,然后捞起加少许油盐炒得烂熟。这种方法既节省油盐,蚕豆也显得松软量多,如加点辣椒面与葱花,更加喷香可口。可惜数量甚少,各桌只能节省分享,大家一般每次只夹一颗,更不会用汤匙舀取。据说亦有每人分若干粒者,我则从未见过。新鲜蔬菜倒是有一大碗,多半是淡而无味的牛皮菜或很老的藤藤菜(竹叶菜),都是农家用以喂猪的饲料,我们主要还是靠盐巴与辣椒粉加上米汤咽饭。因此,许多同学因营养不良而体弱多病,比较常见的疾病,冬有疥疮、气管炎,夏有痢疾、打摆子(疟疾)。这些病我都被传染过,此外还患过更为凶险的丹毒(据说腿上的红线上升越过肚脐即死,而且当时盘尼西林贵过黄金,几乎无药可治),所以发育很差,身材与年龄极不相称。幸好酷爱游泳、双杠之类运动,又常徜徉于山林田野,大自然慷慨赐予的充足阳光与新鲜空气弥补了营养不足,否则真会如有些长辈所担心的“活不到二十岁”,至少是很难越过丹毒那一关。当时只有黑药膏,无任何特效药,后来主要是靠农村土法,用水田烂泥涂抹挺过难关,听说烂泥里面有盘尼西林,真是天佑我也!
我的漫画无非是这种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顶多是用稍许夸张的笔墨宣泄若干内心蕴积的苦闷。如果说是蓄意借此煽动学生闹事,当时的我确实既无此心更无此胆。但以后的事实表明,已有极少数人正是这样认定我的作画动机,而且已经记录在案,并为我准备了陷阱。回想起来,我是自己往陷阱里跳,因而成为一只并未出头而横遭枪打的无辜小鸟。
据《西渡漫记》作者回忆:“(毒药案)事件发生后,校方对高一分校学生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加强思想控制,深入追查案情。军事教官由原来的两人突然增加到一二十人,平均每个班派驻两三人,教官大部分临时抽调自军校或部队。”但我却从来没有这个印象,可能作者讲的是我离开九中以后的情况,因为他是1945年才转学到九中。1944年底我参加青年军,所在连队的连长正好是九中教官,但我在校时并未见过他,想必就是1943年暑假以后增派的。
对我来说,真正的思想压制并非来自军训教官,因为我在高一分校几乎没有经受过什么军训,只是听说有年暑假在校本部集中进行过军训,仿佛现今的夏令营,但并未要我们参加。对我公开严厉施压的,是高一分校新来的训育主任魏老师。他是山东人,身躯高大,经常穿黄色中山装,颇有军人风度。他教世界史,特别崇拜俾斯麦,经常在课堂上赞颂这位铁血宰相的文治武功。由于山东口音极为浓重,他把俾斯麦的原名读成Biesmarkai,所以我们背后称之为“俾斯马凯”。他出任高一分校训育主任之后,大有治乱世必用重典的气概,而我就成为他首次重拳出击的倒霉对象。
我读高二以后,对文学的兴趣转移到近现代,最喜爱的作家多半属于左翼文学队伍,如鲁迅、茅盾等。由于我的作文比较关心社会现实而且笔调常显冷峭,所以有些年长同学常以“小鲁迅”相称。我自己虽无非分之想,但舞文弄墨的兴趣却因此而愈浓。我常在规定必做的周记中写点半调侃半讽刺的杂文,有的好心老师如朱彤,早就以批语警示:“小小年纪,牢骚太盛,将来不知伊于胡底。”我不知“伊于胡底”深意,依然我行我素,结果还未及等到将来就以文字获罪。
1943年春夏之交,有天上世界史课,魏老师面容凝重,挺胸收腹摆出一副威严架势。他先不讲正课,而是用山东口音拖长声调宣读一篇我刚写的周记。周记实际上是语文课外作业,一般无题,可长可短,便于班主任与学生交流思想。我的短文大意是: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悠扬的鸽铃声惊扰了酣睡者的清梦,这时绅士们手舞竹竿并怒吼追赶,但鸽群依然在蓝天飞翔,鸽铃也悠然如故。我已记不清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可能主要是模仿鲁迅某篇杂文,而鸽子又是我自幼就欢喜的鸟类。当时自己确实没有讥讽时政的用意,何况在长期连报纸都看不到的穷乡僻壤,连什么是国共之争都弄不清楚。但魏老师却如同堂吉诃德手执长矛向风车出击,厉声呵斥:“你要自由吗?什么地方自由?到莫斯科去!”当时我还不满17岁,根本不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对“到莫斯科去”一语的险恶含义毫未察觉,只是以后才想起他为什么不说“到延安去”。我感到很委屈,因为实在没有起过这样勇敢的念头,但又气愤郁结不知应该如何回应,干脆就保持沉默,低头站着。魏老师号召全班同学揭发批判,满心指望能够出现“鸣鼓而攻之”的热烈场面。可是却迟迟无人应声而起。过了一会儿,只有班长起来揭发,编造若干莫须有的情节以坐实我对党国心怀不满已久。班长姓王,以前当过兵,原来在校本部吹号,稍后转来插入我班读书,因为已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所以被魏老师指定为班长。记得好几年以前,全校举行总理纪念周,邓校长请著名音乐教育家马丝白讲演声乐原理,老王也持号站立随侍。马丝白讲到某个音阶时,必定大声喊道:“号兵吹个哒!”借以示范定音。所以我们平时与他开玩笑,常说“号兵吹个哒”。他倒也犯而不较,显示出少有的宽容大度。平时我总是把他当成老大哥。不料正是这个貌似忠厚老实的老大哥,现在却落井下石,公然编造一些虚构的证词,使我更加气愤。我自幼外表虽然柔弱,但实际上比较倔强,母亲称之为“牛脾气”,大哥往往用上海话骂我“杠头”。此时此刻,我那与生俱来的脾气又大发作,率性歪脖扬头,满脸涨得通红就是不开腔。课堂一片寂静,顿时形成僵局。魏老师似觉有点尴尬,但又无可奈何,只得大手一挥命我坐下,继续开讲正课。
课后我逐渐冷静下来,恍然大悟祸正来自班长。因为周记一般都是由班长收交班主任,而兼语文课代表的班长平常总是夸奖我的周记,不知为什么这次却径直交给训育处,引发魏主任肝火,使我雪上加霜。我想班长大概是新发展的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或者什么也不是,就是按照魏老师的意旨办事。但我仍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课后“俾斯马凯”或是班主任都没有找我单独谈话,也没有要我写任何检讨。我以为已经风平浪静,依然按照原来样式学习与生活。
很快就放暑假,多数同学都回家或到外地探亲访友,只有我与少数不大熟悉的同学留在空空荡荡的宿舍,整天阅读各种书籍,或独自到江边游泳,倒也自由自在,丝毫没有觉察已厄运当头。有一天,校本部突然派人来通知我:“你已经被勒令退学。”简直如五雷轰顶,我的头脑顿时一片空白。记得当时接过正式通知书,具体内容已记不清,大意是思想不纯,行为越轨,勒令退学云云。说来极为可笑,当时我害怕的并非政治迫害,而是马上没有饭吃。因为只有在读生才能保证一日三餐供应,而退学则意味着饿肚与流落街头。我已经找不到身边可以求助的老师与好友,只得硬着头皮到镇上校本部向姐姐告急,再由姐姐带着去见唯一的亲戚李玉屏。她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但她在教务处,与训育处是两个系统,再则又是一般职员,人微言轻,无能为力。她认为已经无可挽回,应该及早离校另谋出路,以免出现更为难堪的后果。她为我买了船票,与姐姐一起帮助我整理好简易行李,并送我到江津码头上船,千叮万嘱要我一路注意安全,到重庆后立即找开平大哥设法安置。她们没有任何责怪,只有关心与体贴,这种深挚的亲情温暖了我已被严重伤害的心,并且使我增添了在茫茫人海中挣扎前进的勇气。
毕竟是只有17岁的少年,轮船起碇后我便暂时忘记了一切不幸。望着渐渐远离的德感坝,还有那连绵不绝的远山与湍急翻滚的长江,我突然触发了写作的冲动。有一首小诗就是在船上暗自吟诵写成的:“青山望不断,江水与天连。烟霭苍茫处,应是旧家园。”整整五年,浑浑噩噩,从未认真想过家,仿佛九中就是我的家。然而就是一场春梦,如此迅速就失去了这个家,于是就想起另外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家,那个远在千里以外被战争烽火隔绝的父母所在的家。诗作谈不上多么深沉的乡愁,更多的倒是对古代文士的效仿。17岁的少年,特别是愚钝如我,没有那么多成熟的感情,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求知欲与冒险犯难的冲动。江津在重庆上游,此行是顺风顺水,我拼命扼制跳进江中与船同行的古怪念头,在甲板上到处闲逛远眺,早已忘记身在何处,今后又将何往。
我就这样离开了苦读五年的九中,田园牧歌式的童年到此结束,从此迈上更为迂回曲折的人生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