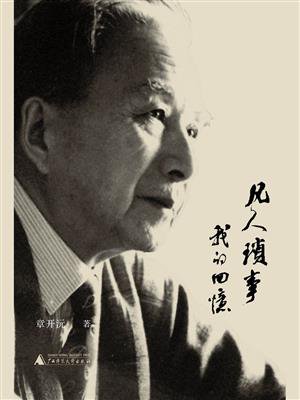转学王家坪
说来令人好笑,到重庆乘坐的轮船竟是我下乡以后再一次接触的现代文明。那些年,德感坝既不通火车,又没有公路,水上交通主要靠木船,陆路主要靠骡马、滑竿与鸡公车(即传说中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实际上就是手推独轮车),而更多的是靠人们两条腿跋山涉水。轮船到达重庆后,背着行李攀登朝天门码头长而且陡的石阶,一级一级爬上江岸,终于又看到重庆这座雄伟山城,对我来说,就是从落后的乡野回到现代文明。那绕山盘旋的马路,来往奔驰的汽车,令人目眩的霓虹灯,使我感觉仿佛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求生的紧迫,使我无暇从容欣赏这个城市,便匆匆挤上公交汽车前往歌乐山,大哥就读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就在此山深处。大哥原来随文矿师到贵州,曾在遵义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习画,由于父亲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提供学费与昂贵的绘画材料开支,再则将来就业也不容易,只好劝他及早改学一门谋职较易的专业。大哥从小就痴迷绘画,而且还很有天分,但深知长子应该承担的家庭责任,遂毅然考进药专制药专业。这是一所国立大学,沦陷区学生可以享受“贷金”待遇,而且高级药剂师又是比较稀缺的人才。这是大哥为我们这些弟妹所作的牺牲,从艺术专业转入理工专业需要克服何等困难!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唯一担心的是如何向大哥交代被开除的原因,因为大哥比我年长七岁,我从小就对他存有敬畏之心。不过见面后这种疑虑立刻就消失了,我与大哥分别六年,他已长成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男子汉,虽然已改学制药三年,但仍然保持着艺术家气质。大哥见我平安到达,感到非常高兴,不仅没有任何责难,反而温言开导。最奇怪的是,他一直没有问我被开除的原因,可能李老师与姐姐已经在信上做过说明,知道我的被迫辍学并非由于道德与学业方面的缺失,至少还不算辱及家门,因此便对这个顽劣幼弟免予追究吧。
但我的到来毕竟给大哥带来极大负担,因为他还差一年才能毕业,目前没有任何收入,而远在江西的父母也难以为我提供全部生活费用。幸好是暑假,大哥的同室级友徐国钧担任周太玄教授的助手,主动住进他的实验室,为我让出一张床。一日三餐在大食堂混食(现在叫作蹭饭)。药专的伙食比九中好得多,而且管理也不甚严,大哥的同学都很同情我,即使大哥出外,他们也会热心邀我一道用餐。当然也有尴尬之日。有个星期天食堂因修理炉灶停火一天,大家都各自设法分别到各种小餐馆进餐。大哥正好身上无钱,临时又找不到熟人可以借钱,只好带我捡梧桐树籽,用小电炉炒熟后聊以充饥。但捡到的桐籽不多,硬壳内的果仁很小,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下午幸好有本地回家的同学闻讯赶来,请我们各吃一碗热腾腾的汤面,这才混过艰难的一天。
在药专住了一个多月,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一样的生活。因为是新建的院校,宿舍教室宽敞明亮,电灯自来水一应俱全,进城还可以坐公共汽车。但我很少外出,因为前途茫茫,根本没有闲逛的兴致。大哥要我认真准备报考大学,但我有自己的难处:一是连高三上肄业证书都没有拿到,是个没有学籍的另类学生;二是没有高中课本可供复习,因为九中所用课本都是由学校提供借阅,学期结束时一律交回,而我自己又无钱购买课本。我自幼性格内向,虽然爱写点小文章,但却拙于语言,有难处也闷在心里,很少向别人求援。大哥由于准备毕业论文,整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此外,他还是学校话剧团的导演、演员与美工设计,连节日也难有余闲,所以也顾不上督促我认真备考。因此我每天待在空空荡荡的宿舍,不知如何复习,也干脆没有复习。幸好大哥有一架美术书刊可供消磨时光,其中有一套《中国绘画史》,印刷精美,插图丰富,引人入胜。我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从吴道子、顾恺之,到扬州八怪、岭南画派,都似懂非懂琢磨一番。宿舍后面是一大片菜地,每逢黄昏时分夕阳西下,我便去搜寻已经被厨工摘剩的小番茄,借以填充经常处于饥荒状态的肠胃。那些青色或黄色的没有成熟的果实,又酸又涩,吃多了就会反胃,有时甚至呕吐大滩黄水。以后很长时间我非常怕吃番茄,其根源就在于此。
我在九中读的是春节始业班,所以我在1943年暑假只读完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即便不开除也拿不到毕业证书。我的同班级有好些人为了尽早就业,都办了肄业证书到重庆报考大学。他们没有忘记我,常有人远道赶来歌乐山看望我,有时也邀我到他们家中吃饭,这样就稍微消解若干寂寞与无聊。夏国彦同学还为我多办了一张他自己的肄业证书,换上我的照片,以便我冒名顶替报考。但我始终没有使用,因为如果这样做,我的姓名、籍贯永远都改换了。我受旧小说的影响太深,认为大丈夫必须坐不改姓立不改名,但对他这种深情厚谊,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
我的高考是无学业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的,加上没有任何准备,考试成绩很差,所以几所报考的大学发榜时都名落孙山。大哥也无可奈何,但他没有任何埋怨与斥责。后来不知道他找到哪位稍有地位的亲友长辈,为我办理一张沦陷区流亡学生的证明,报考直属教育部沦陷区学校救济委员会主办的“计政人员专修班”,两年学制,相当于职业专科。此类学校以救济与就业为主,分数线较低,我居然被录取了。大哥非常高兴,因为这不仅解决了我的食宿问题,而且将来还可以谋求一个银行或邮局之类待遇优厚而稳定的职业。考试的日子,他亲自送我进考场,唯恐我出什么差错,但我去计政班报到入学却是独自前往,因为路太远,车费较贵。
报到那天,我一上公共汽车就出了差错,因为人太挤,我又站在车门边,车门一关就夹住我的行李,车太旧,门又关不拢,行李就掉下去了。我急得大声呼唤,同车的大人也帮着叫停。好心的司机发觉后立即停车,让我下车把行李取回。行李虽然取回,但我已跑得满身大汗,幸好车上的热心长者为我让出一个座位,因为这是长途车,我要到青木关终点站。
坐定以后,车已走过了几站,车上的乘客也减少甚多,大家都有座位。我的心神略为松弛,便开始观察同车乘客。乘客男女老少都有,高矮胖瘦与贫富差别很大,我不知道他们从何处来,往何处去,可能是由于得到他们的同情与帮助,觉得人人都是慈眉善目,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甚至产生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汽车永远不停,让我长期生活在这个群体之中该有多好。”我竟然产生幸福感,并沉浸于这个幻觉之中,这就是当年我的虚幻世界——昼梦。
但车终于停在终点站青木关,站牌这三个大字赫然入目,直到人都下完了,我才提着行李慢慢离开我曾经暂时栖息的“和谐号”公交车。王家坪与青木关相距三十里。这是我第一次孤身步行这么远的山路。沿途风景秀美,但我哪有心思观赏风景,一路急行终于到达我的另一个栖息地——计政班。
王家坪是高山上的一块平坝,早晨甚至整个上午都有朵朵白云缭绕,行走在林间小路仿佛是仙境漫游。山脚有一条较大的溪河,清澈见底的溪水围绕着大山缓缓流淌。溪上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从山顶石寨下去,走过石桥,便是一家小小的所谓餐馆,实际就是一间破旧的茅棚,里面摆着少许桌椅,卖点胡豆、白酒与汤面之类的食品,此乃本地唯一的商业中心,也是唯一可供消费的休闲场所。原来可能只有偶尔路过的人进来歇息,现在却不时有计政班的师生光顾,喝点小酒或吃碗清汤寡水的阳春面。
计政班是当地最高学府,就设在古老的山寨里,一色的竹篱茅舍,倒显出几分古朴幽雅。该校名义上分为会计、统计两个专业,但由于师资与图书设备不足,实际上只有一个课堂“一锅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读过的课程有会计学、货币学、簿计、统计与世界经济史,也许第二年还要学若干专业会计、统计,并出外实习。住校的专任老师极少,除几个青年助教(兼图书室工作)以外,只有一位杨荣国教授。不过当时他不教哲学,而是教世界经济史,也没有解放后那么出名。他教学非常认真,课余也很关心学生与学校事务,因此很受尊敬。其余的兼任老师上完课就回去了,课余很难见到。杨老师的家也在重庆市区,但他经常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并且在学生食堂买饭回去吃。每逢周末,步行三十里到青木关乘公共汽车回家,星期一清晨又循同样的路线回校。他的教学任务不算很重,课余与学生接触也不多,可能主要为潜心治学与写作。他随身还带有一个四五岁的儿子,可爱而又顽皮,好像是靠那几位年轻女助教代为照料。小孩还经常爬到我的床上(双人床上层)淘气,死乞白赖不肯回去。由于交通不便,杨老师并非每周都带他进城,就把孩子留在校园,好在大家都很喜欢他。
班主任是教育部一位官员兼任,河南口音,典型的国民党公务员派头,常常穿一套蓝布中山服,前额头发打理得干干净净。他似乎不常来校,偶尔来校也不与学生交谈,显得神秘兮兮。学生管理主要靠两位军训教官,一姓党,山西人;一姓杨,江苏人。党教官年龄较大,军衔也较高,人如其姓,满脸严肃,寡言少语,城府甚深。杨教官刚从军校毕业,由于年轻,比较热情活泼,欢喜与学生聊天,具有较多亲和力。我不知道这两位教官如何分工,反正杨教官出头露面时多,早晨起床号一响,他必定快步巡视各个寝室,大声催促学生起床集合做早操。上课时他也经常进课堂巡视,督促学生认真听讲。晚上9时再次巡视寝室,催促学生熄灯就寝。至于党教官整天干些什么,大家不清楚,也没人想打听。
学生成分复杂,有不少是颇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大多为混口饭谋个职而来。真正从中学转来而又有志于升学的并不多,而我又是其中年龄最小的。可能由于班主任是河南人,所以豫籍学生人数最多而且很自然地抱成一团,仿佛有点优越感,成为学校中的主流派。有少数北方省籍(如天津、山东)学生,也与河南学生气味相投,结成一帮。其他南方省籍的学生,分别来自江、浙、皖、赣、鄂等省,人数都很少,很难形成像豫籍学生那样的地域群体。不过由于河南学生的强势专横,他们也很自然地增强了彼此联系,声息相通,互相关切,隐约形成南北对峙局面,因而很容易产生大大小小的摩擦与冲突。也许班主任正需要这样的局面,以便于他的党化教育与思想统治。不过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此类政治问题。
由于省籍的原因,我自然归属于南派,在该校期间,很少与河南同学交谈,当然他们也从未主动找我聊天。他们大部分都住在一起,与我同寝室的则是河南以外省籍的人。南派人数不多,但其中藏龙卧虎,虽不如北方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却也不乏智勇兼备不畏强敌的豪杰。记得有位名叫罗翔的湖北人,原本是航校学员,且已进入单飞阶段,却由于毕业前想在女友面前露一手而毁了“翔程”。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事先约定女友乘某班轮船渡江,观看他驾驶飞机从轮船侧面低飞掠过,满心指望女友可以近距离观赏其翱翔的英姿,却不料因角度有误,连人带机一头栽进江中。幸好他比较灵活,迅速爬出机舱,得以保全性命,但最终还是遭到开除军籍的严重处分。罗翔英姿飒爽,热心快肠,所以无形中成为南派头面人物。南派中可以与罗翔相提并论的还有两位,一位是罗翔的老乡,两人亲如手足。名字我早忘了,只记得他身材修长,仪态潇洒,社会阅历比较丰富,常常高谈阔论,显示见多识广。虽然不如罗翔那样沉稳大气,但常能以妙趣横生的胡侃吸引众多听众。其最大特点是放言无忌,因为已先后进过几次所谓“培训班”(即变相集中营,以“感化”思想偏激青年为主的拘留所),而且又确实查不出任何“异党”背景,随抓随放,反而破罐子破摔。另一位是上海人,只记得姓裔,因为这个姓少见,反而记住了。他原先是银行职员,着装整洁,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下巴总是刮得青青的,颇有西方绅士风度。因为口音相近,他常常爱找我闲聊,主要是谈京剧唱腔。我自幼受父亲影响,稍微能够听懂,因此成为裔兄的知音。他不仅是戏迷,而且还曾花钱拜师成为票友,最常吟唱的是《还珠吟》中那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程派唱腔摇曳婉转,特别富有感染力。
但与我关系更为密切的却是另外三个人,一是闻刚,南京人;一是秦邦文,四川人,冒籍沦陷区;另一个姓孙,江西人,名字忘了,年龄似乎已近三十。
闻刚与秦邦文结识在前,很快与我成为密友,可能因为年龄相近,又都来自中学,思想都比较单纯因而投缘吧。我们不仅上课时坐在一起,课余也常结伴休闲。闻刚个头比较高,是个英俊少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高官的司机,家庭经济情况稍佳,多少还有点零花钱,着装也比较整洁。我们经常在山林里夜游,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海阔天空,自得其乐。有时月光皎好,我们就坐在赭红色的石头寨墙上,由我演奏二胡,为秦邦文唱歌伴奏,而闻刚便成为唯一的听众。山林在银色的月光下特别幽静,没有犬吠,没有虫鸣,仿佛整个王家坪都沉睡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杜鹃凄楚的啼鸣。那漫山遍野的白色蔷薇与红色杜鹃花,在月光照耀下如同锦绣。我们充分享受这山林秀丽的夜色,很晚才回寝室。
山寨边缘有一座破旧古庙,由于位置偏僻而附近又没有什么人家,香火早已极为冷落。庙里只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僧人,一人右腿已残,走路时总是先迈左腿,站稳后再抬起右脚,悬空环绕一圈后才能落地。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阿基米德,仿佛他正在画几何图形,这个荒唐的想法,总也挥之不去,一直残留至今。两位老僧由于无力下山寻求布施,所以除早晚诵经拜佛外,还摆个小摊,卖点炒胡豆、米花糖之类廉价小吃,附带也为行人提供点茶水,借此维持生计。所谓茶水,其实就是四川乡镇常见的“老鹰茶”(谐音),用的并非真正的茶叶,而是以某种树叶晒制的代用品,一枚铜圆可以买一大碗,还可以续添开水。我们三人常来庙里小坐,一边嚼胡豆,一边漫无边际地胡聊,两位僧人一般都不应答,仿佛入定似的闭目养神,但双手照样捻动着佛珠。我们不知他们来自何处,更难想象他们未来的归宿,只看见他们已经在为自己准备棺木,白天偶尔还可以听见他们挥斧伐木的声音。但僧人圆寂应是无需棺木,他们为什么要在生命的终点回归世俗呢?
也许正是从老僧那里获得若干人生感悟,我开始思考生命的原始、归宿与人生的意义,而在此以前根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亲眼看见死亡,外婆还有两个弟弟都是在我面前缓缓死去,总觉得他们无非是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某一天又会回来,有时甚至做过与他们重新聚会的甜美的梦。在九中读书期间,每年暑假都会有同学在江中游泳不幸溺水而死,有一年一次溺死四人,尸体置于高一分校路边,我们游泳归来正好目睹惨景,但从未想过死亡也有可能降临到自己身上。直到最后一个暑假,离开九中之前曾经独自到江中游泳,仰卧顺水漂流时,忽然听见岸上有啼哭声,原来是一对夫妻为溺水的儿子烧纸悼亡。我的心猛地一震,这才想起如果我也不幸淹死,爸妈将如何悲伤,因而奋力划过险恶的湍流,慌忙登岸回校。这是我第一次想到自己也会死亡,想到战争给多少人带来死亡,乃至人们生老病死的痛苦与悲伤,终于追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但这样深奥的问题绝非一个幼稚少年所能给出解释,也许这些想法与当时的年龄原本就太不相称,不想这些问题可能活得更加轻松。正因为如此,在被开除以后虽然依旧得到家人和同学的关切与照顾,但自己内心仍然潜藏着孤寂与苦闷。只有书籍可以解忧,阅读使我的求知欲得到某些满足,使我忘记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幸与困惑,把我引进一个虚幻但毕竟存在的精神世界中,让我充分享受思想自由飞翔的愉悦。
计政班的图书不多,大都是配合课程的教材与相关专著,但中外文学名著却为数不少,听说是由于杨荣国老师的建议,因为山间缺乏应有的文娱活动,休闲只能依靠阅读。但学生借阅图书者为数甚少,他们大多缺乏阅读习惯,得空宁可打扑克、闲聊、喝酒,甚至躲到偏僻的地方打麻将。所以我得以随意借阅自己喜欢的书籍,而且没有任何时间限制。我看得较多的是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名著,如《战争与和平》《死魂灵》《猎人日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乃至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等。我之所以能够从容阅读长篇小说,是因为课程负担不重而教学管理甚松,老师上完课就走,而学生很多只是混张就业的文凭。计政班虽然在乡下,但毕竟属于重庆郊区,晚上有电灯照明,这就比在九中时优越多了。直到晚年我都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我们这代人是俄罗斯19世纪古典文学乳汁哺育长大的”,指的就是这大半年颇能使我感到满足与幸福的乡居时光。
与我有相同阅读兴趣的是那位姓孙的同学。我一直无法弄清他的实际年龄,由于面容比较苍老,看起来至少有二十七八岁。他似乎历经沧桑,早已不复幼稚与浮浅。他很少与别人交往,总是埋头读书或处理生活杂务。但不知为什么他唯独主动与我交好,可能由于我年龄在班上最小,他出于兄长情结而自然流露出关切,也可能因为我俩同样是班上仅有的虽隆冬仍穿草鞋的最贫寒的学生。他教我缝补衣服鞋袜,一个人如何独立洗涤、晒干直至上好棉被等生活技能。只要是温度不算太低的月夜,他必定邀我,而且也只邀我一人,前往山脚小溪游泳。他游泳技术很好,蛙泳很少溅出水花,有节奏地舒展手足徐徐前行。我虽然在江津江中游过好几年,自认为经历过许多风浪艰险,但姿势、速度、耐力都不及他。我特别欣赏他那悠然自得的神态,仿佛已与两岸山林及潺潺溪流融为一体。他从不停下来等我,也从不催促我紧跟,但自有一种说不出的神秘力量,促使我始终不敢懈怠,坚持尾随他作漫长的遨游。我们往往游一两个小时,这是我们一天最快乐的时间,仿佛这星空,这明月,这山林,这溪流,乃至这宁静的夜晚,全都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很少讲话,只有他偶尔低声吟唱江西民间小调,几乎每句都以“哎呀来”开头。他的声音略带嘶哑,但曲调幽美且流露若干深沉的柔情。相知渐深以后,我才知道他来自赣南苏区,但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任何政治倾向。当时我对政治也没有任何感悟与兴趣,虽曾听他偶尔讲过若干苏区社会生活情况,但也如同东风过马耳,并未对我产生任何影响。
我几乎同时保持与他以及闻刚、秦邦文的亲密友谊,但他与闻、秦却无任何交往,相遇如同陌生路人。闻、秦与南派许多同学关系比较亲密,而我与孙大哥都是若即若离的边缘人物。也幸好是这样,我俩才没有卷入南北两派之间的一场大型武斗。
那是在1944年年初寒假期间的一个晚上,不知为什么两派由口角而动起武来,开头只有少数人参与,继而双方都有十余人介入,而且打斗相当激烈。幸好尚未使用器械,只限于拳打脚踢,总算未酿成流血事件。北方同学虽然孔武有力,但南方颇多久经战阵的打斗老手,罗翔更有一身过硬的擒拿武术,一人可以对付好几个人。闻刚由于身材高大,自然成为主力,就连平常斯文一脉的裔同学,由于学习京剧练过武功,也大显一番身手。总的来说,双方旗鼓相当,都没有吃好多亏,也没有占什么便宜。战场在食堂,离宿舍较远,所以躺在床上沉迷于看长篇小说的孙大哥与我当时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天吃早餐时,才听见闻刚与秦邦文谈论此事。这些斗士也真拿得起放得下,颇有江湖好汉风度。第二天居然风平浪静,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两派之间的嫌隙也没有从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