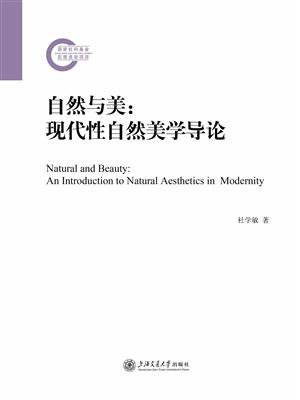一、自然观当代转型的伦理学范式的局限性
近代自然观的当代转型迄今一直以伦理学的方式推进。基于生态危机反思的生态伦理学与环境伦理学是其主要代表。加入中西比较而在更高合题层面诠释古代天人合一的各种思想,如以“诚”抵达“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叁”,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仁者”,都仍可视为人性的伦理扩张。主张超越人类本位伦理学的海德格尔,甚至不惜激活谢林泛神论而力图消弭康德自由与自然的分立,但即使是一种他一再强调的“恰当理解”的泛神论,若不愿倒向神性立场,其存有或“ereignis”是否拥有日常普遍的(而非精英的)现代生活经验
 ?是否在伦理学或思辨哲学之外存在着一种人类更加“合乎自然”的人性—自然观经验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主流范型的生态伦理学的局限性。
?是否在伦理学或思辨哲学之外存在着一种人类更加“合乎自然”的人性—自然观经验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主流范型的生态伦理学的局限性。
生态伦理学将伦理原则从人际范围扩大到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从而显著地改变了传统伦理学。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
第一,伦理调节固然以伦理关系双方的 差异性 为目标,但伦理关系的建立却以伦理关系双方具有某种 同质性 为基础。传统伦理学在人类性同质前提下协调与规范人类内部差异各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行为),而生态伦理学面对人类与自然物之间的异质性,如何寻找建立伦理关系的同质性基础?
第二,传统伦理尽管存在着伦理关系双方的不平衡而有道德施行与道德接受的区别(如成人救助儿童、贤者不计恩怨感化罪人),但道德接受者即使处于被动状态也依然是潜在的人性主体。因此,互为主体性是传统伦理学的一块基石。互为主体性以双方均具有意识与自我意识并能交流理解为前提。但是,迄今没有根据肯定自然物具有意识与自我意识,至少自然物不具有与人同等水平的意识交流能力。那么,在此情况下,一种具有伦理主体性质的自然观念依然须由人去判断,这种判断依据何在?同时,人如何可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又保持对自然伦理主体身份的尊敬?
第三,作为伦理尺度的善,其消极(弱化)功用在于限制与均衡伦理关系双方,其积极(强化)功用则在于提高伦理关系双方。因而善是既适宜于伦理关系双方又超出其上的中介。生态伦理学对善的这种中介性具有格外复杂的要求:一方面善须与人具有同质性(合乎人的目的),同时与自然也具有同质性(合乎自然的目的);另一方面善又须在均衡人与自然双方之外具有超越并提升人与自然的理想品质。生态伦理学是否能够指示这种善?
第四,依照当代元伦理学,任何伦理学的善必须拥有相应的直觉经验才能确证。生态伦理学这种成物成人又升华人与物的善,是否有其现实经验基础?落实生态伦理学此种善的直觉经验至关重大:它不仅是生态伦理学的公理前提基础,而且是生态伦理行为的实践基础。
当代生态伦理学基于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可分为两大立场:基于传统伦理学亦即人类伦理学的立场和基于生态系统的环境整体主义。其中,前者又可分为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学和将生态伦理视为传统伦理内在组成部分的观点;后者则将整体生态系统作为人与全部自然物的同质性基础。以上观点的介绍具体如下:
(一)基于传统伦理学亦即人类伦理学的立场
1.基于人类整体利益的生态伦理学
这类伦理学从功利主义传统确定人类利益,人类利益被理解为物种之一的人类生存发展。此种立场强调人类局部、近期利益与整体、长远利益的相关性,从人类整体长远利益出发克制、改变对自然竭泽而渔的急功近利态度,以人类持续发展的尺度取代高速增长的传统社会目标
 。但在这一尺度下,爱护自然与保护生态根本上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依然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材料与工具手段,而并非具有自身内在目的、与人互为主体的伦理对象。
。但在这一尺度下,爱护自然与保护生态根本上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依然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材料与工具手段,而并非具有自身内在目的、与人互为主体的伦理对象。
然而,即使是基于人类利益,但为了整体长远的持续发展而将自然纳入人类利益观念予以保护,这仍应视为对狭隘的人类自我中心状态的突破与超越。沿此方向,作为技术手段环节的生态保护会逐渐培养起尊重与热爱自然的新型态度及经验基础,从而反过来消解与改变人类自我中心的出发点。因此,这种基于人类利益而开展的形而下的生态保护运动,具有超出自身立场的形而上的人文教化意义。也就是说,这类生态伦理学更为根本的意义乃是其实践运动对自身传统观念的消解与转化。
这类生态伦理学理论在生态保护实践中引导着基于人类自我中心态强化对理性(康德所说“知性”:verstand)与科技的倚赖,即相信理性的统筹与算计而付诸科技实施,便可使生态系统更为持续长远并且最少负面后果地为人所用。这实质是人类统治更大的扩张,与上述人文教化方向相比,这一方面是强力性的。然而,康德早已论证并指出,作为整体的自然并非人类有限的知性(及其科技)所能把握的对象。整体的自然及其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数十亿年演化的成果,或者借用神学语言表述:那是上帝的创造。人类自身也只是这一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分支,人类有其不可超越的客观限定,他们只能看到人在宇宙特定位置角度可能看到的
 。
。
因此,基于人类整体利益而对自然生态在更大时空中凭借知性科技调节甚至重塑,这种为康德所禁戒的知性僭越,即使含有保护生态的好意,也可能伏有远非人类所能预料把握的危险后果。例如截源引水以保持水土,却可能毁灭某类鱼群的产卵地;捕杀狼以保护羊,却可能使食草动物过度繁盛而毁灭草原,以至在暴雨冲刷土壤后毁灭这一地带全部生物……生态学已不断向人类揭示出这类新的生态联系,然而它却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的揭示。康德因此从哲学上早已指出,要以有机生命亦即内在目的的方式去看待自然,这意味着对人类自我中心统治的知性技术手段的限定,也意味着真正以伦理主体来看待自然。
2.视生态伦理为传统伦理内在组成部分的观点
唯物史观已揭示人对自然的生产方式与人际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相互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则进一步揭示出“戡天”与“役人”的内在关联。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对自然的宰制与理性对人性爱欲的压抑,属于互为因果的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因而“解放自然”具有社会革命的意义:
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发现(或者主要是重新发现)自然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是一个同盟者,在剥削社会中,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
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

马尔库塞的学生莱斯则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滥用科技造成的生态危机,源于支配科技行为的“控制自然”观念,而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具有相互包孕的关系,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而不是自然。生态伦理从而被归结于社会伦理。
与前述第一种基于物种生存的人类观念的生态伦理学有别,在这里人性具有形上自由的意义:
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

生态保护根本上取决于人类自我中心立场的转变,这一方向已在本质上不同于前述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但是,将生态伦理完全还原为人类伦理,也就取消了自然独立的伦理主体地位。莱斯缺乏对自然本身的关注,他主张的人性自我转变也因而成为封闭性的主观修养,这种人性自我转变明显缺少超越性活动所必需的外在客观参照坐标。就此而言,莱斯未能看到确立异在于人的自然伦理主体同教化人欲之间的关联性,片面地将前者消解掉,割裂了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从而恰恰又坚持了一种新型的人类自我中心立场。
(二)基于生态系统的环境整体主义(environmental holism)
此种立场视有机生命与无机物为同一生态系统,强调彼此之间的依存性与可转化性,从而将整体生态系统作为人与全部自然物的同质性基础。
与之有别的另一类生态伦理学强调有机生命同质性,其实仍可归入环境整体主义。传统自然观念本已接受无机物与有机物的联系性,而当代信息论对信息交流普遍性的揭示、系统论关于系统整体的观念、耗散结构理论关于非平衡条件下无序混沌向有序组织与生命转化的研究,以及苏联科学家维尔纳茨基在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研究中关于生命与无机物循环关系的发现
 ,都支持了整体生态系统的观念。但仅凭生态系统同质性尚不足以建立生态伦理学:
,都支持了整体生态系统的观念。但仅凭生态系统同质性尚不足以建立生态伦理学:
首先,自然生态同质性无法提供人与自然超越自身的更高尺度,而只能在自然生态水平上调节、均衡人与自然。但如果仅此而已,这实质是将人类降低到与自然物(乃至无机物)同一的原始状态。尽管生命伦理学与环境整体主义都同时还强调物种个性多元化,但物种含义仍是指自然自在状态的物种。此种含义下人的“个性”与岩石或虎豹的“个性”并无重大区别。这一理论倾向忽视了人性超越自然的本质:人类今日之自觉与自然均衡,亦并非意味着返回自然同一体,而恰恰相反地是进一步超越自然人性物种中心狭隘眼界的表现。环境整体主义从人类中心利己主义提高到人与自然协同演进的“系统利己主义”(Frankena语),呼吁人类无私热爱自然,但都未超出利己主义或利他主义的功利主义眼界。这仅仅属于平等规范的消极(弱化)意义的善。
其次,由于环境整体主义贬抑人类积极性活动在生态伦理中的枢纽地位,从而又倾向于将承担此种整体主义的意识主体归诸神或泛化于物(物活论:hylozoismus)。整体主义极力引导人否弃人类立场而与神或万物同一,但神意或万物有关观念的实际承担者却仍然是人。这里不仅存在拔自己头发离地的悖论,而且潜伏有僭越神性位格的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因为这种关于万物是否有灵的判断恰恰属于上帝的眼光
 。
。
最后,由于自然宗教与活物质的科学理性观念在现代人类中均缺乏普遍经验基础,所以环境整体主义迄今尚未找到环保实践所必需的感性经验资源,而被人类中心主义攻击为少数人的乌托邦。
整体主义的教训表明,生态伦理学不可能离弃人类根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能因循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