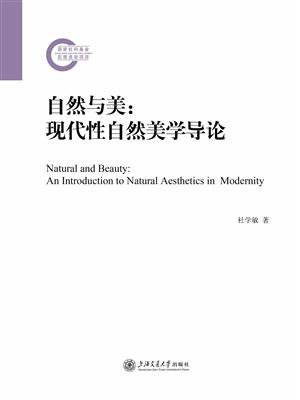二、自然美:一种有待阐释的生态经验
在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中,有一种普遍而悠久的经验形态,它既非自然宗教崇拜,又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权衡,而是对自然由衷地赞美。这就是自然审美经验。
迄今各派生态伦理学均已注意到了自然美对于生态伦理学的积极意义,但却存在着如下缺陷:
第一,把自然美与实用价值等量齐观,视自然美为人类游乐与怡悦的手段。由于这种观点只停留于审美价值的外层、甚至贬低、歪曲了审美价值,因而已受到广泛的批评
 。
。
第二,即使超越实用价值予自然美以形上精神意义,但仍将自然美片面地纳入人类中心主义而视为人类主体性文化形式。
第三,缺乏哲学水平的概括,未能从美学与伦理学结合的角度揭示自然美在生态伦理学中的地位。因此,即使如E.Hargrove、John Muir那样一再从经验层面强调自然美对于生态伦理学的特殊重要性,甚至美国生态保护之父A.leopold将生态伦理尺度概括为“完整、稳定和美丽”三原则已在事实上承认审美对于生态伦理学的本体意义(三原则中“完整”也可归于审美形式规律),但学界对此依然缺少哲学论证。
当代生态伦理学缺乏哲学本体论高度的自然美理论,这与其注重社会运动而忽略形上深层理论的实践倾向特性有关。但从美学角度看,当代美学依据对康德美学的流行阐释将自然美视为人类主体性形式,从而阻断了自然美与自然的实质性关联,使自然美自始便无法从逻辑理论上进入生态伦理学。
然而,反独断论是康德哲学的基本特色,康德审慎的态度使其哲学保持着巨大的阐释空场:“由于自然界问题异常复杂,解决它时不可避免地将遇到一些暧昧之处。这种巨大的艰难可以使人原谅我仅仅正确地指出了原理,而未能明确地把它表述出来。”

因此,有必要重新阐释康德的自然美理论,以便为生态伦理学提供可能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