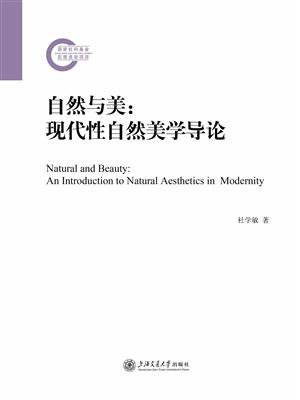三、康德自然美理论的悖论:一个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洞口
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变,是以人类主体性文化建构取代客体中心地位。这一转变在审美判断中达到了主体性极致:“一个客体的表象的美学性质是纯粹主体方面的东西,这就是说,构成这种性质的是和主体而不是客体有关。”
 物自体(Ding an sich)在认识活动中尚是感性刺激来源与知性系统化焦点(目的),在道德中则转化为自由的客观根据,而审美对象所呈现的却只是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是人文性(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但问题是:应如何理解人文性?
物自体(Ding an sich)在认识活动中尚是感性刺激来源与知性系统化焦点(目的),在道德中则转化为自由的客观根据,而审美对象所呈现的却只是主体的合目的性的形式,也就是说,审美对象是人文性(以主体自身为对象)的。但问题是:应如何理解人文性?
自然美“作为形式(仅是主体的)合目的性的概念来表述”
 ,而“对于自然界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而经由某一种暗换付予了一自然界的对象(把这对于主体里的人类观念的崇敬变换为对于客体)”
,而“对于自然界里的崇高的感觉就是对于自己本身的使命的崇敬,而经由某一种暗换付予了一自然界的对象(把这对于主体里的人类观念的崇敬变换为对于客体)”
 ;甚至“自然界在这里称作崇高,只是因为它提升想象力达到表述那些场合,在那场合里心情能够使自己感觉到它的使命的自身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
;甚至“自然界在这里称作崇高,只是因为它提升想象力达到表述那些场合,在那场合里心情能够使自己感觉到它的使命的自身的崇高性超越了自然”
 。因而,康德说自然崇高审美中的人是“自我推重”的。
。因而,康德说自然崇高审美中的人是“自我推重”的。
康德上述论点典型地表现着启蒙主义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文主义(humanism)热情,它邻近着人类主义(anthropologism)。这确是康德哲学的基调。沿此方向,人类中心主义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其表现或是将审美对象纯归于个体主观性“审美态度”(英美距离说、快感论、联想论等),或是将审美归于主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中国实践派、苏俄社会派)。后者虽然攻击前者的个体主观意识基点,并强调主体性心理结构的社会历史客观背景,但其实践本体基于人类物种的生存劳作,因而并未超出人类中心主义
 。
。
但康德并非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者。西方的精神信仰传统在康德哲学中成为抵制唯我主义与人类主义(anthropologism)的重要支柱,并保护了本体论
 。康德哲学这一方面的一个深刻兆象便是时隐时现的对物自体的信念(belief),它在《判断力批判》中特别表现为第42节(“关于对美的智性的兴趣”)将自然美客体化(自然主体化)的倾向。
。康德哲学这一方面的一个深刻兆象便是时隐时现的对物自体的信念(belief),它在《判断力批判》中特别表现为第42节(“关于对美的智性的兴趣”)将自然美客体化(自然主体化)的倾向。
在第42节开始,康德针对人工美饰背离道德的文明流弊而强调:“对于自然美具有一种直接的兴趣(不单具有评定它的鉴赏力)时时是一个良善灵魂的标志。”
 他进一步展开分析:
他进一步展开分析:
谁人孤独地(并且无意于把他所注意的一切说给别人听)观察着一朵野花,一只鸟,一个草虫等的美丽形体,以便去惊赞它,不愿意在大自然里缺少了它,纵使由此就会对于他有所损害,更少显示对于他有什么利益,这时他就是对于自然的美具有了一种直接的,并且是智性的兴趣了。这就是不但自然成品的形式方面,而且它的存在方面也使他愉快,并不需一个感性的刺激参加在这里面,也不用结合着任何一个目的。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假使人们欺骗了他而是把假造的花(人能做得和真的一样)插进土地里,或把假造的雕刻的鸟雀放在树枝上,后来他发现了这欺骗,他先前对于这些东西的兴趣就消失掉了;但可能另一种兴趣来替代了这个,这就是虚荣的兴趣,他把他的房间用这些假花装饰起来以炫别人的眼睛。自然是产生出那美的;这个思想必须陪伴着直观与反省;人们对于他的直接的兴趣只建立在这上面。
否则只剩下一种单纯的鉴赏判断而绝无一切的兴趣或只是和间接的,即关系着社会的兴趣相结合着,但后者对于道德上善的思想并不提供确实可靠的指征。
这种自然美对艺术美的优越性,尽管自然美就形式方面来说甚至于还被艺术美超越着,仍然单独唤起一种直接的兴趣,和一切人的醇化了的和深入根底的思想形式相协和,这些人是曾把他们的道德情操陶冶过的。

康德反复强调的对自然美的“直接的兴趣”,如他已排除的,并非对自然占有的感性(亦即自然)欲望,那属于物种人类主义(anthropologism),也不是纯粹美的主体性形式感,那只是将自然作为拟人类比的形式符号——而是对“自然本身”的喜爱与惊赞。这意味着承认并尊重自然内在的目的亦即一个客观自在的自然主体。自然美的客体化也就是自然主体化:自然美从人类主体性形式转向主体自然,从而独立于人类而客体化。康德指出,这种对自然主体的尊重,是道德的表现。这可以理解为是人际道德的充溢延伸或泛化;但它又是道德感“最可靠”的表现,因而又反过来是人际道德的基石尺度,或者可以理解为是道德最纯粹、最高品格的表现。从而,人对自然的伦理态度不仅对于人际道德,而且对于整个本体都具有至关重大的意义。
上述结论与康德哲学的哥白尼式转变在表面上似乎是相反的:它又把人的眼光投向了外界客体。然而,康德在这里同样坚持着他的基本立场:一个实在论的自然客体概念是非法与僭越的,一种物活论(Hylozoismus)式的主体自然观念同样是臆断性的。
在《判断力批判》目的论部分,康德从对有机生命体的特殊认识要求出发,设定自然目的概念,以提供机械论无法承担的统一性原理。“这个目的概念就会是理性的概念(idea)而把一种新的因果作用引入科学中去。”
 因此,自然目的亦即主体自然概念,仅仅是非实在性的客观合目的性形式。这种主观上充分而客观上无法证实的自然目的概念,乃是一种“信念”(belief)
因此,自然目的亦即主体自然概念,仅仅是非实在性的客观合目的性形式。这种主观上充分而客观上无法证实的自然目的概念,乃是一种“信念”(belief)
 。“信念作为一种习惯(habiytus)而不是作为一种行为(actus)来看,乃是理性在其确信处在理论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的真理的那种道德思考方式。”
。“信念作为一种习惯(habiytus)而不是作为一种行为(actus)来看,乃是理性在其确信处在理论知识所能达到的范围以外的真理的那种道德思考方式。”
 与批判哲学将认识论极限的物自体理念转换成道德本体的自由信念一致,目的论批判终于从认识论功能需要的自然客观合目的性导引出作为最高目的的道德的人。因此,康德关注自然的立场依然是道德人文主义:“对于自然的很大赞赏的来源——这个来源与其说是外在于我们的,毋宁说是处在我们的理性里面的。”
与批判哲学将认识论极限的物自体理念转换成道德本体的自由信念一致,目的论批判终于从认识论功能需要的自然客观合目的性导引出作为最高目的的道德的人。因此,康德关注自然的立场依然是道德人文主义:“对于自然的很大赞赏的来源——这个来源与其说是外在于我们的,毋宁说是处在我们的理性里面的。”

然而,本文关心的是康德论述中包含的如下悖论式关联:虽然道德的人关注自然本身,但关注自然本身才是真正道德的;或者说,人对自然目的的赞赏源于人对自身道德主体的赞赏,而人只有赞赏自然目的才能真正成为道德主体。从而可以对康德关于自然以道德的人为最后目的的命题做出如下重要补充:道德的人是自然的最高目的,而道德的人以自然目的的信念为最高道德。
这样,人对自然的道德态度亦即自然目的信念在人际道德与本体道德中依然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关键地位。问题在于,自然目的信念的发生学基础是什么?康德在设定了自然目的概念(自然客体合目的性形式)之后指出:“但是这个假定的正确性还是很可疑的,虽然自然众美的现实性正公开在我们的经验的面前。”
 也就是说,自然美已经真实地向人类提供了自然目的的经验,但这一经验的内在结构依然有待说明,否则我们就仍像当代生态伦理学那样仅仅停留在经验现象描述中。
也就是说,自然美已经真实地向人类提供了自然目的的经验,但这一经验的内在结构依然有待说明,否则我们就仍像当代生态伦理学那样仅仅停留在经验现象描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