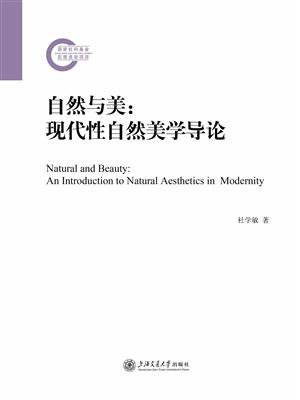四、自然美: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善
审美作为主体的合目的性形式运动,具有合主体目的性与合客体目的性的两极运动结构。即使是纯粹美的审美愉快,也“不仅表示着客体方面联系到主体中按照自然概念而反味着的判断力时的合目的性,而且,反过来,表示着主体方面按照着自由概念联系到对象的形式乃至无形式的对象时的合目的性”
 。主体合目的性形式感虽然不提供实在客体概念,但仍然以其普遍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审美对象。审美对象虽然只是客体表象,但仍可作为宾词。后来罗素将之列为伪专名的摹状词(description),以从逻辑上防止将其实在对象化。但这也正表明了审美对象所拥有的实在感。这当然并非对实在经验对象的感知,但这种对非实在对象实在感的追求,却是人类最深刻的精神现象之一
。主体合目的性形式感虽然不提供实在客体概念,但仍然以其普遍有效性提供了一个审美对象。审美对象虽然只是客体表象,但仍可作为宾词。后来罗素将之列为伪专名的摹状词(description),以从逻辑上防止将其实在对象化。但这也正表明了审美对象所拥有的实在感。这当然并非对实在经验对象的感知,但这种对非实在对象实在感的追求,却是人类最深刻的精神现象之一
 。如康德所说,“逻辑的述项和实在的述项的相混淆(所谓实在述项是确定一个东西的述项)所引起的幻象几乎是不可纠正的”
。如康德所说,“逻辑的述项和实在的述项的相混淆(所谓实在述项是确定一个东西的述项)所引起的幻象几乎是不可纠正的”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工作之一即是揭露这种超感性实在论的幻象性。但人类这种对形上观念实在性的自发追求,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归位于道德本体:“这样,一切超感性的东西才不能都认为是虚构,而且它们的概念也才不是都缺乏内容:而现在实践理性自身事前并不曾与思辨理性商定,就给因果性范畴(自由)的超感性的对象保证了实在性(虽然这个范畴还是作为一个实践概念,专供实践的用途);这就通过一事实证实了在思辨理性方面原来只能被思维的那种东西。”
。《纯粹理性批判》主要工作之一即是揭露这种超感性实在论的幻象性。但人类这种对形上观念实在性的自发追求,却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归位于道德本体:“这样,一切超感性的东西才不能都认为是虚构,而且它们的概念也才不是都缺乏内容:而现在实践理性自身事前并不曾与思辨理性商定,就给因果性范畴(自由)的超感性的对象保证了实在性(虽然这个范畴还是作为一个实践概念,专供实践的用途);这就通过一事实证实了在思辨理性方面原来只能被思维的那种东西。”
 这样,西方哲学史上从在理念中寻找真实存在的爱利亚学派与柏拉图,到中世纪唯实论、宗教改革运动先驱者威克里夫等与唯名论的抗衡,其形上普遍实在观的道德性质经康德分离认识论的纠缠之后,被格外清楚地确定下来了
这样,西方哲学史上从在理念中寻找真实存在的爱利亚学派与柏拉图,到中世纪唯实论、宗教改革运动先驱者威克里夫等与唯名论的抗衡,其形上普遍实在观的道德性质经康德分离认识论的纠缠之后,被格外清楚地确定下来了
 。
。
因此,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没有实在对象以及审美只是主体的合目的性形式运动的强调,只是从认识论角度而言。但从道德本体角度来看,审美判断却显示出对道德客体强烈追求的指趋。审美中不仅合主体目的性(自由)是导向道德的(这已为人们普遍肯定),而且合客体目的性(自然)也是趋向于道德的。在鉴赏判断第二契机的研究中,康德将后一方面解释为合客体概念性,即它是“诸表象能力在一定的表象上向着一般认识的自由活动的情绪。”
 这在当代美学中被普遍地理解为“合规律性”,即它是接近于认识的。本文基本同意康德及其研究者的上述判定。但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
这在当代美学中被普遍地理解为“合规律性”,即它是接近于认识的。本文基本同意康德及其研究者的上述判定。但是,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
合客体目的性即“向着一般认识的自由活动的情绪”,导致审美对象(客体)观念(idea)的呈现。审美由此可有两个方向:
第一,以合客体目的性(自然、客体概念方向)与合主体目的性(自由,道德本体方向)相统一为重心,主体怡悦于此种两个方向合目的性情绪的来回冲荡交流协谐。在此种审美状态中,主体自娱于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平衡而并不神往道德本体与关注审美客体。也就是说,审美主体合目的性两种形态(合主体自由道德与合客体自然)都不积极推进各自的运动方向,而只作为形式化(虚拟性)运动汇聚于审美主体的感知情绪层面。这属于怡情,而非悦志。
第二,合主体目的性与合客体目的性两极运动强化各自运动方向,双方又在更高层面达到统一。合客体目的性的强化使审美客体凸出而吸引主体,这使此前主体只是借物娱情的自我中心态将重心移向客体一方,从而由(自我)怡悦升华为神往与倾情。如果说此前合客体目的性尚需借助弱化的认识(合客体概念)模式形成审美客体意象,那么当主体忘我投入地关注神往审美客体时,已全无认识意味:审美客体本质上属于理念(idea)的象征,它不是认知的对象。如前所述,这种对于超实在对象实在感的肯定,实质是爱与向往极致的信念,它已进入道德本体。如此一来,它与合主体目的性(自由)的道德本体便融合了。
上述分析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42节“对自然的直接兴趣”的强调含义。从以自然为审美鉴赏形式契机的主体自我欣赏转变为“对自然的直接兴趣”,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借景抒情式主体怡悦转变为自然审美客体的凸出,合客体目的性的运动不断强化审美客体一极,它吸引人沉静下来,倾心与神往于自然美对象;第二,合客体目的性运动的继续强化使自然美进一步客体实在化,当这种由爱与向往推动的实在感强化到更高程度后,作为审美客体的自然美便与作为自然美物质载体的自然实在重合为一。由此所引起的后果是,一方面自然实在承受了人类对自然美的赞赏而合目的化,同时自然美也自然实在化而使主体性的合目的性形式趋于客观合目的性、甚而客观实质目的化。这意味着一个拥有自身内在目的价值、从而享有主体地位的伦理对象的自然的诞生。这已经不再是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形式对自然形式的借用(纯粹美),也不是为知性认识所假设的客观合目的性的先验原理,而是拥有审美——伦理尊敬与惊赞实在经验的自然伦理主体:“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维,它们就给人心灌注了时时在翻新、有加无已的赞叹(Bewunderung)和敬畏(Ehrfurcht):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惊赞”(Bewunderung)并非知性概念判断而是情意判断。因此,对自然目的的惊赞并不是回到自然实在目的的物活论,而依然是前述“信念”,即它是道德性的。如前所述,自然目的并非自然客体合目的性这一认识论的先验原理的推导结论(那恰是被禁止的),而是审美主体内合客体目的性一极运动的产物,它标志着自然美从主体合目的性向客体合目的性超越的顶峰与极致,同时也标志着人性超越人类自我中心所达到的道德最高境界:在对一个异己并异于人类的自然目的(自然主体)的无私而由衷地赞美中,人际关系中超越个体自我中心的道德自由以更为普遍彻底的形式出现在超越人类自我中心的水平上。
因此,向人类呈现为伦理主体的自然同时依然是审美客体。自然美作为伦理主体自然的渊源基础,同时也正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善。它具有以下五点意义:
第一,自然美是唯一不贬低人性主体而承诺自然主体的基础,因而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同质性基础。可见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它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物种人类的利益,也不是环境整体主义所主张的有机系统,更不是神力。基于这一同质性,自然美具有调节、均衡人与自然关系的善的弱化尺度意义。
第二,由于自然美是主体(人类)合目的性包含的合客体目的性一极突破主体中心态,又在更高层面达到与合主体目的性统一的产物,因而既关联又高于人与自然。自然美提供了提升人与自然双方的统一的更高的善:自然美的存在使人不仅实现了对个体自我中心的超越,而且实现了对物种人类自我中心的超越;自然在自然美中既摆脱了受人宰制的地位,也未流于自发调节的荒蛮丛林法则,而是在与人类主体合目的性统一协谐、并获得帮助的人化形式中提升合自然目的性系统
 。
。
第三,无论作为信念的自然目的还是作为主体的合目的性形式的自然美,都系于人超越自我的意识。因而,人在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承担着道德施行者的责任。
第四,作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善,自然美审美本身即是直觉经验,从而可以提供元伦理学所要求的关于善的直觉前提。
第五,自然美审美经验的人类普遍性为实践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提供了普遍的感召经验。
这五点意义是对本文开始所列举的生态伦理学四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它们同时表明,自然美已满足了生态伦理学所必需的逻辑前提与经验基础。
这是否意味着,自然美比伦理善更切合于自然观的当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