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凡为圣:
二胡与《二泉映月》
二胡是“胡人”的乐器吗?
小泽征尔说:这是应该跪着听的音乐
让二胡登堂入室的刘天华
“瞎子阿炳”与杨荫浏

图1.14 二胡(中国艺术研究院藏品)
二胡,是现今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之一,但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这件乐器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因为名字里带一个“胡”字。据说从唐朝开始,就有一种类似二胡的乐器叫奚琴,“奚(部)”也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和鲜卑族有关系。《乐书》中记载的奚琴,不是用马尾弓来拉的,而是用竹片,“两弦间以竹片轧之”。到了宋朝,沈括《梦溪笔谈》里有一句诗:“马尾胡琴随汉车。”“马尾胡琴”就和今天的二胡是一样的了。当然,胡琴是一大类,有二胡、京二胡、低音二胡、四胡等。二胡这个乐器在中原出现和发展得都比较晚,虽然宋朝以后都有记载,但一直到明清,仍然只是在民间流传。在北方,二胡基本上只是各个民间戏剧的伴奏乐器。在南方,除了一般的娱乐,二胡主要是在民间仪式中作为伴奏乐器。近代,二胡的发展与道教关系密切。道教分全真派、正一派。正一派的道士在民间俗称“火居道士”,一般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或是手工艺者,或是农民,在业余时间给民间的老百姓做法事、做斋醮,其中二胡就是民间火居道士手中的乐器。
讲到二胡在近代的发展,必须谈到两个人。一个就是道士华彦钧,即大名鼎鼎的“瞎子阿炳”。他是无锡人,其父就是火居道士,他的道观叫雷尊殿,在无锡。他把这座道观传给华彦钧的同时,也把自己的音乐技艺和才能传给了他。华彦钧作为雷尊殿的一个小道士,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讲到华彦钧,还必须讲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学家杨荫浏。杨荫浏先生也在无锡出生,从小喜欢音乐,小时候曾经跟一个叫颖泉的道士学习中国的民族乐器。杨荫浏后来也跟华彦钧学过琵琶,但由于华彦钧天性比较放荡不羁,而杨荫浏的家庭很注重礼教,所以后来就不让杨荫浏再跟他学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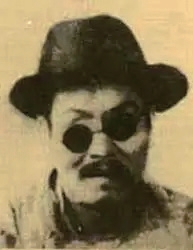
图1.15 阿炳

图1.16 杨荫浏
杨荫浏在上大学之前,还遇到过一个基督教的美国女传教士,叫郝路易。杨先生不但跟随掌握中国传统音乐的道士学过民间音乐,跟当时的昆曲大家吴畹卿学过昆曲,同时又跟这位美国传教士学钢琴、作曲、和声,所以中外兼通。他最早的论文《中国音乐史纲》就是用英文写的。杨先生还研究过佛教音乐、基督教音乐。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几个基督教会联合编辑了一本中国基督徒使用的赞美诗集,即著名的基督教圣诗集《普天颂赞》,杨先生是其中唯一专职的编辑,是实际的主编。在这部中国化的圣诗集中,杨先生专门用中国传统的乐调,比如《老六板》来配合基督教的歌词,努力促进基督教赞美诗的中国化。可以说,杨荫浏是基督教音乐中国化的第一人。在几十年的音乐研究当中,杨先生以他渊博的学识和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深刻了解,成为中国音乐史的奠基性作家,他的两卷本《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至今仍是所有学习中国音乐史的学子的必读书。
1950年暑假,杨荫浏和琵琶演奏家、音乐学家曹安和(杨先生的表妹,也是他最重要的助手)从北京回到无锡,去寻访教过他的华彦钧。但是这个时候,华彦钧的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大家都叫他“瞎子阿炳”。阿炳中年失明之后,又把雷尊殿丢掉了,所以生活无着,变成了一个沿街乞讨的乞丐,每天去街上拉二胡。那个时候,无锡的人们无论晴天雨天,总会听到石板路上传来的盲人手拿竹竿“嘟嘟嘟”点地的声音,然后就会听到一阵悠扬的二胡声。这就是阿炳的后半生。当然,阿炳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有悲惨,也有他的努力、奋斗和追求,包括他的家国情怀。阿炳是有文化的,他知道一些发生的时事,就会迅速地把这些时事变成他口里用民歌小调所唱的“早间新闻”。所以,他不但拉二胡,而且自编自唱,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他自己创编的随口吟唱的类似新闻播报里,包含着他内心和绝大部分中国人一样的家国情怀。
当杨先生找到阿炳的时候,他已经几年不动乐器了,贫病交加,只有一个叫董彩娣的农村妇女始终陪着他,是他的伴侣,也是他的拐杖。据董彩娣讲,在此之前不久,阿炳发现他的二胡的皮被老鼠啃破了,就觉得老天不再让他演奏了,于是他就把琵琶、二胡通通换了衣食。杨先生这次找他,是有一个重要任务:把这位流落民间的天才音乐家的音乐录下来,以免湮没无存。他从北京带来一台当时最新、最先进的德国产钢丝录音机和昂贵的录音带。
因为阿炳已经三年不近乐器,也没有乐器了,于是杨先生就从乐器店给他借来了一把琵琶和一把二胡。据说录音的时候,阿炳没有试奏,拿起来就演奏,拉的第一首曲子就是今天誉满全球的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二泉映月》。演奏之后,杨先生问他这首曲子叫什么,他说没名字,就是随手拉的。阿炳经常拉这首曲子,虽然有一个基本固定的旋律,但每次即兴演奏的时候,还是有所不同。杨先生说,没有名字不行。因为无锡有所谓的“天下第二泉”,于是两人商定就叫《二泉映月》,借鉴杭州的“三潭印月”。实际上,这首曲子和天下第二泉无关,和天上那一轮看尽人间悲苦的月亮也无关,它只是阿炳个人苦难生活的写照,也是一直回荡在他胸中的感情和乐思的升华,是一个伟大的民间艺术家纯粹的艺术创造。他创造了这首曲子,但从没想到有一天会被这么一台机器录下来,更会在他百年之后,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代表性曲目。

图1.17 录制《二泉映月》的钢丝录音机和钢丝带(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品)
20世纪70年代,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造访中央音乐学院,听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为他演奏了这首乐曲。没过几天,日本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个随访记者的文章,报道小泽征尔听了这首音乐之后的反应,文章写道,当时他用手捂着眼睛说:“这样的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2007年,我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负责人,曾带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团”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展览和演出,在那场全部由中国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的节目中就有这首二胡曲《二泉映月》。
在演出现场,我用中文给大家做了导聆之后,演奏家开始演奏。从现场的气氛当中,我不但感受到大家都听懂了这首音乐,听懂了我的介绍,而且感到现场有一种和音乐相融的神圣感。散场后,我问年轻的翻译:“我讲的小泽征尔的这句话‘这样的音乐,是应该跪着听的’,你是怎么翻译的?”她说:“我没有直译,因为说这样的音乐应该跪着听,大家会不理解。我知道西方人有天主教,他们对天主教的音乐非常尊敬,音乐里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这么多伟大的音乐家,所以我是这么翻译这句话的:‘听这样的音乐,就应该像在教堂听圣乐一样。’”所以,所有观众听的时候都非常安静,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而这样一种像进了庙堂一般的神圣、肃穆、敬仰的情绪,自然而然地让来自一百多个不同国家的来宾理解了这位中国盲人艺术家的心声,演出非常成功。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杨先生所能带去的钢丝录音带太少了,阿炳只给杨先生录了六首曲子,即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以及三首琵琶曲《龙船》《大浪淘沙》《昭君出塞》。最遗憾的是,他们录了这几首曲子,录音带用完之后,阿炳找到感觉了,杨先生也找到感觉了,说:“我跟你合奏吧。”在无锡流行的十番锣鼓,就是民间的雅乐,也是民间即兴演奏的一个乐种,是阿炳和杨先生自幼学习、已经融化在血液里的音乐。据说,当时二人合奏时心领神会,配合默契;独奏时各显其能,出神入化,令在场的人叹为观止。曹安和先生后来回忆说:“他们两个的演奏,如果能留到今天该多好啊!”那将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两位大家难得的绝唱,堪称世纪绝响!遗憾的是,因为所带的录音带不够,为了能继续录制阿炳的音乐,就把这一段洗掉了!这是中国音乐史上没有办法补救的一个遗憾。
杨先生和阿炳约定,让阿炳留下乐器,再好好地练一练,熟悉熟悉,明年再去给他录音。阿炳的脑子里有多少像《二泉映月》这样的乐曲呢?据他自己讲,有三百首左右,假如这三百首乐曲都能留到今天,该是一个多么大的民族音乐的宝库。可惜的是,阿炳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杨先生离开无锡回到北京三个月之后,阿炳就去世了。他所有的音乐和他一起离开了世间。从古至今,我们不知道在传统社会有多少和阿炳类似的民间音乐家,像一根根野草一样长出来,又像一粒粒草籽一样被风吹得无影无踪。这些曾经的生命、曾经的天才,也不知道曾经给了多少人艺术的享受,安慰了多少颗和他们同样凄苦的心。但是,这些卑微的存在,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文字,更不可能留下声音。因为有了杨荫浏这样一个对中国民族音乐怀着深厚感情的音乐学家,世界才知道在20世纪初的中国,有过一个天才叫“瞎子阿炳”;才知道在当时无锡狭窄的弄堂里,曾日夜飘荡着《二泉映月》如泣如诉的深沉乐声;今天的中国人,才有了令我们充满文化自信、可以代表中国民族音乐的六首不朽经典。
从民间到音乐厅
假如说“瞎子阿炳”继承了二胡艺术里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这一节提到的另外一个人则开创了二胡新的历史和篇章,把中国民族乐器和传统音乐与西方的音乐理念、技术结合起来,创造了二胡发展的新的途径,这个人就是刘天华。
刘天华是著名的作曲家、二胡演奏家,他家兄弟三人都在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建设当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大哥刘半农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也是“五四运动”的闯将。他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很多新的文化建设的设想,其中包括推行简化汉字的想法。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先生、胡适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中国的文化靠繁复的汉字来传承,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人是文盲,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刘半农和李家瑞合编了一本《宋元以来俗字谱》,为后来的简化字奠定了基础。同时,作为语音学家,他还把西方语音学、音韵学介绍到中国,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语音学、音韵学。刘半农还创造了“她”“它”这两个不同的第三人称,一直使用至今。新文化运动以前,一个“彼”字表示所有第三人称,但“彼”是男还是女?是人还是物?因为刘半农的发明,汉语书写才分清了男、女、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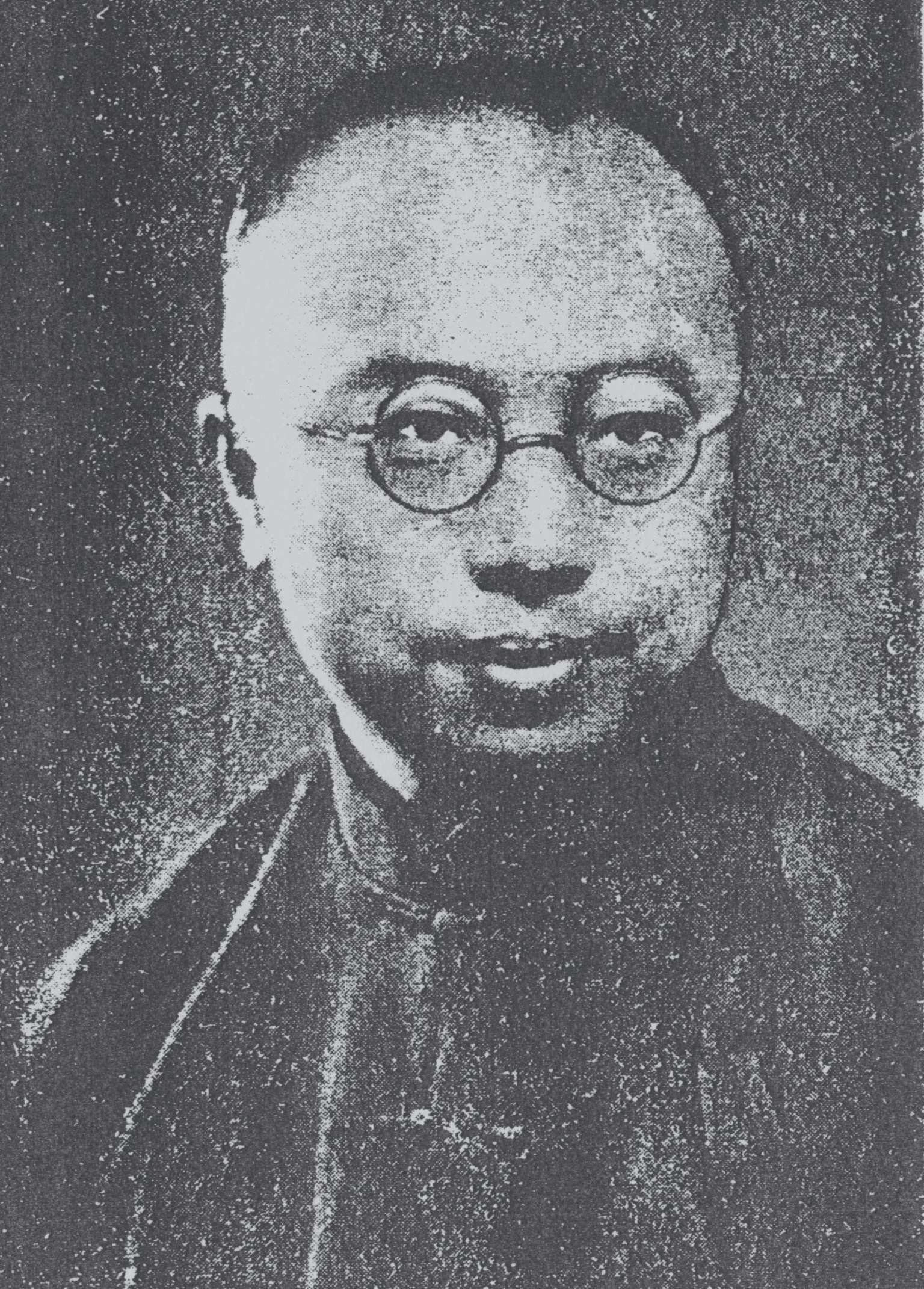
图1.18 刘天华
刘天华从小喜欢音乐、关心国事,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在自己的家乡江阴加入童子军,做小号手。后来他跟着哥哥到上海,在当时的开明剧社做音乐伴奏,这期间学习了西方的一些乐器。他对中国乐器的学习开始得更早,曾经走访很多地方,用游学的方式去学古琴、琵琶、三弦等。有一次,生病的他偶然到集市上买了一把二胡,就开始向民间艺人学习,并且自己研究。他受哥哥大力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逐渐有了一个设想,叫“国乐改进”,研讨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如何面向现代化和面向世界,如何让我们古老的音乐焕发新的青春。他和其兄一样,也是学贯中西,既会拉二胡,也会拉小提琴,于是他就对二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进:一方面是对二胡本身进行了改革,将定弦音高固定,使二胡的音高和调性得以统一,同时扩大了二胡的把位,从传统的一把、两把延展到四把、五把;另一方面是改进了演奏技巧,将小提琴演奏中的揉弦和古琴弹奏技法中的泛音用在了二胡上。
刘天华不但对二胡这件乐器进行了改良,而且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多首新创作的二胡作品,集中保存在《刘天华二胡曲集》里。他的作曲既有传统的乐思和新鲜的旋律,又不与中国人传统的审美习惯相悖。他不但在二胡音乐中引进了西方的进行曲体裁,而且在一些乐曲创作中,明显融会了西方音乐的调式和旋律进行,比如在《光明行》《空山鸟语》中,就大胆使用了西方的分解和弦
 式的旋律进行。应该说,二胡这件在民间为草台班子伴奏,在城镇街头用以讨饭的乐器,在刘天华的手里才华丽转身,得以登堂入室。刘天华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二胡独奏音乐会的人,他把一件粗糙的戏曲伴奏乐器完美地转化成了一件独奏乐器,不但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提升了它的品位,也提升了二胡在乐器家族和社会生活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刘天华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良宵》《病中吟》等。其中有一首作品,他其实写得很早,但是完稿比较晚,就是《空山鸟语》。
式的旋律进行。应该说,二胡这件在民间为草台班子伴奏,在城镇街头用以讨饭的乐器,在刘天华的手里才华丽转身,得以登堂入室。刘天华是第一个在中国举办二胡独奏音乐会的人,他把一件粗糙的戏曲伴奏乐器完美地转化成了一件独奏乐器,不但丰富了二胡的表现力,提升了它的品位,也提升了二胡在乐器家族和社会生活里的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刘天华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大家熟悉的《良宵》《病中吟》等。其中有一首作品,他其实写得很早,但是完稿比较晚,就是《空山鸟语》。
唐朝大诗人王维有一首诗: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既冷寂又带着些许温暖,既神秘又似乎常见的意境。这充满禅意的诗给了刘天华空灵、幽远的想象和灵感,仿佛是他在家乡的深山里常常见到的场景:青山绿水,万籁无声,没有人言,只有鸟语。于是,他创作了这样一首向自然致敬的音乐,用模拟的禽鸟的声音来歌颂大自然,用禽鸟的啼吟来反衬山林间的寂静。
从“瞎子阿炳”到杨荫浏和刘天华,中国音乐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天才的创造,使中国这件原本籍籍无名的草根乐器——二胡,从传统到现代,从继承到发展,百年演进、潮涨潮落,最终成为今天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了解了二胡的发展史,我们就更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民族音乐复兴、发展、创新,并把民族音乐真正推向世界中央的理想奠定基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