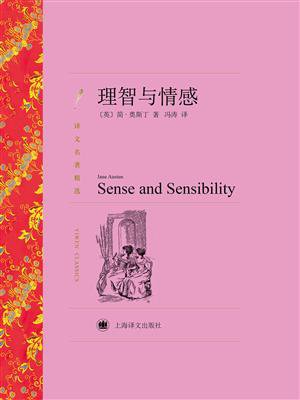|
第八章 |

|
詹宁斯太太是个寡妇,丈夫死后给她留下一笔充裕的财产。她只有两个女儿,她都眼看着嫁到了好人家,所以她如今无事可做,只想着成全全天下的男婚女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她总是热心积极,但凡能力所及,从不错过机会,一心替她认识的所有青年男女筹划婚事。她眼睛尖得很,最善于发现男女间倾心暗许的苗头,最喜欢点破某位小姐已经迷住了某个小伙子,非常享受眼看着她们脸红心跳的乐趣。凭借着这种洞察力,刚到巴顿庄园不久她就宣布布兰登上校已经深爱上了玛丽安·达什伍德。他们第一晚聚在一起的时候,她心下就颇有些怀疑是这么回事儿,因为玛丽安在唱歌的时候,他听得是那么用心;等到米德尔顿一家前往小别墅回拜用餐,他再次听她唱歌的时候,这事儿就已经确定无疑了。一定是这么回事儿。她已经有了十成的把握。这倒是一桩美满姻缘,因为 他 很有钱而 她 很漂亮。詹宁斯太太自打因为女婿的关系知道了有布兰登上校这个人以后,她就一心想给他择配个好太太;而她但凡见到一位漂亮姑娘,又总是想为她找个好丈夫的。
这件事对于她眼前的好处来说也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就为她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好材料来开他们俩的玩笑。在巴顿庄园,她打趣上校,到了小别墅,她就打趣玛丽安。对于上校而言,只要她的玩笑只牵涉他一个人,倒是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但是在玛丽安这边,起先她完全不明就里,等到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究竟该是笑它的荒诞无稽呢,还是该斥责它的鲁莽无礼,因为她认为这是对上校年事已高以及对他身为一个老单身汉的孤凄无助的无情嘲弄。
达什伍德太太倒是很难想象,一个比自己还要年轻五岁的男人,在她女儿那种青春少女的心目中就已经是老迈得无可名状了,于是就冒昧地替詹宁斯太太开脱,说她不太可能是故意拿他的年龄寻开心。
“可是至少,妈妈,你没办法否认这种说辞是荒唐的吧,尽管你不认为这是出于恶意。布兰登上校自然是比詹宁斯太太年轻一些,可他老得都可以做 我 父亲了;就算是曾经有过恋爱的精神头儿,也肯定早就心如死水了。这太荒谬可笑啦!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免受这种奚落呢,如果年老和病弱都保护不了他的话?”
“老弱!”埃莉诺道,“你说布兰登上校老弱?他的年纪在你眼里也许比在母亲眼里要大得多,这可以理解;可是你总不至于自欺欺人地故意看不见他的手脚还是灵便的吧?”
“你没听见他抱怨风湿病吗?那不是人衰老以后最常见的病痛吗?”
“我最最亲爱的孩子,”她母亲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你一定是时时刻刻都在为 我的 衰老而心惊胆战啦;我居然已经活到了四十岁的高龄,在你看来一定觉得是个奇迹了吧。”
“妈妈,你这么说我可是不公道。我当然知道布兰登上校还没老到会让他的朋友们担心将要失去他的程度。按照自然的规律他也许还能活上二十年呢。不过三十五岁可是跟婚配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也许,”埃莉诺道,“三十五和十七岁的最好不要谈婚论嫁。可要是碰上一位二十七岁尚且单身的女人,我并不觉得三十五岁的布兰登上校如果想娶她的话会有什么障碍。”
“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玛丽安沉吟了一会儿才说道,“是再也没有希望能感受到或者激起别人的爱意了,如果她家境不好,或是财产太少,出于嫁人为妻以后可以生计无虞、终身有靠的考虑,那倒是不妨屈就这么个保姆的职位。他要是想娶这么一个女人的话,确实没什么不合适的。这是桩双方两便的协议,大家都会感到满意。但在我看来这却根本就不是什么男婚女嫁,不过这倒也无关紧要。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桩商业交易,双方都希望对方吃亏,自己赚到便宜。”
“我知道,”埃莉诺回答道,“你是不可能相信一个二十七岁的女人还有可能对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产生任何接近于爱情的情感,使他成为自己的如意郎君的。不过只是因为昨天他偶然抱怨了一句一边的肩膀略微有点风湿疼的感觉(昨天是个非常寒冷的阴雨天),你就判决把他和他妻子永远都关进病房里,这我可是必须要反对的。”
“可他还说起了法兰绒的背心,”玛丽安道,“我感觉法兰绒背心总是和疼痛、痉挛、风湿以及各种侵袭年老病弱者的病痛分不开的。”
“他如果只是发了场高烧的话,你就不会这么瞧不起他了。说实话,玛丽安,你是不是觉得人发起烧来两颊通红、眼睛眍
 、脉搏加速也挺有趣的?”
、脉搏加速也挺有趣的?”
说完这话以后,埃莉诺没过多久也就离开了这个房间。“妈妈,”玛丽安在她走了以后说道,“说起生病来我倒是真有些担心,这个不能瞒你。我恐怕爱德华·费拉尔斯肯定是病了。咱们搬到这儿已经快半个月了,而他却还没有来。除非真是偶染微恙,否则是绝不会迁延这么久的。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事能把他硬留在诺兰庄园呢?”
“你真的认为他这么快就会追过来?”达什伍德太太道,“ 我 可不这么想。正相反,要是在这上头我有什么担心的话,倒是我想起当初我邀请他来巴顿做客的时候,他表现得有些犹犹豫豫、没精打采。埃莉诺已经开始盼着他来了吗?”
“我从没跟她提过这事儿,不过她肯定是盼着他来的呀。”
“我倒是觉得是你弄错了,因为昨天我跟她提起那间空余的卧室还需要添一个新炉架的时候,她说没必要这么着急,那个房间一时半会儿也不大会有人来住的。”
“这可太奇怪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过他们两个对待彼此的态度也真是莫名其妙!他们上次分手的时候是多么冷淡,多么平静啊!待在一起的那最后一个夜晚,他们说的话是多么没精打采!爱德华在道别的时候,对待埃莉诺和我没有任何差别:都像是一位满怀关切的兄长的良好祝愿一样。最后一天的那个早上,我有两次故意留他们单独在一起,可每一次他都莫名其妙地跟着我走出了房间。而埃莉诺在离开诺兰和爱德华的时候,哭得还没我厉害。就是现在,她也还是一如既往地克己自制。你见她什么时候灰心丧气、伤心难过过?你见她什么时候躲着不想见人,或者在人前显得不耐烦、不高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