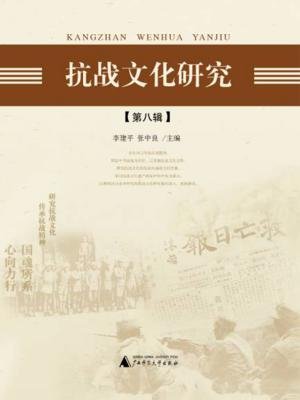从广义文化角度解读朱德的抗战思想
王盛泽
[摘要] 从广义文化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朱德的抗战思想进行一种新的审视和解读,它决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和全民性;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战,探索符合实际的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中国正义战争的必胜性。
[关键词] 朱德;抗战思想;广义文化
一、从文化的发展阶段看,战争是两种文明的剧烈冲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它决定了中国抗战只能是持久战、总体战
对于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辞海》的定义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陈华文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的生存和持续的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
 可以说文化是一切社会发展的集成,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发展所继承和保存下来的状态。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受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人类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当时的发展阶段,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朱德的抗战思想就是对于这种阶段的深刻把握。他通过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等进行分析,明确了抗战期间中国文化发展处于哪个阶段,提出了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正确认识。从总体上说,与日本比起来,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军事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朱德从中国和日本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状况对比入手,分析出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批驳了“抗战必败”的论调和“唯武器论”者的错误认识,指出:日本资源缺乏,人口又少,所以并不是那么可怕。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抗日游击战争是“时代的产物”,但抗战将是持久的、艰苦的。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可以在持久战中,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实现强弱的转换,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可以说文化是一切社会发展的集成,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发展所继承和保存下来的状态。文化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时受不同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制约。人类的活动只能局限在当时的发展阶段,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朱德的抗战思想就是对于这种阶段的深刻把握。他通过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等进行分析,明确了抗战期间中国文化发展处于哪个阶段,提出了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正确认识。从总体上说,与日本比起来,中国还是一个弱国,军事技术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朱德从中国和日本两国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状况对比入手,分析出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批驳了“抗战必败”的论调和“唯武器论”者的错误认识,指出:日本资源缺乏,人口又少,所以并不是那么可怕。抗战是中国唯一的出路,抗日游击战争是“时代的产物”,但抗战将是持久的、艰苦的。只要我们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因为中国可以在持久战中,以空间换时间,从而实现强弱的转换,最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朱德是著名的军事家,非常善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指导和总结战争的历史经验,他坚持认为抗战的主体力量是人民群众,这一点必须毫不动摇,同时强调进行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必要条件。他指出:“我们用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因素,乃是政治上的理直气壮和人力方面的无穷源泉”,“所以动员民众,武装民众,给民众以充分的救国抗日的自由,这是胜利的最必要的条件”。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弱国要战胜日本这样的强敌入侵,就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进行人民战争,中国的抗战不仅要靠几百万的军队,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成千上万的民众。没有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抗战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正因如此,他强烈主张在中国要开展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要加紧武装民众,实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同时对那些害怕民众起来、总是想方设法压制民众,企图单一依靠军队实行片面抗战的错误做法提出尖锐批评。指出动员民众参战,实行全民抗战,只会提高国民政府的威信,增强抗日的伟大力量,使持久抗战具有更加强大而坚实的基础。“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朱德的抗战思想最鲜明的体现就是他的抗日游击战争思想,在战术上表现为抗日的大众战和民兵战,“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战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朱德虽然认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因素”,但“人的问题是决定战争最后胜败问题”。这里所指的并非作为个体的某个人,而是指社会的人,是社会人的总体的集合。当时我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4,等于日本人口的7倍以上,“这是我们制胜的最重要的条件”。“持久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去团结这庞大无比的人力,并很好地运用它。”因为抗战是一个持久战、总体战,“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
朱德提出:游击战争“要能完全适当地运用和发挥上述五个要素,但因为游击队在某些要素上特别薄弱,如武器方面的低劣不精、经济方面的极端困难,所以更要善于发挥五个要素的特质,从而有针对性地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适当地运用它们,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因此,朱德将抗日游击战争划分为政治战争、经济战争、人员战争、武器战争、交通战争来进行论述,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概而言之,就是要运用总体战的思路来进行这场战争,才能赢得胜利。为此他主张要形成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军三者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主力必须与地方军、民兵相结合,才能使自己更强大”,而“广泛的群众性的武装组织——民兵,是坚持敌后抗战中配合与补充正规军,保卫与巩固根据地的重要基础,是支持敌后长期浩大战争的最雄厚的后备军”。从地域文化出发,朱德对以华北为中心的抗战进行了论述,给予充分重视。他指出华北从来是中外民族斗争的主要战场,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民族风格,即“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具有很深的民族意识。“这种具有很深民族意识的广大人民,便是坚持华北抗战、进行广大游击战争的无限源泉。”作为八路军总司令和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书记,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及主力,转战山西并指挥华北抗战,与山西人民一起度过了充满硝烟的峥嵘岁月。他在一封电报中提议:山西的发展前途,应以山西人民、地形、交通诸具体情形及华北大势来做一总的估计,“应有决心争取晋东南两大山脉,将巩固游击区,使入晋敌军陷入我群众重围中”。
从总体战出发,朱德倡导军垦屯田政策,坚持自己动手,动员、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经济困难。自力更生,发动军民生产运动,各地方政府设法帮助人民,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军民相互帮助,努力增加生产,以求达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目的。他还具体指导了南泥湾的开垦工作;帮助陕甘宁边区解决资金和技术困难,发展边区经济。同时提倡节约,节省开支。朱德提出:抗日游击队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同时要节省,过艰苦的生活。这种刻苦生活的模范作用,“往往成为决定抗日游击队前途的主要因素之一”。
抗战期间解放区战场的经验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在八年抗战中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中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鼎力支持和协助,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鼎力支持和协助。这种战争不仅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更是军队与民众万众一心实行的总体战。
二、从文化的发展特性看,它宽广的包容性和不绝的继承性、创新性,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探索符合实际战略战术的极端重要性
文化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特征,但这种阶级性又不是绝对的,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阶级性是可以让位于民族性的,如在外敌入侵时,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其阶级性和民族性也有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宽广的包容性就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就决定了中国抗战一定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实现团结抗战。因为在日本的侵略下,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只有抗日救国,才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
朱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维护者,不仅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极为赞成,而且身体力行。在卢沟桥事变前,1936年9月18日,在一次党的会议的讨论中他提出:统一战线和各个工作部门都有密切关系,要把一切视线都引到这方面来,要首先说服我们的干部和战士重视统一战线。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群众的政治中心”,在爱国家、爱民族的大义下,把各党、各派、各阶级、各宗教的同胞团结和组织起来,为祖国的存亡而战。他认为,在日本加紧侵略,亡国危险即将降临在每个中国人头上的时候,必须牢记“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不管过去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都应该抛开,唯有摈弃前嫌,放下私人恩怨,团结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才是出路。他提出要真正做到“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枪炮出枪炮,真正团结得像同胞兄弟一样。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要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他强调应“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
朱德以民族大义为重,模范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团结国民党友军共同抗日。朱德曾任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利用这一身份,对阎锡山和其他高级将领做统战工作,常到晋绥军和川军部队中做政治、军事报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朱德还以实际行动,协助友军抗战。在忻口会战期间,在卫立煌所部面临危险的紧急关头,他电令八路军部队从侧翼切断日军的交通线,对日军造成极大威胁。此举令卫立煌深为折服,此后卫立煌不仅与八路军协同作战,而且多次支持枪支弹药,形成国共军队合作抗日的良好局面。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在1938年5月曾指出:在世界大潮流中,民族冲突大于阶级冲突,中心工作还是统一战线,要用一切方法巩固统一战线。因此朱德也对国民党顽固势力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了坚决还击,用斗争方式教育并促使他们重新回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同时提出希望美、英、苏等盟国能加强对华援助。他努力与国际友人沟通,做好争取工作,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
文化还具有累积性和继承性特征,一种是对本民族文化的累积继承,一种是对外来文化的累积和继承,最终通过连续的文化累积和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学习实现文化的创新。朱德既重视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又特别重视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如在战略战术方面,他要求战争指导者一定要从战争的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找出隐藏在战争背后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正确的战争指导。抗战期间,朱德根据总体上是持久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结合抗日战场的具体情况,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比如坚持战略上的防御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坚持战略的持久战、消耗战与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歼灭战,坚持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的统一,根据需要灵活使用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等作战形式等。在从土地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后,从内战转到民族战争。面对日本军队,他不墨守成规,善于随机应变,求得主动,一再强调要“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朱德特别注重抗日游击战在抗战中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也注意到历史的继承性和与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性,“现代的抗日游击战争,其反抗性和一些战法的原则(如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之类),是与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大致相类”。但又大不相同,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应从现代的游击战争中,甚至从普法战争、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中,从中国十年来的国内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吸收各国的军事理论与经验”,“在新的条件下加以研究,使之完全适合于全国一致抗日的新条件”。总之就是要做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因为“战争诸要素不断发生变化,作战方式也随之不断变化”。当然游击战只是起配合作用的,正规军也可以开展这种游击战。无数游击队的不断活动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所有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起行动起来,最终就能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这种游击战还是要向运动战发展。“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朱德特别强调要使每一个战士能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技术,“务使物有所用,人与技术密切结合”。把旺盛的土气同技术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提高军队士气,提高作战能力与信心。
三、从文化的发展趋向看,先进文化必将战胜落后文化,中国抗战将激发起全民斗志,决定中国必定取得最后的伟大胜利
文化具有时代性特征,这使不同的文化具有可比性,使文化有先进与后进之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先进的文化必将战胜落后的文化。文化的时代性也决定了它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可以发生转化的。虽然有时物质文化暂时落后,但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如精神或制度文化层面来弥补,从而使它具有更大的先进性。从文化的发展趋向看,中国抗战代表着先进文化一方,这主要体现在下述方面:一是中国抗战是正义性的事业。朱德认为,中国虽然是弱国,但所进行的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政治上是理直气壮的,得道多助;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野蛮的、非正义的战争,失道寡助。所以中国抗战得到全国人民的全力拥护和支持,得到海外炎黄子孙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世界上坚持正义国家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二是抗日战争除了军事上的对抗外,更表现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坚定地维护了全民族利益,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虽然日本在军事力量上远较中国强大,但政治上却处于劣势。三是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力量得以不断壮大,对抗战起到政治领导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文化认同,可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相同的思维模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和语言与风俗习惯,可以形成巨大的认同抗异力量。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抵抗外敌的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特别是在外族入侵,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凝聚力也表现得更为强大。朱德非常重视挖掘和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抗战的重大作用。他极为重视战争的政治因素,认为一切战争都具备政治因素,没有政治因素的战争是没有的。应当认识政治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治华的阴谋,要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归纳出政治战争就是要达到“巩固自己、团结群众、瓦解敌军”三个目标。只有完全站在保卫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以求得抗日民族自卫战争最后胜利,才能团结成为坚强的队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是千千万万最勇敢、最坚决、充满民族意识和朝气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起来搏斗。任凭敌人怎样凶狠,也丝毫不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的精神,真是动天地而泣鬼神。”
朱德提出要培养和弘扬抗日英雄主义,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抱着牺牲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到底的民族英雄”。他认为,八路军、新四军中艰苦卓绝、奋不顾身的英雄主义气概,是一种新英雄主义,与旧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不能混同,革命斗争需要有革命的英雄主义,需要有许许多多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赤胆忠心,自始至终为革命服务,为革命效死的革命英雄,这种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值得充分肯定和弘扬,甚至要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使得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中涌现出更多的英雄和模范。
针对日本极为重视政治战、宣传战、文化战的做法,朱德提出要针锋相对地开展政治战争,进行全面的反制。如日本极力宣传“日本人口过剩”的侵略理论;提出“共存共荣”、“东亚和平”,收买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实施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等等。所以我们也要十分重视政治战,“必须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政治战争的胜利尽管不容易马上见效,不像军事胜利那么直白,但“其实际意义却等于缴了敌人许多枪炮,甚至还不止此”。进而他把抗日游击战争中政治战争这一要素提升到最主要的地位,要求全体队员不懈怠地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他主张“不仅要依靠政治的进步,而且要依靠军事的进步”。因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一方面军事的进步,需要政治的进步作为保障,另一方面一定要加强政治的进步,来保证战略战术的提高。他还十分强调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紧密结合,反对片面强调突出政治,将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脱离,甚至相对立的错误思想。朱德还非常善于用中华传统文化来宣传鼓动民众的抗日情绪。如在提到要团结抗战时提出要实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在练兵方面“练兵必先练心”的古话;在带兵问题上他提出干部要以身作则,引用古人“能身先士卒与士卒共甘苦者为名将”来说明。
朱德还特别对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及其作用进行了总结,认为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军,而且敌人在宣传中重视利用艺术,特别注意借用中国形式。朱德认为宣传工作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同时要利用艺术的民族形式和民间形式,即实现大众化和通俗化,接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良的东西而加以发扬,这样我们的宣传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才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取得的成绩将更大。朱德提出要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和文明是与黑暗和落后相对立的,马列主义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论,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掌握了它可以使一切科学得到新的发展。要取得抗战胜利,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这体现出朱德跟上时代,保持先进性的思想。
对于革命军人,要求其“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因而能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同时加强从实际出发的军事教育。朱德总结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能够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的经验,认为就是因为下定了决心,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生存,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到底;同时坚持了进步。带头倡导和坚决执行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坚持团结全国各个界别、阶层和各支军队,彻底实行“三三制”政权,增强代表性,制定并实行兼顾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使一切属于抗日人民范畴都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等的充分自由,都享有人权、政权、财权、地权等保障。特别是根据民众的要求,实行精兵简政,这样得到各阶层人士的同情与支持,赢得民心。在党的领导下,贯彻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方针,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建立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达成了各阶级和各阶层的大团结,这就是中国能够坚持全民抗战并取得巨大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全民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广义文化角度审视朱德的抗战思想,更加说明朱德抗战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基础上进行总结创新,从而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补充和发展,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探索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朱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为中国抗战胜利和军事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
(本文中的朱德言论引自《朱德选集》《朱德年谱》《朱德军事文献》等,不做一一详注)
作者简介:
王盛泽,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