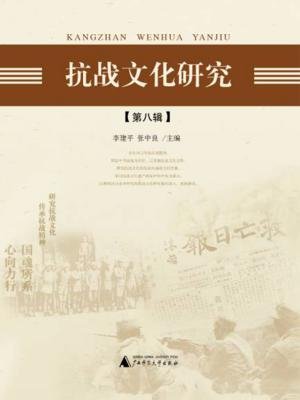延安文艺中的农民形象
吴继金
[摘要] 农民在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中是没有地位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成功地塑造了农民的形象。早期延安文艺对农民的刻画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和欧化现象,但在延安文艺整风后,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前提下,延安文艺不仅以农民作为文艺接受对象,而且根据地农民成为了文艺作品的主人翁,成为歌颂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 延安文艺;农民形象;接受对象;文艺政策
谁是文艺作品的主人翁,这是由文艺的阶级性和社会的文艺政策决定的。过去时代文艺作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作品中才真正出现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文艺不仅强调文艺接受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且翻身作主人的农民成了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人,成为歌颂的对象。
一、农民成为延安文艺作品中的主角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自己少年时的读书经历,说自己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国旧小说。“这些旧小说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农民,自古至今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却很少被文人认真注视和着意表现过;农民和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极少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和描写的主体。千百年来,一切旧的文艺舞台上,上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不是不准登台,就是被百般丑化。农民即使在文艺作品中露过头面,也只不过是被当做生产粮食和抚养家畜的,甚至是能代替家畜的动物,再不然就是被当做抽象的自然人或被命运安排好了的,或者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好汉,或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运儿。
农民,自古至今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却很少被文人认真注视和着意表现过;农民和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极少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和描写的主体。千百年来,一切旧的文艺舞台上,上演的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不是不准登台,就是被百般丑化。农民即使在文艺作品中露过头面,也只不过是被当做生产粮食和抚养家畜的,甚至是能代替家畜的动物,再不然就是被当做抽象的自然人或被命运安排好了的,或者是“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好汉,或者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幸运儿。
直至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随着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一批高举文学为人生旗帜的现实主义作家,开始面对广大的农村,关心生活其中的农民的命运,再现农民的不幸,特别是通过揭示他们被戕害了的灵魂,以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在中国文学史上,传统农民形象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是从鲁迅开始的。著名文学史家王瑶曾指出:“中国文学史上真正把农民当做小说的主人公的,鲁迅是第一人。”
 钱谷融也认为:“农民问题是鲁迅先生注意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关注和最深的同情给予农民。”
钱谷融也认为:“农民问题是鲁迅先生注意的中心,他把最多的篇幅,最大的关注和最深的同情给予农民。”
 鲁迅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闰土、爱姑、七斤等不朽的文学典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代言人。到30年代,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家对那些觉醒着并为明天的幸福而斗争的农民,给予了充分的展现。
鲁迅所塑造的阿Q、祥林嫂、闰土、爱姑、七斤等不朽的文学典型,早已成为中国传统农民形象的代言人。到30年代,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左翼文艺家对那些觉醒着并为明天的幸福而斗争的农民,给予了充分的展现。
毛泽东生于农村,自幼与农民有较多接触,对贫苦农民怀有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深谙中国社会现实,一方面强调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领导革命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强调:“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
 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他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认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他指出:“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者和农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始终关注农民,投身革命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对传统文艺中只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这种颠倒历史的不公正现象极为不满,对旧戏曲中排斥劳动大众的生活和精神的做法更是感到不安和愤慨。他在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所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劳动者和农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始终关注农民,投身革命后,长期从事农民运动,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对传统文艺中只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这种颠倒历史的不公正现象极为不满,对旧戏曲中排斥劳动大众的生活和精神的做法更是感到不安和愤慨。他在1944年1月9日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所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面目。”
 “文以载道”,毛泽东把文艺当成思想启蒙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武器看待,要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必然要求文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体到延安文艺要以工农兵为主角,表现根据地农民的新形象。
“文以载道”,毛泽东把文艺当成思想启蒙与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武器看待,要用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必然要求文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具体到延安文艺要以工农兵为主角,表现根据地农民的新形象。
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曾说过:“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
 换句话说,一旦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自然就会在文艺中占据重要席位,成为文艺的主体。农民阶层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潜在社会能量最大的群体,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自然是革命文艺所不能忽视的。伴随着农民在政治上的崛起并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农民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日渐凸现。而抗日战争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势必会引起文艺的关注。因此,农民在抗战中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延安文艺中农民形象的主人翁地位。
换句话说,一旦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统治地位,自然就会在文艺中占据重要席位,成为文艺的主体。农民阶层作为中国社会人数最多、潜在社会能量最大的群体,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自然是革命文艺所不能忽视的。伴随着农民在政治上的崛起并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农民在文艺中的主体地位日渐凸现。而抗日战争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解放战争,势必会引起文艺的关注。因此,农民在抗战中主力军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延安文艺中农民形象的主人翁地位。
陕甘宁边区的农村、农民历来是延安文学的主要表现对象与创作题材,即使在被认为最脱离生活斗争实际的1941—1942年间的,除了表现抗战内容的创作之外,延安作家的题材选择也主要集中在对边区农村生活的描摹和刻画上,“边区农民以及根据地普通百姓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展露,构成了唯一可以与延安战争文学相抗衡的文学表现天地”
 。尤其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群众成了一切剧本的主人公”
。尤其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群众成了一切剧本的主人公”
 。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人民文艺丛书》,汇集了177篇作品,据周扬的统计:“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一百零一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十一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十六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七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十二篇。”
。反映解放区文艺创作成果的《人民文艺丛书》,汇集了177篇作品,据周扬的统计:“写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包括群众的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与人民军队(军队作风、军民关系等)的,一百零一篇。写农村土地斗争及其他各种反封建斗争(包括减租、复仇清算,土地改革,以及反封建迷信、文盲、不卫生、婚姻不自由等)的,四十一篇。写工业农业生产的,十六篇。写历史题材(主要是陕北土地革命时期故事)的,七篇。其他(如写干部作风等),十二篇。”
 周扬热情地赞颂孔厥小说在题材上的转向:由写知识分子(而且是偏于消极方面的)到写新的、进步的农民,认为这是作者创作道路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周扬热情地赞颂孔厥小说在题材上的转向:由写知识分子(而且是偏于消极方面的)到写新的、进步的农民,认为这是作者创作道路中的一个重要进展。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农民艺术形象,“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所有村干部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许多农民,……是以写农民(村干部当然在内并为其代表者)为主的”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塑造了许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农民艺术形象,“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所有村干部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许多农民,……是以写农民(村干部当然在内并为其代表者)为主的”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反映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憧憬和欢乐,主题写的都是农民。由此可见,在延安文艺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已被“工农兵”所取代,工农兵形象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根据地农民成了被歌颂的主角,完全颠覆了传统文艺中无视下层人民(即使有也只是“强盗乱民”之类),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偏见。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反映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憧憬和欢乐,主题写的都是农民。由此可见,在延安文艺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等已被“工农兵”所取代,工农兵形象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根据地农民成了被歌颂的主角,完全颠覆了传统文艺中无视下层人民(即使有也只是“强盗乱民”之类),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偏见。
二、农民成为延安文艺歌颂的对象
在中国文学史上,尽管鲁迅使农民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但他所塑造的农民形象具有一系列愚弱、麻木、奴性等性格特征。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生活,成了鲁迅致力揭示的“病态社会”,充满着阴郁、灰暗、悲剧的色调。周作人曾经说过:“鲁迅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出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痛苦与黑暗的人生观,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一片黑暗的悲观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启蒙”、“改造国民性”,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启蒙”、“改造国民性”,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指出:“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种“鲁迅式”改造国民性观念下的农民形象,显然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要求是不相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农村新气象是不适应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
 毛泽东在1939年11月7日给周扬的信中说:“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做是旧的,……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
毛泽东在1939年11月7日给周扬的信中说:“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做是旧的,……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
 农民既有落后的一面,也有革命性的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政治和文化因素而言,在全国不仅不落后,而且是先进的。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农民既有落后的一面,也有革命性的一面。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政治和文化因素而言,在全国不仅不落后,而且是先进的。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一篇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大批政治和文化精英因为战争而意外地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城市的依托,流向他们本来不大可能选择的像延安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这样原来在文化上极端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因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大量涌来,延安逐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全国”的“心脏”了。
大批政治和文化精英因为战争而意外地失去了原有的中心城市的依托,流向他们本来不大可能选择的像延安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这样原来在文化上极端贫穷落后的陕甘宁边区因为政治文化精英的大量涌来,延安逐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全国”的“心脏”了。
在这样一个作为新中国雏形的模范抗日根据地里,农民翻身得了解放,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改变,而且在政治地位和精神面貌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民形象在文艺作品中仍然是愚弱、麻木、奴性的话,就难以说明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了,也难以证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了。周扬说,在解放区这个环境之下,人的变化是迅速的。“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天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
 既然作为农民典型形象的阿Q已经觉醒,启蒙文学在解放区自然成为多余。既然阿Q已经成为时代的英雄,在文学中加以丑化就不合时宜了,歌颂自然也就顺理成章。1947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县给中国平剧院(即京剧院)做了一次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并特别提到:旧的艺术这个东西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来源,我叫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和农民创造的。比如孔明一出来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大众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工农大众,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却在艺术上被形容成小丑。在毛泽东看来,劳动大众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在文化活动中理应占据突出的位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颠倒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不能享有文化,不能在艺术舞台上获得歌颂和肯定;相反,劳动大众接受的文化艺术,却是让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打旗跑龙套的喽啰,随人驱使。翻身做主人的农民不仅要成为延安文艺作品中的主人翁,从配角变为主角,而且还要成为歌颂的对象,表现的正面形象。
既然作为农民典型形象的阿Q已经觉醒,启蒙文学在解放区自然成为多余。既然阿Q已经成为时代的英雄,在文学中加以丑化就不合时宜了,歌颂自然也就顺理成章。1947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西米脂县给中国平剧院(即京剧院)做了一次题为《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报告,并特别提到:旧的艺术这个东西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来源,我叫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并不是那些英雄宰相创造的,而是那些劳动者和农民创造的。比如孔明一出来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人民大众不过是跑龙套。然而,世界上百分之九十是工农大众,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的手盖的,却在艺术上被形容成小丑。在毛泽东看来,劳动大众是整个历史的创造者,在文化活动中理应占据突出的位置。封建社会意识形态颠倒历史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化的创造者不能享有文化,不能在艺术舞台上获得歌颂和肯定;相反,劳动大众接受的文化艺术,却是让他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打旗跑龙套的喽啰,随人驱使。翻身做主人的农民不仅要成为延安文艺作品中的主人翁,从配角变为主角,而且还要成为歌颂的对象,表现的正面形象。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的延安文艺作品中,对根据地农民的刻画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具体语言的运用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丑化现象,但在文艺整风运动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如果说,在这以前,农民劳动者,时常以丑角姿态,扮演在戏剧中,作品中,文艺家们还时常从他们的‘愚笨’与‘粗野’上来描写,而引起一些观众发笑的话。那正说明这些人在那个社会里面的地位,是委屈的,是渺小的。今天,他们踏着轻盈的舞蹈走到广场上来,他们是那样光辉,……走进文艺领域中间来了。”
 当时延安影响很大的秧歌《兄妹开荒》,在之前的演出中还都有丑角出场。主要演员李波后来回忆道:“在我们的节目中,虽然内容都是宣扬党的政策和宣扬抗日的,但无论在秧歌队或小节目中都有一些丑角,……大化和我演《拥军花鼓》时,我倒是村姑打扮,而大化却扮成了小丑。”
当时延安影响很大的秧歌《兄妹开荒》,在之前的演出中还都有丑角出场。主要演员李波后来回忆道:“在我们的节目中,虽然内容都是宣扬党的政策和宣扬抗日的,但无论在秧歌队或小节目中都有一些丑角,……大化和我演《拥军花鼓》时,我倒是村姑打扮,而大化却扮成了小丑。”
 这种情况被周恩来、彭真以及周扬批评为“把劳动人民丑化了”。待到王大化在《兄妹开荒》中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对劳动生产充满热情、明朗与快活的边区青年形象了。赵树理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周扬认为赵树理是歌颂派的典型。比如,周扬赞扬小二黑的胜利时写道:“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至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这种情况被周恩来、彭真以及周扬批评为“把劳动人民丑化了”。待到王大化在《兄妹开荒》中出现时,已经是一个对劳动生产充满热情、明朗与快活的边区青年形象了。赵树理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周扬认为赵树理是歌颂派的典型。比如,周扬赞扬小二黑的胜利时写道:“作者是在这里讴歌自由恋爱的胜利吗?不是的!他是在讴歌新社会的胜利(只有在这种社会里,农民才能享受自由恋爱的正当权利),讴歌农民的胜利(他们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懂得为更好的命运斗争),讴歌农民中开明、进步的因素对愚昧、落后、迷信等等因素的胜利,最后也至关重要,讴歌农民对封建恶霸势力的胜利。”
 沈文慧指出:“延安文学竭力讴歌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进程中农民身上所焕发出的崭新精神风貌,农民的革命精神、翻身解放、觉醒成长成为文学的主旋律。”
沈文慧指出:“延安文学竭力讴歌在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进程中农民身上所焕发出的崭新精神风貌,农民的革命精神、翻身解放、觉醒成长成为文学的主旋律。”

延安的木刻版画作品,出现最多,也最为重要的一类题材,是直接描绘和反映在解放区这片明朗的天空下出现的“新的时代”、“新的世界”、“新的中国”的生活与工作的题材,大量歌颂了翻身作主人的农民形象。“必须从劳动与土地结合过程中去寻找构图,在民主的阳光下去发现色彩,生产动员,开荒,春耕,移民,生产竞赛,公粮会议,运盐,合作社的发展,都必须成为画家们新的表现题材。”
 范迪安在谈到延安时期的“革命美术”时说:“革命美术大量表现了乡村农民新的生活现实。作为后来新中国的雏形,延安正在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受民主权利的新的理想。这样一种新的现实,在画家们的笔下有了极为充分的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农民作为社会主人新的精神面貌,也使得在中国绘画历史上,艺术第一次接近了民主。”
范迪安在谈到延安时期的“革命美术”时说:“革命美术大量表现了乡村农民新的生活现实。作为后来新中国的雏形,延安正在由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受民主权利的新的理想。这样一种新的现实,在画家们的笔下有了极为充分的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农民作为社会主人新的精神面貌,也使得在中国绘画历史上,艺术第一次接近了民主。”

延安文艺家将表现农村生活和塑造新型农民形象,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作为他们创作的首要任务。然而,作为歌颂对象的农民身上也有弱点,新农村中也还存在着阴暗面。在文艺创作中如何对待消极的东西,如何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是塑造新型农民形象的艺术创作绕不过的问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
 毛泽东要求“以写光明为主”,“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毛泽东要求“以写光明为主”,“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
 。周扬坚决反对王实味的做法,大声宣告“写光明比写黑暗重要,一般地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如此,特殊地就先进阵营内来说,尤其如此”。写光明,“就是主张写现实的积极的方面,成长的方面有将来的方面……不错,我们也是主张歌功颂德的,但这是歌群众之功,颂群众之德,而这种歌颂,是完全正当的,必须的”
。周扬坚决反对王实味的做法,大声宣告“写光明比写黑暗重要,一般地就全国范围来说,是如此,特殊地就先进阵营内来说,尤其如此”。写光明,“就是主张写现实的积极的方面,成长的方面有将来的方面……不错,我们也是主张歌功颂德的,但这是歌群众之功,颂群众之德,而这种歌颂,是完全正当的,必须的”
 。延安文艺将农民作为表现、歌颂、赞美的对象,正是在与主题倾向、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协同合作中,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这些文艺作品告诉人民:解放区的劳动人民,已彻底摆脱了旧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镣铐,以社会主人公的崭新姿态在生活中出现。
。延安文艺将农民作为表现、歌颂、赞美的对象,正是在与主题倾向、人物塑造、语言风格等协同合作中,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这些文艺作品告诉人民:解放区的劳动人民,已彻底摆脱了旧社会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镣铐,以社会主人公的崭新姿态在生活中出现。
三、以农民作为文艺接受对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由于延安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毛泽东眼中,作为战争主力军的穿军装的农民——抗日的军队,和广大不穿军装的农民——支持战争的最基本的群众力量,都是革命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延安文艺的生存空间在农村,主要接受群体是农民,欣赏主体也是农民,因此,延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广大农民服务。“如果说五四作家对农民是俯视的,那么延安时期无疑是仰视的。与五四文学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不同,延安文学是‘写农民’也是‘为农民而写’的文学,就世界文学而言,如此大规模地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学运动也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延安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基本上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毛泽东眼中,作为战争主力军的穿军装的农民——抗日的军队,和广大不穿军装的农民——支持战争的最基本的群众力量,都是革命文艺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民族利益的代表。延安文艺的生存空间在农村,主要接受群体是农民,欣赏主体也是农民,因此,延安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广大农民服务。“如果说五四作家对农民是俯视的,那么延安时期无疑是仰视的。与五四文学主要表达知识分子的个人体验不同,延安文学是‘写农民’也是‘为农民而写’的文学,就世界文学而言,如此大规模地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学运动也是史无前例的。”
 “为农民而写”,“为农民而唱”,“为农民而画”,文艺家们就是要自觉以广大农民为艺术接受对象,使文艺能够转换成一种老百姓能接受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从而被农民所理解、所喜欢。周扬赞扬赵树理写的人物不存在“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现象,在作叙述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语言,其根本原因在于赵树理情感立场上与农民的统一:“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
“为农民而写”,“为农民而唱”,“为农民而画”,文艺家们就是要自觉以广大农民为艺术接受对象,使文艺能够转换成一种老百姓能接受的艺术语言和艺术形象,从而被农民所理解、所喜欢。周扬赞扬赵树理写的人物不存在“衣服是工农兵,面貌却是小资产阶级”现象,在作叙述时也同样是用的群众语言,其根本原因在于赵树理情感立场上与农民的统一:“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
 周扬不满意于孔厥小说中“一长串的,雄辩而又有条理的叙述”,认为这“既不适合农民的身份,又容易混入知识分子的口吻和语气”。
周扬不满意于孔厥小说中“一长串的,雄辩而又有条理的叙述”,认为这“既不适合农民的身份,又容易混入知识分子的口吻和语气”。
 范迪安在谈到延安版画时指出:“原先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艺术目的现在成为以艺术的接受对象为中心的艺术使命,原先作为民众‘导师’的艺术家个体现在溶入了民众的集体之中,甚至以为民众‘服务’为自己从事艺术的价值。”
范迪安在谈到延安版画时指出:“原先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艺术目的现在成为以艺术的接受对象为中心的艺术使命,原先作为民众‘导师’的艺术家个体现在溶入了民众的集体之中,甚至以为民众‘服务’为自己从事艺术的价值。”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导下,文艺家们“检讨了自己过去思想中和作品中存在的某些偏向,……进一步与工农兵结合,……而且和过去的‘作客’完全不同,从思想情感上和群众打成一片,成为工农兵行列中的一员。”
 为了更好地使文艺为农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原来作为农民“导师”的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不仅要成为工农兵行列中的一员,而且还要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拜农民为师,学习和借鉴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这其实就是农民形式,是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为农民所易于接受、所喜闻乐见而被知识分子忽视的形式。版画是战争年代迅速有效宣传革命的画种,延安艺术家学习和吸收农村传统的民间艺术,如剪纸、年画等,创造性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为了使艺术的接受者——士兵和农民——能够理解艺术,版画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绘画传统的另一巨大的资源体系——民间艺术,版画开始有了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的特点,平面化的结构和明亮的色彩以及清晰的形象使它们成为士兵和农民‘读’得懂也喜欢的艺术。”
为了更好地使文艺为农民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自觉改造世界观,原来作为农民“导师”的高高在上的艺术家,不仅要成为工农兵行列中的一员,而且还要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拜农民为师,学习和借鉴文艺的民族形式和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这其实就是农民形式,是长期存在于民间的、为农民所易于接受、所喜闻乐见而被知识分子忽视的形式。版画是战争年代迅速有效宣传革命的画种,延安艺术家学习和吸收农村传统的民间艺术,如剪纸、年画等,创造性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的木刻艺术。“为了使艺术的接受者——士兵和农民——能够理解艺术,版画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绘画传统的另一巨大的资源体系——民间艺术,版画开始有了剪纸、年画等民间艺术的特点,平面化的结构和明亮的色彩以及清晰的形象使它们成为士兵和农民‘读’得懂也喜欢的艺术。”

以农民作为文艺接受对象,来自农民创作的文艺作品与群众的生活更加贴近,语言更加通俗易懂,农民感到更亲切,更容易接受。1942年10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康生的《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一封信,提出“应积极组织工农份子写文章”,以此“提高工农干部写文章的热情和信心,打破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写文章的错误心理”。
 艾青“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诗,更提倡老百姓自己的诗,提倡不离生产的工农兵大众写的诗”,并坚信“新的诗人将从大众中产生,而我们至多是一个助产妇”
艾青“提倡写给老百姓看的诗,更提倡老百姓自己的诗,提倡不离生产的工农兵大众写的诗”,并坚信“新的诗人将从大众中产生,而我们至多是一个助产妇”
 。为了帮助农民文艺作者的成长,《解放日报》于1942年10月5日起在第4版陆续组织刊发了一些出自工农兵作者之手的文章,后来还开辟了一个名为“大众习作”的栏目,大多以原作和经修改后的改作相对照的形式刊发工农群众的作品。1943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登载“本版征稿启事”,正式征集“工农士兵的写作及一切通俗启蒙性质的著述”。1943年3月19日《解放日报》开始增设“大众习作”专栏,发表工农士兵自己写作的作品,开展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延安文艺作品中许多是农民创作的作品,特别是涌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农民诗人,如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韩起祥创作的《刘巧团圆》等。周扬称颂不识字的农民诗人孙万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好欢喜和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
。为了帮助农民文艺作者的成长,《解放日报》于1942年10月5日起在第4版陆续组织刊发了一些出自工农兵作者之手的文章,后来还开辟了一个名为“大众习作”的栏目,大多以原作和经修改后的改作相对照的形式刊发工农群众的作品。1943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登载“本版征稿启事”,正式征集“工农士兵的写作及一切通俗启蒙性质的著述”。1943年3月19日《解放日报》开始增设“大众习作”专栏,发表工农士兵自己写作的作品,开展文学艺术的普及工作。延安文艺作品中许多是农民创作的作品,特别是涌现了一批影响较大的农民诗人,如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韩起祥创作的《刘巧团圆》等。周扬称颂不识字的农民诗人孙万福是“一个优秀的诗人”,“好欢喜和兴奋”的神情溢于言表。
 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许多作者就是农民。“这些秧歌并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一种完全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不仅有诗人、作家、戏剧音乐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识分子、学生,这一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店员也参加了。”
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许多作者就是农民。“这些秧歌并不是哪一个人创造的,而是一种完全的集体创作。参加创作的不仅有诗人、作家、戏剧音乐工作者、行政工作者、知识分子、学生,这一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农民、士兵、店员也参加了。”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中国共产党不仅帮助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而且在文艺上以农民为主体,从而赢得了农民的支持。以农民为接受对象、为文艺作品的主人翁和歌颂主题的延安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鼓舞人民斗志、打击敌人的艺术武器的作用。
作者简介:
吴继金,湖北美术学院公共课部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理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