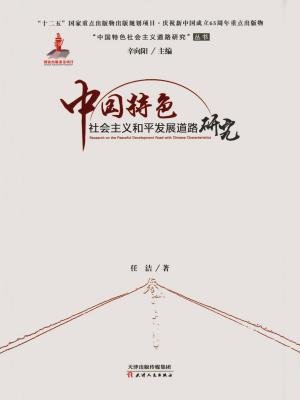第一节 悠久深厚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深深扎根于中国悠久深厚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之中,是对中国和平主义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概括起来,中国和平主义文化传统蕴含在“尚德”“贵和”“天下”的文化理念之中,并外化为朝贡、和亲等制度建构,通过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具体行为得以践行。
一、文化的解释力:考量中国和平发展不可或缺的变量
任何一种文明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多年,“尚德不尚武”“以和为贵”,追求实现“天下大同”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之一。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我们很容易挖掘出中国“尚德不尚武”“以和为贵”“天下大同”的文化资源。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侧重于宣扬自然而然、不尚武力的思想。老子说:“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兵家传统中也有尚德不尚武的思想。《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兵家传统中也有尚德不尚武的思想。《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可见,军事和武力手段并不是实现国家目的的上策,如果能通过政治或外交手段实现国家目的,就不应该进行战争,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可见,军事和武力手段并不是实现国家目的的上策,如果能通过政治或外交手段实现国家目的,就不应该进行战争,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图1-1 《孙子兵法·谋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非常崇尚“德行”,注重人的内心对世界、人生正义、善良美好事物的认同和追求,强调“以德服人”。在儒家文化中,“德”的思想通过“仁”和“礼”加以体现。《礼记·曲礼上第一》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故“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论语·学而》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指出:“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
这种“尚德不尚武”“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最终体现为追求实现天下大同、天下太平的社会理想。最早阐述“天下大同”的文化典籍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为大同”。老子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图景。《礼记》和老子的大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起义口号;南宋康与之提出的“计口授田”、人人耕桑、自食其力、劳动成果平均分配的社会构想;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纲领;及至康有为《大同书》中力主实现“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既无专制之君主,亦无民选之总统”的“大同之世”;再到孙中山提出的中国五大种族扩充自由、平等、博爱于全人类,大同盛世则不难到来,都直接传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大同思想。
之所以追溯中国崇尚和平、不尚武力、追求实现“天下大同”的文化传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国家如何与外部世界交往相处,制定何种外交政策、外交目标,实施何种对外发展战略,深受本国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的文化铸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气质、认知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基本的心理定式,这些特质必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或支配领导者的决策过程,引导国民的价值取向,也会影响其处理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交往方式。”

但是也有学者主张不宜夸大中国的和平主义文化传统对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的影响,认为:“中国有自己悠久的和平主义人文传统可资借鉴,但中国已不是封建帝国,也不处在以前封闭的状态,不应再过多地从过去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寻找依据和话语来注释。当然,这并不是要抛弃本民族的光辉历史(其实,我们虽然能找出许多和平传统的例证,但外国人士更多关注的是非和平事例,因此说服力有限)。”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和平主义文化传统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选择中的作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当然不难找出中国发动战争的记录,国外学者确实从同样的历史典籍中得出了与我们不同的结论。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对以上思想家(指孔子、孟子、孙子)的著作和历史记录做更仔细的审视,就可以发现这些材料一般并不证明以上看法(指中国具有和平主义对外关系传统)是正确的……只要粗略审视中国的安全行为就会看到,中国的统治者常常采用暴力来达到他们的国家安全目的。事实上使用武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普遍现象。”

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武力和战争。漫长的中国历史出现战争是正常现象,但是应该有一个相对的视角,可以将同时期的中国战争数量与欧洲国家作比较,一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发生战争的次数已经是少之又少。再者,还可以深入研究中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和性质,这比单纯统计中国发动战争的数量更具说服力。有学者指出:“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基本上没有对外扩张的历史,即使有,这段历史的时段也不超过200年。这样算来,和平与扩张的时间比例为5000:200=25:1。而西方国家从古希腊以来就充斥着对外扩张的历史,古罗马帝国的征服就长达100多年,后来的‘十字军东征’长达200多年。从14世纪以来,西方对外扩张的历史更是没有中断过,达到600余年,这样一来,西方扩张的历史长达1000多年。其和平与扩张的时段比例为2500:1000=2.5:1。”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先生的评价可以用来回应这种观点,他说:“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他说:“欧洲国家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并不在于他们有如此多的战争,而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总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来抢夺他谋害他。这样,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保持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历史上极少出现以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土地、财富、人口为最高目的的征伐。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教授辜鸿铭先生的评价可以用来回应这种观点,他说:“的确,在中国是存在战争的,不过自从2500年以前孔子时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没有发生像今天在欧洲所看到的那种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一种意外事故(accident),可是在欧洲,战争则是一种必需(necessity)。我们中国人是会打仗的,但是我们并不指望生活在战争中。”他说:“欧洲国家最不能让人容忍的一件事,并不在于他们有如此多的战争,而在于他们每个人都总担心其邻居一旦强大到一定程度,就要来抢夺他谋害他。这样,压在欧洲人民身上的便不是如此多的战争,而是不断武装自己的需要,一种必须利用物质力量保持他们自己的绝对的需要。”
 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战争事例并不足以否定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不足以否定中国文化“和”的性质。
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战争事例并不足以否定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不足以否定中国文化“和”的性质。

图1-2 “十字军东征——蒙吉萨战役”油画
文化是考量国家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变量,这是一个既定的共识。文化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和国民性格。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文化传统作为流动着的活的文化,深深熔铸在国家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和国民性格之中。当我们用外部环境、国家利益等因素仍无法解释某种国家行为时,不妨将目光投向文化,或许文化传统的因素能帮助我们寻找到合适的解答。
例如日本和德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对世界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然而两国对战争罪行的认识却大不相同。日本不仅不深刻反思本国的军国主义罪行,反而一再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受害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而德国人对希特勒纳粹战争罪行却进行了真诚的反省和彻底的忏悔。1970年,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跪倒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前,表示自己要“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下跪”。1995年,德国时任总理科尔在以色列的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再次代表德国向受害者道歉。2004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在华沙向死难者纪念碑鞠躬时说:“在这片代表波兰骄傲和德国罪行的土地上,我们期待宽恕与和平,德国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2013年1月26日,在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前夕,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要一代一代保留下去。”还说:“面对历史,我们不会隐瞒和压制任何事,德国必须正视事实,确保未来能成为极佳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就如我们现今一样。”


图1-3 1970年,联邦德国时任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向遇害者纪念碑下跪
日本和德国对本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不同认识,折射出日本和德国不同的文化民族性。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菊与刀》一书就是揭示日本文化民族性的代表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面临对德日采取何种政策的问题。对于德国,美国比较了解,采取武装占领和直接管制的政策就行得通。但是对日本,美国不太了解,尤其对日本是否投降的问题无法确定,由此连带的疑问是:如果日本不投降,美国是否可以像对德国那样武装占领日本、对日本实行直接管制;如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且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专家、学者对日本进行研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就是受政府之托完成的研究报告。在《菊与刀》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的强制力来自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德日两国在对待同样的战争罪行时所采取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和行为。
二、朝贡制度的再现
中国悠久绵长的和平主义文化理念必然在制度上有所体现。古代中国,朝贡制度是确定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模式的核心制度。朝贡制度的确立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天下是统一的,华夏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其四周的各种文明或者是中国文明的变种,或者是不发达未开化、野蛮的少数民族。这些中国文明的变种,和有待文明开化的蛮夷或戎狄需要用纳贡、朝觐的方式向天子表示敬重之意,同时也意味着对华夏文明的臣服。朝贡制度成为彰显中华文明影响力、辐射力,达到“以夏变夷”目的的制度形式。
古代的中国之所以会自认为是“中央之国”“世界中心”,首先与其地理环境有关。中国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北及西伯利亚,西达帕米尔高原,西南迄喜马拉雅山脉,东和东南濒临大海。中国疆域所处的独特地理单元,成为中华民族的“隔绝机制”,天然的地理障壁确实使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面临困难。其次,从世界古代史的视角看,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各个文明中心都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当时是轴心时代,世界几大文明各自繁荣发展,相互之间无交流、无了解,各自都视自己为世界中心,中国自诩为世界中心也不足为怪。再次,中国文明虽然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发展,但却绵延不断,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而且经过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几次大的文明高峰阶段,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加强了中央之国的观念。西方学者曾经以比较的视野阐述中国古人创造的辉煌经济成就:“过去的2000年里,有180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都要超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除却生产总值的震撼力,中国古人为世界贡献的四大发明、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任何一项都彪炳史册。这些成就和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成为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学者认为:“朝贡制度的两个关键特征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在规模上压倒性的差距以及双方对中国优越性的认同和默许。”
除却生产总值的震撼力,中国古人为世界贡献的四大发明、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任何一项都彪炳史册。这些成就和贡献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的自豪感和优越感。这成为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有学者认为:“朝贡制度的两个关键特征是中国与邻国之间在规模上压倒性的差距以及双方对中国优越性的认同和默许。”


图1-4 明朝时期的朝贡外交
朝贡制度的和平性突出体现在它的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在如何进贡、进贡的次数、物品、数量等问题上,中国古代实行的是“五服”制。“五服”制这样规定:国都以外五百里叫甸服。离国都最近的一百里缴纳连秆的禾;二百里的缴纳禾穗;三百里的缴纳带稃皮的谷;四百里的缴纳粗米;五百里的缴纳精米。甸服以外五百里是侯服。离甸服最近的一百里替天子服差役;二百里的担任国家的差役;三百里的担任侦察工作。侯服以外五百里是绥服。三百里的考虑推行天子的政教;二百里的奋扬武威保卫天子。绥服以外五百里是要服。三百里的要和平相处;二百里的要遵守王法。要服以外五百里是荒服。三百里的维持隶属关系;二百里的进攻与否流动不定。
 虽然“五服”制明确规定了进贡的物品和数量,但是进贡的物品和数量更多地体现进贡者对天子的敬重和臣服,而不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上的剥削和压榨。对于要服和荒服地区进贡的次数和品种都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是否来进贡也要视情况而定,并不使用武力强迫其进贡。如果五服、荒服地区不来进贡,反而应该自我检讨,通过加强自己的文德修养,使远人臣服。
虽然“五服”制明确规定了进贡的物品和数量,但是进贡的物品和数量更多地体现进贡者对天子的敬重和臣服,而不是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经济上的剥削和压榨。对于要服和荒服地区进贡的次数和品种都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是否来进贡也要视情况而定,并不使用武力强迫其进贡。如果五服、荒服地区不来进贡,反而应该自我检讨,通过加强自己的文德修养,使远人臣服。
和亲制度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制度。和亲也称为“和戎”“和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处理不同政权之间的关系。虽然学界关于和亲制度的发端有争议,但是班固和司马光等史学家关于“和亲始于西汉”的论断对后世影响最大。自汉以后,和亲逐渐成为历代统治者采取的处理两个不同的民族政权或同一种族的两个不同政权之间关系的制度。根据历代史书所记载的和亲事例划分,大体有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割据政权之间的联姻,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南朝与北朝之间的联姻,百济与新罗、高句丽之间的联姻六种类型的和亲。按照和亲的功能及性质划分,大体有安边型、结交军事同盟、分化瓦解边疆民族政权、借兵及酬恩报德、发展关系、巩固盟好或政治联盟等几种。
 最为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例是“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和蕃”的动人故事。昭君与匈奴单于的联姻,消弭了战争,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不仅带来了唐和吐蕃的友好和平相处,而且促进了唐和吐蕃的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造纸、建筑、酿酒、制墨、冶金等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带去了医生、厨师、乐师等各类专门人才,对吐蕃文化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
最为我们熟知的和亲事例是“昭君出塞”和“文成公主和蕃”的动人故事。昭君与匈奴单于的联姻,消弭了战争,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文成公主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联姻,不仅带来了唐和吐蕃的友好和平相处,而且促进了唐和吐蕃的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了唐朝的造纸、建筑、酿酒、制墨、冶金等各种先进生产技术,带去了医生、厨师、乐师等各类专门人才,对吐蕃文化技术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1-5 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
中国古代,通过朝贡制度维持着相对稳定与和平的周边秩序。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一些学者和政要提出中国很可能想恢复昔日的朝贡制度,并且认为当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可以描述为“朝贡体系再现”。
第一位研究中国崛起思想影响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2010年出版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书,他认为,中国和所有从属国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朝贡体系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这种体系保持长期稳定性的根本原因。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相对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包括东亚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性,结果便是这些国家可能会高度依赖中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以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初级产品为主的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如果从双方经济规模上的巨大差距着眼,那么用朝贡体系的理论进行评判,相比较于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观点更合适。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更是通过中国想要恢复朝贡体系的猜测,表达了他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在格拉汉姆·阿莉森等人所著新书《李光耀:大师论中美和世界》中,李光耀说“中国”就是“中央王国”的意思,这让人回想起其主导东亚的年代,“对东南亚,工业化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像美国自1945年以来那样善意呢?新加坡对这个问题不确定。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或越南都不确定。亚洲很多中小国家很担忧中国可能想恢复昔日的帝国地位,他们担心可能再次沦为不得不向中国进贡的附庸国”
 。
。
强大起来的中国果真意图恢复古代的朝贡制度吗?稍加分析即可得出答案。且不说朝贡制度下的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强制性的进贡关系,周边国家是出于对中国的向往才实行朝贡,以表达对天子的敬意和对中央王国的臣服、归顺之意。对于进贡物品,天子往往予以回赠,且回赠之物多于贡品几倍、几十倍。进行朝贡的周边国家仍具有独立的主权,中国给予其恩惠,但并不干涉其内政,更不对其进行殖民统治。更何况,以现在中国与周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不仅不强迫这些国家“进贡”,反而对这些国家施以大量援助,形式从最初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项目援助到适应受援国实际需要的技术合作项目,如工程承包、劳务合作、技术服务、业务培训、科技交流、合作办厂、合资经营企业等,这无论如何无法用“朝贡制度”进行解释。
三、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实践
秉承以德服人、以和为贵的和平主义文化理念,通过朝贡制度、和亲制度等彰显中华文化“和”特征的制度安排,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成为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一贯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大量的和平实践表现出来。最为我们熟知的事例便是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郑和下西洋。
汉代时期,中国开始了真正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张骞两次通西域,后来班超、甘英西行,他们到达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国家,带去了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而不是兵器,与那里的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友好的贸易往来关系,开辟了丝绸之路。
1405—1433年明代初期,中国开始了历史上最为壮观的航海之旅。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统率当时技术最为先进的舰队出洋,远至爪哇、印度和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欧洲的探险时代尚未开始。据史书记载,宋明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当时的中国舰队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最精良的装备和数量最多的船舰。中国拥有多达4个甲板、4~5个桅杆和12个帆的多层甲板帆船,使用船尾舵驾驶,船上配有航海图和指南针,可容纳500人左右。
 这样的船舰技术配备和规模,即便是150年后才出现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无法与之相比。
这样的船舰技术配备和规模,即便是150年后才出现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无法与之相比。

图1-6 郑和下西洋
经过这样一次规模宏大的航海之旅,郑和却没有为中国攫取任何领土和资源,反而是每到一处,都厚赠他遇到的君主,宣示中国当朝皇帝的德威,邀请他们或亲赴中国,或派遣使者来华,让他们行叩头礼以表示他们认可中国的中心地位,臣服中国,承认皇帝的至尊地位。郑和除了扬天朝之威、通过庄重的仪典显示中国的伟大以外,似乎对开疆扩土、攻城略地并无兴趣。更值得人们思考的是:正当西方对航海兴趣日浓之时,中国的航海能力非但没有得到发展却日渐衰微,中国的航海史就此成了“一片生了锈的合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于明代首都1421年从南京迁往北京后,常常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导致政府对北部边界的关注超过对沿海的关注;二是明代政府更加关心航海的成本和与北方蒙古进行军事对抗的代价;三是明代统治者担心由于沿海中心城市与其他陆地接壤会成为动乱的发源地,影响王朝稳定的统治秩序。在这些原因之外,我们或许还能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得一些启示。
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和自居于世界“中心”的自我认知,加之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和辐射力,使得中国在与外界交往时,始终有“施恩于彼”、使之臣服天朝的情结。这种情结的直接体现便是重视扩大王朝的政治影响,而不是经济剥削和掠夺。《剑桥中国明代史》讲:“在永乐年间,明朝在东南亚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这个区域是皇帝主要关注之处。郑和的探险性远航……是为了通过和平方式扩大明帝国的影响,加强东南部边境的安全。”明代奉行的和平原则始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决心固守中国的“内地”,不再向外扩展以免再生枝节。他以明朝开国之帝的地位,传示子孙后代,声称明军“永不征伐”周边的15个国家。
明代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外国先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说:“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
 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推崇的是热爱和平的性格。它在调解纠纷时根据的是公正的原则,而不是诉诸暴力”
20世纪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在中国人所有的道德品质中,“我最推崇的是热爱和平的性格。它在调解纠纷时根据的是公正的原则,而不是诉诸暴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