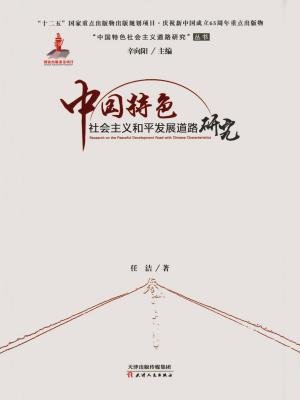第三节 顺应和平发展的世界潮流
2011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对当今世界大势和时代大背景作了如此概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停滞;要对话,不要对抗;要理解,不要隔阂,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

一、和平是世界大势
20世纪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对所有参战国家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无论对战胜国还是对战败国,战争带来的创伤都难以弥合。饱经战争苦难的世界人民,具有阻止战争、暴力和敌对的迫切需要,萌生了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望。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讲,当今时代,发动战争的代价远远高于战争获得的收益。在殖民主义扩张时代,强国只需要付出较少的代价就可以组建军队、发动战争,战利品是相当丰厚的,除了土地、人口,还有大量的能源资源开采权,可谓一本万利。相对微小的代价和相对丰厚的战争收益,成为殖民主义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从当今时代战争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看,除了美国有实力承担巨额的战争费用之外,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发动战争。即使强大如美国,也因为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且并不能如预想的那般实现速战速决而深陷战争泥潭,导致国家经济被拖累,政府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大幅度增长,再加上2008年爆发的金融风暴的打击,整个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中,难以自拔。对于因战争付出的高昂代价,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有深刻认识。2011年9月11日,奥巴马出席了纽约世贸大厦遗址、首都华盛顿五角大楼和宾州尚克斯维尔三处遇袭地的纪念活动,并在当晚出席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会时表示,“9·11”事件后10年的经历证明,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而美国的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发表的《2001年以来的战争代价: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报告,则为奥巴马的论断提供了一个详细的注解。该报告认为,“9·11”事件之后,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美国为进行反恐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些代价既包括那些能够用美元和数字计算的代价,也包括那些无法量化的代价。就美国反恐10年的总代价而言,不仅要考虑美国及其盟友的代价,而且要考虑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平民的代价,还要考虑战斗停止、军队回国后,战争的影响和许多社会与政治代价。
 当今时代,考虑到战争的代价和长久的影响,即使战争胜利,也很难作出战争胜利方就是赢家的论断。发动战争的种种顾虑和出于对战争成本的考量,国家与国家之间轻易不愿意卷入战争的漩涡。
当今时代,考虑到战争的代价和长久的影响,即使战争胜利,也很难作出战争胜利方就是赢家的论断。发动战争的种种顾虑和出于对战争成本的考量,国家与国家之间轻易不愿意卷入战争的漩涡。

图1-14 “9·11”事件中遭受恐怖袭击的纽约世贸大厦
从当今世界格局的现状及发展方向讲,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现行国际秩序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实力较量的结果,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实力对比状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调整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与趋势。苏联解体后,两极称霸的格局终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但是一超独霸的单极格局并未出现,世界各种力量都在发展,比如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区域集团和亚洲地区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涌现,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美国霸权主义时有显露,比如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一切打着“反恐”旗号发动的战争,都表现出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的强势特征,但是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大趋势。从长期来看,美国单极霸权与世界多极化趋势之间的较量和斗争是国际关系的重要矛盾之一。亨廷顿曾指出这种较量和斗争的存在:“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它作为霸主国的单极体系,而且它也经常这样行事,好像这种体系已经存在似的。另一方面,大国们则更愿意建立一个多极体系,以便它们能单独或集体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须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限制、胁迫或压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无论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而言,维护世界和平是众望所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科技革命为推动力,经济全球化不断向纵深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潜力可以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机制中得到良好的结合,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赢”局面。但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发达国家占据有利环节,是世界经济的主要获利者,所以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借助金融手段、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从发展经济、增加贸易往来中获得财富,发动战争对发达国家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损失。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战争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最优的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将面临机遇和风险双重效应,但是除了积极化风险为机遇,抓住机遇发展本国经济,并逐渐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规则外,没有实力也没有意愿发动战争,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对发展中国家是更为有利的选择。
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以和平的方式、合作的态度加以化解。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气候环境变化、严重自然灾害等危及全人类生存、制约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催生了一系列诸如多边合作、全球治理、国际关系民主化等更具和平、合作性质的国际新理念。国际新理念的传播和被接受,又使得国际组织的数量大量增加,这些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国际组织在协调各种国际冲突和矛盾、处理各种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合作、化解全球性危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组织的增长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美国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对国际组织这种国际体系现象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在国际体系关于合作与规制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其中绝大多数对其成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常规性管制。在1909年,全世界共有37个政府间协定组织(IGO)和76个非政府组织(NGO);1951年相应数字分别为123个和832个;1986年分别达到337个和2649个。由这些组织所发起的各类会议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在1838—1860年,每年召开约200次会议;到20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3000次。”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为国家之间通过集体的多边谈判解决国际冲突和矛盾提供了平台,单边的诉诸武力行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机制制约。国际组织的迅速成长和日益拓展的国际影响,成为营造国际合作新理念,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二、发展是世界各国的生存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在亚非拉地区土崩瓦解,一大批主权国家涌现。其中,亚洲出现了7个独立国家,非洲大陆出现了35个新独立的国家,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一年因此被称为“非洲独立年”;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出现了6个独立国家。

图1-15 南部非洲一个新独立国家的独立庆典仪式
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获得国家主权之后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成为这些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因为国家主权的独立并不自然而然带来国家经济的发展,主权独立只意味着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在经济上却依然受宗主国控制。因为漫长的殖民化过程早已经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在宗主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手中,长期依附于西方发达经济,使得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结构单一、过度依靠资源能源输出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低下,这种状况即使获得国家主权独立一时也很难得到根本改变。一位长期从事非洲史和世界现代史研究的学者曾经对非洲发展的起点和历史背景作了如下描述:“非洲是世界上受苦受难最深重的大陆。500年的奴隶贸易破坏了非洲传统社会的生产力,约100年的殖民瓜分和奴役使一切试图走向近代化的改革都化为泡影。独立时,各国只有几家矿山和初级产品加工厂。农村中沿用着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殖民统治造成的二元经济和单一经济结构,使城市之外仍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不少国家要靠出口一两种农矿产品维持生计。它们的经济受外国垄断公司的控制,受国际不平等经济秩序的制约。”
 尽快摆脱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经济体系,成为获得主权独立后国家的迫切任务。
尽快摆脱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民族经济体系,成为获得主权独立后国家的迫切任务。

图1-16 联合国将每年的3月25日设立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奴隶制受害者国际纪念日”
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视为国家的首要目标,还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重要意义。试想,一个经济不发展、不独立,长期作为西方发达经济体附庸的国家,其政治独立又能维持多久?经济不发展,主权独立只能是政治形式上的独立,一个不能依靠自己本国经济发展强大的国家无法保证政治社会稳定,也不能真正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看看非洲一些长期处于种族冲突、内乱和政变状态的国家,就能知道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正是为了真正实现国家独立和社会稳定,所以获得主权独立的“新兴国家”格外重视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调整本国的经济结构,尽快割断本国经济发展与宗主国及西方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脐带。
此外,亚非拉等民族独立国家重视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愿望分外迫切也与西方国家长期推行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有关。现代化作为发源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追溯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有助于阐明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的兴起。现代化理论最初是在欧洲殖民体系崩溃瓦解、冷战的战场迅速向亚非拉第三世界扩散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作为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理论提出的。二战结束后的五年间,涌现了几十个新兴主权国家。当这些新兴的国家与亚非拉地区原有的“欠发达国家”一道要求国际援助以满足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时,就形成了一种全球对抗的局面。
 美国担心苏联蚕食这些“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削弱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联盟体系,期望现代化能够帮助美国战胜苏联的地缘政治野心,并保持美国经济扩张的机会。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曾说,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随着殖民关系的终结,新的极具建设性的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人之间新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一样”
美国担心苏联蚕食这些“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削弱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联盟体系,期望现代化能够帮助美国战胜苏联的地缘政治野心,并保持美国经济扩张的机会。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曾说,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随着殖民关系的终结,新的极具建设性的关系能够被建立起来……这是一种自由人之间新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一样”
 。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欠发达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和它的盟友必须要找到赢得战斗的手段。这种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冈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
。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不同的方式来利用欠发达地区的不稳定性,美国和它的盟友必须要找到赢得战斗的手段。这种战斗“不仅要用武器来打,而且要在生活在村庄里、山冈上的人们的心灵世界中展开,还要靠掌管当地政府的人的精神和政策来打”。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直接介入,积极投身于“现代化的整个创造性进程”
 。于是,现代化理论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论,而且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方法。
。于是,现代化理论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学术理论,而且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手段,还是一种用以帮助美国确定推进、引导和指导全球变迁的方法。
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用现代化理论替代革命理论,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以实现对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和地区“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用现代化理论替代革命理论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时期使用的手段和策略。到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化理论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社会科学不再是单纯的价值无涉的纯粹科学,而成为一种具有感情色彩的文化态度。科学与国家使命感混合了起来。
肯尼迪政府时期,就有一大批思想家如罗斯托、丹尼尔·勒纳、白鲁恂、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等以社会科学为工具,提倡对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进行比较评判。“现代化”涉及经济组织、政治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等方面一系列紧密关联的变化。他们着手研究的问题无非是要创建一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性的坐标体系,以描画全球变迁的总体状况。普林斯顿大学的西里尔·C.布莱克曾提出一个宽泛的界定:所谓“现代化”,就是“历史上演化而来的诸项制度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各种功能的过程,而这些功能反映了人类知识前所未有的巨大增加,使人类得以控制自己的环境”
 。
。
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化进程研究终于主宰了关于国际社会变迁的各种问题的学术研究。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部分集中在以下四个互有重叠、互有关联的假设之上:①“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②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③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④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
 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美国的历史经验昭示着“停滞的”社会进入社会变迁的真正的现代性之路。
理论家们将西方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美国的历史经验昭示着“停滞的”社会进入社会变迁的真正的现代性之路。

图1-17 美国现代化一景:纽约时代广场
20世纪60年代晚期,学界开始了关于现代化模式是否有效的争论。有学者对现代化变迁的整体性观念发起挑战。有学者认为,与工业化世界的联系交往所产生的远非一种有益的“示范效应”,反而经常遗留下破坏和暴力的遗产。依附理论认为拉美等国家地区的欠发达恰恰是因为美国、西欧与它们建立了剥削性的关系。世界体系论从漫长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认为跨国经济关系已经增加了工业化中心国家的财富,同时又将边缘性卫星国锁定在对剥削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屈从位置上。

通过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兴起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现代化理论决不仅仅是一种纯粹学术性的学说,而是社会科学界与美国政界联手推出的为推动本国自身的现代化而创造出的理论形态。社会科学凭借自身具有的那种为社会的孕育、发展、变迁和治理提供合法性依据和阐释的地位和作用,在总结西欧社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一整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阐释,并赋予这种理论以普遍性的特色。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便于进行资本剥削。
西方大国出于意识形态控制与资本剥削的需要,代替视发展为头等生存大事的国家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发展计划,尽管这些计划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意志,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并且还带有许多不平等的附加条件,但是对于迫切需要通过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国家提供的种种发展规划毕竟向他们昭示了一种现代化发展的美好图景。当然,这种看似美妙的发展规划从长期来看却使他们本国经济陷入更大的困境,丧失了发展本国民族经济和转变经济结构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