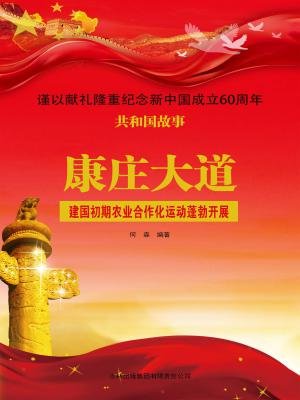毛泽东主张农业合作化
1951年4月17日,正值春暖花开时节,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送交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
山西省委在报告中说:
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方向发展。
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问题如不注意,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这是一方面的情况。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互助组产生了新的因素。
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会后退。
山西省委认为:
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的因素。公共积累,按成员享有,一人一票,出组不带。这虽然没有根本改变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
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红,应当按劳力和按土地两个标准分配,但按土地分配的比例不能大于按劳力分配的比例,并要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加大按劳分配的比例。
这两个进步因素逐步增强,将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前进一步。
在1951年,距离山西全省完成土地改革已经过了5年。
作为最早站稳脚跟的一块土地,中国共产党迅速在这里完成了土地改革。到1946年为止,整个山西省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
1951年,山西省委发现了一个问题。中国老一代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中央农工部的杜润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山西省委了解的情况是,农村这几年有两个新的现象出现:一个是农村阶级有所分化,有人卖地,有高利贷,一部分农民希望向富农方向发展;另一个是原来的长期互助组,特别是高级互助组,现在有些涣散,巩固不下来。
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写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说,有一些互助组得到了巩固,是因为搞了一些公积金和公共财产。赖若愚后来找到了当时长治的地委书记王谦,向王谦表示,长治是太行山革命老区,应该想办法把互助合作组织提高一步。
王谦做了调查研究后,认为可以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农业社,一方面按劳分配,一方面允许土地入股分红。同时要积累一点公共财产,退社时不允许带走。农民的土地也不一定都入社,允许自己留一点,自种自收,一般是80%入社。集体劳动,可以有分工,有公共财产和按劳分配,就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使农村的生产、农民的组织程度都能进一步提高。
杜润生回忆说:
山西报告的另一个方面,是考虑如何在互助组织内部限制富农的问题,因为担心互助组会变成富农的“庄园”。
几乎与此同时,东北人民政府也送上一份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在灯下细细翻阅这个报告。
报告首先列举了东北发展农村经济的成绩,然后写道:
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
报告中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
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
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农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和生活习惯的作用。
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中明确表示:
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
毛泽东看完报告以后,十分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嘛!”
毛泽东提起狼毫小楷毛笔,在报告上飞快地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写下这样几行字:
此件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放下笔,又点燃一支香烟,在房间内踱着步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摊开一张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笺”字样的稿纸,提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
兹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认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
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接下来,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他特意点名要陈伯达主持。
其实,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解放前就十分欣赏“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就已经确立了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农民组织起来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曾经充满激情地对中国未来的合作化远景进行了展望,他对中国未来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作了如下描绘: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