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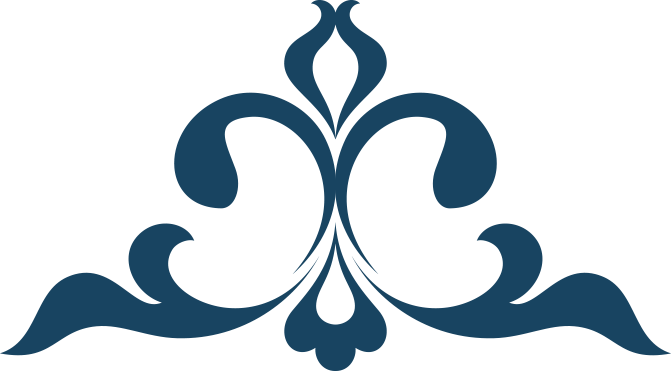
不过,等到我终于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见了面,情况却和之前说的不一样——并不是只跟他认识一下而已。有天早上,斯特里克兰夫人托人送来一张便条,上头写着当天晚上她将举办一场宴会,其中一位客人无法前来,所以希望我能填补这个位置。她是这样写的:
好意提醒,您将会无聊到死。这场宴会从一开始就很乏味,不过如果您能来,我会感激涕零。我们可以在旁边聊聊天。
纯粹为了敦亲睦邻,我接受了她的邀请。
斯特里克兰夫人介绍我的时候,她丈夫相当平常地和我握了手。她则是很兴奋,想用一点儿俏皮话来形容我。
“我请他来,是希望让他看看我真的有个丈夫。我想他已经开始起疑了。”
斯特里克兰礼貌性地笑了笑,就像人们认定一个笑话根本没什么好笑时的反应,不过他并没有说出来。这时来了一批新客人,主人转而去招呼他们,我就被冷落在一旁。最后所有人都到齐了,等着宣布吃饭。我被找去帮忙“接待”一位女宾客,一边闲聊一边想着,文明人有着奇特的巧思,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像这样的聚会,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女主人要大费周章地邀请客人,这些客人又为什么不嫌麻烦地来参加。这天的客人共有十位,他们碰面时态度冷淡,告别时又如释重负。当然,这样的聚会具有纯粹的社交功能——斯特里克兰夫妇受过一些人的邀请,所以“欠”了对方一顿晚餐,尽管他们对这些人没什么兴趣,还是得邀请人家,对方也答应赴会。为什么这些人会来呢?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面对面吃饭太无聊,去别人家吃饭不仅可以让仆人休息一下,也因为找不到理由拒绝,而且还要把“欠”的晚餐讨回来。
饭厅里人一多就有种伸展不开的压迫感。宾客里有一对御用大律师
 夫妇、一对政府官员夫妇、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姊姊及其夫婿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国会议员夫人,正是因为议员发现自己没法从议院抽身,才邀请我来。这些宾客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夫人们非常高雅,所以也没在衣着上太计较,而且彼此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用向谁陪笑脸。男士们正经八百。所有宾客散发出志得意满的气息,一派成功人士模样。
夫妇、一对政府官员夫妇、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姊姊及其夫婿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国会议员夫人,正是因为议员发现自己没法从议院抽身,才邀请我来。这些宾客都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夫人们非常高雅,所以也没在衣着上太计较,而且彼此都很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用向谁陪笑脸。男士们正经八百。所有宾客散发出志得意满的气息,一派成功人士模样。
每个人都出于本能地想让宴会活泼热闹些,音量便比平时高了些,整个房间闹哄哄的。但大家各说各的,没有共同的话题。人人只和邻座说话,如果端上来的是汤、鱼和前菜就和右边的人说话;如果是烤肉、甜点和开胃菜就和左边的人聊天。大家谈的不外乎政治情势、高尔夫球、小孩、新上档的戏剧、皇家学院的画展、天气情况和度假的计划。而大家一开口就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屋子里越来越吵。斯特里克兰夫人也许庆幸这次宴会办得很成功,她丈夫举止有礼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可能是他话不多,我觉得宴会快结束时,他左右两边的女士脸上现出了疲色,她们慢慢发现他是个无聊的人。斯特里克兰夫人不止一次望着他,眼神透着些许忧虑。
最后她站起来,带着一群女宾客离开房间。斯特里克兰在她离开后把门关上,走到桌子另一头,在大律师和政府官员中间坐下。他再次为大家斟了一轮红葡萄酒,并把雪茄递给在场每个人。大律师对手上红酒赞不绝口,斯特里克兰接着说明这瓶酒出自何处。我们的话题转到酿酒和烟草上。大律师说起以前接过的一个案子,上校则在马球的事情上打转。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所以只是静静坐着,很有礼貌地装作对他们的谈话很感兴趣,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在意我的存在,于是放心地观察起斯特里克兰这个人。他比我想象的要壮,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把他想象成身形消瘦、长相平凡。实际上,他体型壮硕、大手大脚,穿起晚宴服有种笨拙感,给人的感觉有点像马车夫为了某个特别日子而穿上正式服装。他大约四十岁,长得并不好看,但也不到丑的地步,因为五官还算端正,只是比一般人大了些,所以整个搭配起来有点朴拙。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一张大脸看起来空荡荡的,让人觉得浑身不对劲。他的发色偏红,剪得很短,眼珠子很小,可能是蓝色或灰色。他看起来一点儿都不起眼。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斯特里克兰夫人提到他时总有点尴尬,对于希望在艺术文学世界取得一席之地的女性来说,他几乎帮不上什么忙,且明显的毫无社交天赋,不过,这并不是男人一定要有的。他甚至连能够显出异于常人之处的怪癖都没有,仅仅是个无趣、诚实、平凡的好人。你会赞赏他的个性,却不愿与他为伍。他没有任何存在感。他也许对社会贡献良多,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也是一个诚实的经纪人,却没有理由该在他身上浪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