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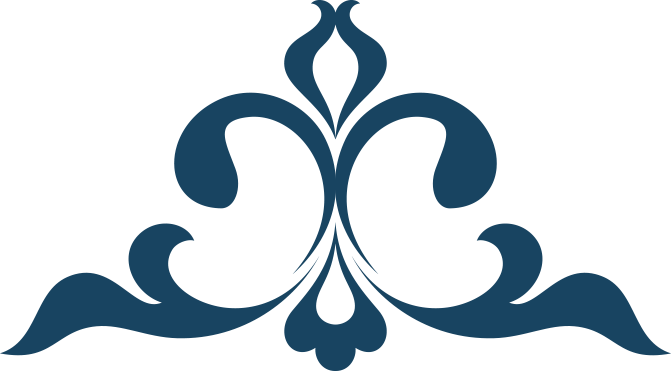
回头看看自己写的东西,我发现斯特里克兰夫妇给人的感觉一定很模糊。我没有把他们的特点好好表现出来,而那正是赋予书中人物真实生命的关键所在。我怀疑问题出在我身上,因此我绞尽脑汁,希望回想起一些与众不同之处,也许能让他们的形象更鲜明。我觉得,要是能描写他们惯用的说话方式,或是生活中奇特的行为,应该就能突显他们独一无二的性格。他们现在有如旧挂毯上的人像,主体和背景难以区分,要是从远一点儿的地方看,甚至连轮廓都看不清楚,只看到一片悦目的颜色。我能找到的解释只有一个——他们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此。他们那种模糊感可以在社会上的某些人身上找到,这些人的生活是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他们只能活在这里面,依赖着它活下去。他们像身体里的细胞,虽然至关重要,但只要它们仍然健康,就会被吞没在整体里。斯特里克兰夫妇属于中产阶级的一般家庭,女主人亲切体贴,对文学圈子里小有名气的作家有种无伤大雅的着迷;男主人相当平凡,在慈悲上帝安排的人生位置上恪尽自己的职责,并且再加上两个容貌端正、健健康康的孩子。没有比这个家庭更寻常的了,我不知道他们身上会有什么事值得追求新奇的人注意。
当我回想后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我扪心自问,是不是我真的太鲁钝,一点儿都看不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与众不同之处。我觉得从过去到现在这段时间,对于“人”,我多多少少累积了相当认识,但就算今天的我遇见了当时的斯特里克兰夫妇,我对他们的评价还是不会有什么不同。然而,也因为我现在很清楚人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如果是今天的我在那年初秋回到伦敦时听见了消息,应该不会太惊讶。
回来不到一天,我就在杰明街上碰到了罗丝·沃特福德。
“你看起来心情好得不得了,”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
她笑了起来,发亮的眼睛里有种我熟悉的恶意。那表示她听到了某个朋友的丑事,而且这位在文学圈子打滚的女性,直觉早已提升得极度敏感。
“你是真的结识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对不对?”
不只表情,她全身上下都散发出警觉敏锐。我点点头。心想,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不是刚在证券交易所大赔了一笔,或在路上被公交车辗了过去。
“这不是糟透了吗?他把自己太太给抛弃了。”
沃特福德小姐肯定觉得在杰明街路边没法让她好好把这事说明白,所以就像个艺术家似的,先丢给你一件没头没脑的事,然后才说详细情况她也不清楚。我不愿让她称心如意,因为我认为处在什么周遭环境这种细枝末节的小事,跟她能否把事情说得明白些,一点儿关系也没有。但她固执得很。
“我跟你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面对我咄咄逼人的问题,她这样回答。接着又轻佻地耸耸肩,“我想,应该有个在城里茶馆做事的年轻女孩辞职了吧。”
她朝着我笑了笑,坚称自己还要去看牙医,便兴高采烈地走了。听她这么说,我其实好奇多于难过。那个时候,和我直接相关的人生经验很少,而这件仿佛书上才有的事,却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实在让人很兴奋。我承认,经过时间的历练,现在看到身边朋友发生这类事情已很习惯,但当时的我是有些震惊的。斯特里克兰肯定有四十岁了,我觉得像他这种年纪的男人还移情别恋,真让人厌恶。我年纪轻,却傲气十足,认为一个男人谈恋爱的上限是三十五岁,过了这个年龄就会被当成笑话看。而且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我人还在乡间住处时已写信给斯特里克兰夫人,告知我何时将回伦敦,并注明若未收到回信,便会在抵达当天找她喝茶。今天就是信里说的那个日子,我并未收到她任何通知。她到底想不想和我见面呢?斯特里克兰夫人此时很可能心烦意乱,而忘了我信里说的事。也许我该识相点,别去打扰她。但另一方面,她也许不希望别人知道这件事,如果被她发现我已知道了这件不寻常的事,那可能会显得我很粗心。我一方面害怕伤了一个好女人的心,一方面担心去了给人添麻烦,两头为难。我可以感觉到她现在心里一定不好受,我实在不愿看别人难过,自己却帮不上忙。但说来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其实又很希望看看她怎么面对这件事。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最后,我灵机一动,只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前去拜访,并请女佣传话,询问斯特里克兰夫人是否方便见面。如此一来,便可让她有机会拒绝这次的拜访。尽管如此,当我对女佣说出这套准备好的说辞时,仍然尴尬得手足无措,在黑暗的走廊上等待回话时,还必须在心里鼓起十足的勇气才没落荒而逃。女佣回来了,这时我心情激动、想象力十足,总觉得从她的样子看来,她好像已完全知道这个家所发生的憾事。
“先生,请这边走。”她说。
我跟着她进了客厅,窗帘拉上了一部分,好让房间暗些,斯特里克兰夫人背光坐着,她姐夫麦克安德鲁上校则站在壁炉前方,借着炉里不太旺的火暖背。我自觉进来这里真的非常尴尬,猜想这次来访一定吓了他们一跳——斯特里克兰夫人只是因为忘了回绝信里的约会才让我进门,又想到,我这样打扰了他们的谈话,她的上校姐夫一定很不高兴。
“我不是很确定你是不是在等我来。”我尽可能若无其事地说。
“当然,我一直在等你。安等一下会送茶过来。”
即使房里不太亮,我还是看得出斯特里克兰夫人的脸因流泪而浮肿。她的皮肤原本就不太好,现在更是泛着土黄。
“你还记得我姐夫,对吗?你们那次吃晚餐时见过面,就在放假之前。”
我们握了握手。我一直提心吊胆,想不出该说些什么,但斯特里克兰夫人此时解救了我。她问我夏天都做了些什么,因为她的帮忙,我才想到一点儿话题,一直聊到茶送上来。上校则要了一杯苏打威士忌。
“艾米,你最好也来一杯。”他说。
“不了,我比较想喝茶。”
这句话首次暗示了遗憾的事已经发生。我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上头,只是很努力地找话和斯特里克兰夫人聊。上校仍站在壁炉前,一声不吭。我心里盘算着要在这里待多久才不失礼,另外也一直疑惑着到底为什么斯特里克兰夫人要让我进门。客厅里没有花,夏天时收起来的各种小摆饰也还没重新归位,这个总是亲切温馨的空间变得有些凄凉沉重,仿佛墙的另一侧正停放着某个去世的人。我将茶一饮而尽。
“你要不要抽根烟?”斯特里克兰夫人问。
她想把烟盒找出来,却遍寻不着。
“我想可能是没了。”
她突然痛哭失声,匆匆离开客厅。
我被她的反应吓一跳。现在回想起来,我猜是因为以前烟抽完了通常由她丈夫补充,此时却被迫想起这幕情景。过去她看到烟盒总会感到小小的幸福,如今习以为常的物品却消失,这种新的感觉让她突然悲从中来。她明白以前的日子再也不会回来了,到此结束。我们之间的社交辞令也无法再往下进行。
“我想你会希望我现在就走。”我一边起身,一边对上校说。
“我猜你已经听说那个无赖抛弃她的事了吧?”他爆炸似的大吼。
我犹豫着该说些什么。
“你知道外头的人是怎么说三道四的,”我回答,“只是有人跟我提了一下,说好像有点问题。”
“他跑了,跟一个女人跑去巴黎,连一分钱也没留给艾米。”
“我真的很遗憾。”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
上校把手上的威士忌一口喝掉。他大约五十岁,又瘦又高,蓄着下垂的胡须,头发已经花白。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唇很薄。我记得上次和他见面时,他的脸给我一种蠢笨的印象,当时他还很骄傲自己在退伍前十年,每周都会花三天打马球。
“我想斯特里克兰夫人现在不会希望我在这里让她烦心,”我说,“你能帮我告诉她,我真的很为她的遭遇难过吗?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得上的忙,我一定很乐意去做。”
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我不知道她接下来要怎么办?身边还带着小孩。他们要靠空气生活吗?十七年啊!”
“什么十七年?”
“他们的婚姻。”他狠狠地说,“我一直不喜欢他。当然,他是我连襟,我也就能忍则忍。你以为他是正人君子吗?她本来就不该嫁给他。”
“事情成定局了吗?”
“她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离婚。你进来的时候,我正要告诉她这个。‘亲爱的艾米,把申请离婚的文件送出去吧,’我这样对她说,‘不管是为了你自己,或是为了孩子。’他最好别让我撞见,要不然一定被我揍个半死。”
我忍不住想,麦克安德鲁上校要做到他所说的可能有点困难,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斯特里克兰身形魁梧,不过,我没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因道德受到侵害而义愤填膺、却又缺乏直接制裁对方的力量,实在是件悲惨的事。我正打定主意再次试着向他告辞,斯特里克兰夫人就回来了。她已把眼泪擦干,并在鼻子上扑了些粉。
“很抱歉,我情绪失控了,”她说,“我很高兴你没走。”
她坐下来。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总觉得不太敢提那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我那时还不了解女人有种难以根除的坏习惯,她们很乐意讨论自己的私事,不管是谁都好,只要愿意听。斯特里克兰夫人似乎正努力压抑着自己。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吗?”她问。
她以为我对她的不幸遭遇一清二楚,这实在让我很吃惊。
“我其实才刚回伦敦,只和罗丝·沃特福德碰过面而已。”
斯特里克兰夫人双手紧握。
“告诉我,她怎么说,一个字都别漏掉。”我还在犹豫,她却非知道不可。“我特别想听她说了什么。”
“你知道大家谈论事情就是那个样子。她说话不太靠得住的,对不对?她说你丈夫离开你了。”
“就只有这样吗?”
我不打算说出沃特福德小姐离开时提到的茶馆女孩。我说了谎。
“她没有说他跟什么人走了吗?”
“没有。”
“这就是我最想知道的。”
我有点困惑,但不管怎样,我知道现在该起身告辞了。和斯特里克兰夫人握手道别时,我告诉她,要是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我都很乐意帮忙。她憔悴的微微一笑。
“多谢你。我不知道有谁能帮上我的忙。”
我不好意思表达我的同情,只好转身向上校告别。他没有和我握手。
“我也要离开了。如果你要往维多利亚街去,我跟你一起走。”
“好,”我说,“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