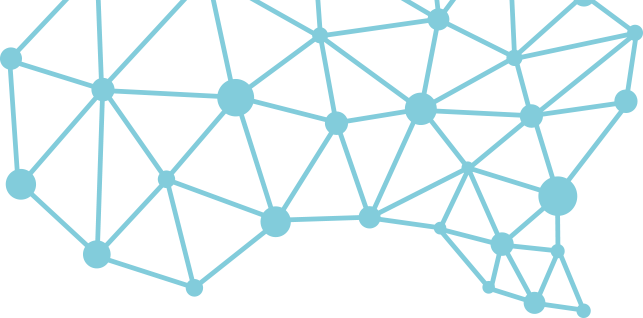
从虫子检测器到概念细胞
青蛙视网膜告诉了青蛙脑什么?
哈特兰在发现蛙视网膜上有给光细胞、撤光细胞和给光—撤光细胞以后,人们就对这些细胞的功能意义很感兴趣。1959年,美国神经科学家莱特文(Jarome Lettvin)
 等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青蛙视网膜告诉了青蛙脑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他们之所以选择青蛙作为实验动物,是因为青蛙的视觉系统比较简单,只有视网膜和上丘两级;并且青蛙的反应也比较简单,它只能看到运动的东西。如果在它身边放上一圈静止的食物,那么它直至饿死都不会去吃;如果用任何昆虫样大小的东西在它面前晃动,它就会去捕捉;而对于任何巨物的迫近,它都会逃之夭夭。
等人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青蛙视网膜告诉了青蛙脑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他们之所以选择青蛙作为实验动物,是因为青蛙的视觉系统比较简单,只有视网膜和上丘两级;并且青蛙的反应也比较简单,它只能看到运动的东西。如果在它身边放上一圈静止的食物,那么它直至饿死都不会去吃;如果用任何昆虫样大小的东西在它面前晃动,它就会去捕捉;而对于任何巨物的迫近,它都会逃之夭夭。
莱特文等人记起以前英国神经科学家巴洛(Horace Barlow)报道过,给光—撤光细胞特别对运动敏感。因此他们想:也许不必拘泥于用小光点一点一点地探测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感受野,而可以用一些有生物学意义的图形刺激细胞的整个感受野。为此,他们用一个铝制半球作为天幕,而让青蛙居中“观天”。他们用一些黑色铁圆斑片(大小合适时就像一个虫子)或是相当大的黑铁长方形放在天幕内壁,而用一个磁铁在天幕外移动它们。
结果他们发现有四类神经节细胞:(1)对整个背景光的照亮或是变暗都没有反应,但是如果有一个亮于(或暗于)背景的边缘进入细胞的感受野并停在那儿的话,细胞就有猛烈的发放。他们把这种细胞称为“持续反差检测器”。(2)第二类细胞也对整个背景光的加强或减弱不起反应,但是如果有一个3°大小(或更小,但不能小于0.5°)的圆斑通过其感受野,它就有反应,但是有直边的黑色物体通过其感受野则没有反应。他们把这称之为“凸边检测器”,人们认为青蛙可能利用这一检测器来检测苍蝇之类的虫子,因此得到了“虫子检测器”的外号。(3)第三类细胞就是哈特兰的给光—撤光细胞,它仅对移动的明暗边缘有反应,如果一个物体的宽度超过5°,那么当它越过感受野的时候,其前沿和后沿会分别引起这个细胞的反应,他们把它称为“运动边界检测器”。人们猜测这种检测器可能是用以检测庞大的敌人正在迫近。(4)第四类细胞就是哈特兰的撤光细胞,它在感受野所受到的光线变暗时有反应,因此被称为“变暗检测器”。
他们的这一工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以前人们多用光点这样比较简单的刺激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样的刺激并不自然。他们所用的刺激则更像是飞近的苍蝇或是迫近的巨兽……这些对象——食物或是天敌——对它们的生存来说意义重大。这样他们的研究就为我们认识动物如何检测对它们的生存有意义的目标的神经机制提供了线索。在哺乳动物的视网膜中没有发现类似的检测器,这可能是因为哺乳动物的视觉系统要远比青蛙高级,此类任务不再由视网膜担任,而由视觉皮层来负责了。休伯尔和维泽尔在哺乳动物初级视皮层中所发现的简单细胞的功能可能就是检测外界事物的边框。那么在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中有没有检测对生物的生存更有意义的目标的检测器呢?
“识别细胞”和“祖母细胞”
20世纪60年代初,波兰心理学家科诺尔斯基(Jerzy Konorski)就提出过“识别细胞”(gnostic cell)的概念,他认为这种细胞可能能知觉到一些复杂的对象,他猜测这种细胞位于下颞叶皮层,而识别对象是掌形、脸形以及脸部表情。
1972年,巴洛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单个单元和感觉:知觉心理学的神经元学说》(Single Units and Sensation:A Neuron Doctrine for Perceptual Psychology),文章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点清了问题:“在本文中我将讨论一个既困难又带有挑战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主观知觉和我们脑中神经细胞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过他把这种细胞称为“主教神经元”(cardinal neurons)。他认为,这种神经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对视网膜上所受到的照明的某些简单特征起反应,而是对某些复杂的外界对象模式(例如人脸)起反应。他说道:“这种细胞的作用是表征场景。”这种细胞“并不是对环境中任意的特征作表征……它们起到所知觉到的对象的特征的相关物的作用”。他把他的思想总结为下面5条:
1. 如果想认识神经的功能,就需要在细胞层次上(不是在更宏观的层次上,也不是在更微观的层次上)观察其中的相互作用,因为行为取决于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组织模式。
2. 对于感觉刺激来说,感觉系统用数量尽可能少的活动神经元给出完整的表征。
3. 通过经验和发育过程,感觉神经元的触发特征和刺激的有冗余的模式相匹配。
4. 知觉就对应于一小群神经元的活动,这些神经元是从大量的高层次的神经元中挑选出来的,每个这种活动就对应于外界事件的一种模式,这种事件的复杂程度可以用某个单词来表示。
5. 如果这种神经元有猛烈的发放的话,这就可以相当肯定确实有相应的触发特征存在。
接下来登场的是美国心理学家格罗斯(Charles Gross)。格罗斯1961年获得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当时莱特文也在同一座大楼里研究他的虫子检测器,并且讲了一个后来闻名遐迩的有关“祖母细胞”的笑话(这个笑话我们下面还要讲);而在一河之隔的哈佛医学院,休伯尔和维泽尔则在脑皮层的18区和19区发现了复杂细胞。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格罗斯等人想知道猴下颞叶皮层的神经元对哪种视觉刺激最敏感。一开始他们用传统的光刺激,结果什么反应也没有。后来他们用手掌在刺激屏幕上舞动,结果细胞就猛烈地发放起来,这真令他们喜出望外,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他们用纸片剪成各种形状作为刺激进行试探,然后按细胞反应的剧烈程度把这些刺激排列起来,结果发现不能用任何一种简单的图形特征来说明,但是非常明显的是这种细胞的反应强度和刺激与猴掌的相似程度有关。很明显,猴掌对猴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格罗斯等人认为这种神经元的功能就是检测掌形。
后来他们又在猴的下颞叶皮层中发现了专门检测脸形的神经元,他们还发现有一种神经元只有当图片中的猴脸正对着观看图片的猴时才有最大的发放,当图片中的猴脸逐步向一边偏转时,发放就会跟着减小。若把正面猴脸照片中的眼或嘴涂去,或是用一张人脸来代替猴脸,发放也会减小。如果看的是猴头的背影或是一把马桶刷,发放就很小,给它看手掌发放就更小了。如果把猴脸的照片剪碎后重新随机拼接成一张图,虽然这张图中的线条元素和原来的猴脸图完全一样,但是它看上去已不是猴脸了,这时的发放非常小。格罗斯的实验是对“识别细胞”(或者“主教细胞”)假说的极大支持。
尽管科诺尔斯基早就提出了“识别神经元”的概念,巴洛也提出了类似的“主教神经元”的概念,但是真正使这一猜想广为人知的是莱特文根据一本小说里的人物波特诺伊(Alexander Portnoy)编的一个故事:
波特诺伊的母亲非常专横,每次一想到她,波特诺伊都非常痛苦。这时正好有一位神经外科医生阿卡希维奇(Akakhi Akakhievitch)发现脑中有18 000个神经元只对自己的母亲起反应。于是,波特诺伊就请医生把他脑中所有这些细胞都一一清除掉。手术完成后,医生为了检验效果就问了他两个问题:
“你还记得你每周四晚上都爱吃的薄饼吗?”
“当然记得,太好吃了。”
“那么是谁给你做的这种饼呢?”
波特诺伊茫然地看着医生不知所对。
莱特文把这个故事讲给学生听以后,还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阿卡希维奇医生接下来就研究祖母细胞了。他的故事大获成功,不胫而走,成了科学家们热议的话题,“祖母细胞”也就成了一个科学术语,反而“识别细胞”不大为人所知了。
在莱特文提出祖母细胞概念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太注意他所讲的故事里的细胞和格罗斯所发现的脸形细胞或掌形细胞之间的微妙差别,后者主要是对一类特定的视觉刺激有选择性的反应,当时人们对识别细胞和主教细胞,以至祖母细胞的理解也是这样。但是,格罗斯的“掌形细胞”和“脸形细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视觉特征检测器,不过它检测的对象更为复杂,例如手掌(随便什么样的手掌)或是猴脸(随便什么样的正面猴脸),而不是检测某个特定对象的概念本身。而莱特文讲的“祖母细胞”实际上比格罗斯的“掌形细胞”或“脸形细胞”还要更抽象一些,它牵涉的已经是和祖母这一概念有关的一切,而不再局限于祖母正面的视觉形象了。但是在开始时人们并没有太注意这些区别,而把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杂起来了。
从概念细胞到读心术
尽管格罗斯的实验支持了存在着祖母细胞或者说识别细胞的可能性,但是还是有许多科学家对此表示怀疑。20世纪80年代,休伯尔曾说过:“对祖母细胞理论是很难当真的。”反对者的主要论据是:如果对世界上每个特殊的事物脑中都要专门有一个细胞对此起反应,那么由于世上的由不同特征组合起来的不同事物数无穷无尽,脑子里的神经细胞数目再多也还是不够用。这被称为“组合爆炸”。何况为了保险起见,每个这样的细胞还必须有备份,那就更不够用了。所以这些科学家认为应该用组合对付组合,即对每一个特殊的对象都有一组神经元构成的集群和它对应,但是和不同对象对应的不同集群可以共用某些神经元。这样不仅能解决由一些特征的不同组合可以构成许多不同对象的“组合爆炸”问题,也能回答为什么即使有些神经元死亡以后,不会对我们辨识不同对象产生灾难性影响的问题。然而以后的进一步工作说明了识别细胞甚至祖母细胞确实还是存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任何事物在脑中都有一个特定的神经细胞和它对应。
20世纪90年代在许多医院中,为了治疗药石无效的癫痫病人,只能动手术切除病灶,为了确定这些病灶究竟在什么部位,需要在脑中埋藏多到10根的电极,并日夜监视这些神经元的活动,以确定哪些部位最先发生癫痫活动,由此得以确定病灶的精确部位。在等待病人癫痫发作的那段时间里,研究人员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研究意识清醒的人脑中单个神经元对什么样的刺激才有强烈的反应。从1992年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外科医生弗里德(Itzhak Fried)的实验室里,研究人员让病人看演员、政治家、动物、建筑物等的图片,同时监视其内侧颞叶皮层(许多癫痫都是由此而起)的神经元,例如杏仁体神经元[它接受来自高级视皮层区域(和其他区域)的输入]的活动。英国生物工程师奎洛伽(R.Quian Quiroga)也参与了这一研究。在50幅图片中,病人的杏仁体神经元只对其中的3幅有反应: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漫画、他的总统标准像,以及他和其他人在一起的合影。这个神经元对其他名人或其他总统的图片都没有发放。考虑到克林顿总统的知名度,对于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克林顿总统,患者脑中能够形成针对他的神经元是可以理解的。也许识别细胞只对经常要接触到的对象(例如,名人、自己的祖母、狗,等等)起反应。但是对于他所不熟悉的人或物则需要许多神经元组成的集群才能表征。上面讲的两种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
后来,奎洛伽在病人脑中同时监视40个神经元。他在每次试验以前都会询问病人最感兴趣的是谁,然后把有关这个人的图片放到100张左右的测试图片之中。结果,他在某些病人的海马神经元中又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神经元,虽然这一次这些神经元起反应的不再是克林顿总统的照片。奎洛伽给病人看各种各样的照片,其中包括当红女星安妮斯顿[Jennifer Aniston,就是在美国电视连续剧《老友记》( Friends )中扮演瑞秋(Rachel)的那位女星]的各种照片,还有其他人的照片,风景照,动物和物体的照片。结果他在病人的海马中找到一些细胞,它们对安妮斯顿的各种照片都有猛烈的反应,而对其他照片都“视若无睹”。他在海马中还找到另一个细胞,它只对电影明星贝里(Halle Berry)起反应,不过这一次这个神经元不仅对贝里的标准照起反应,对她在《蝙蝠侠》( Batman )一片中扮演的戴有面罩的猫女形象也有反应,甚至对屏幕上显示的她的名字都有反应,但对其他人像、建筑物和动物都很少反应。所以在这里引起反应的已经不只是贝里的视觉形象,而且是贝里这位女演员的概念。奎洛伽甚至还发现,在一位酷爱数学的工程师的海马中有只对毕达哥拉斯定理a 2 +b 2 =c 2 才有反应的细胞。因此,他把这样的细胞称为“概念细胞”。另外,杏仁体和海马都不是负责视觉的脑区,所以牵涉的问题不只是特定对象的视觉形象,还牵涉对某个概念的记忆。
当然,像安妮斯顿细胞这样的神经元不可能是生来就有的,由于你经常看见名人、熟人或你熟悉的事物,每次见到时,在你的某些脑区中都有神经元发放类似的模式,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细胞。对于你偶尔遇到的人或物,就不会有此类概念细胞与之相对应。
概念细胞的发现给在特定条件下“读心”以新的可能性。美国加州工学院科赫实验室的瑟夫(Moran Cerf)在一位病人的脑里记录到一个对电影演员布洛林[Josh Brolin,《七宝奇谋》( The Goonies )中的主角]起反应的细胞,另外还记录到一个梦露(Marilyn Monroe)神经元。瑟夫在给她看的屏幕上同时显示布洛林和梦露的影像,当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布洛林上时,布洛林神经元的发放要强过梦露细胞。然后瑟夫用一个反馈电路,使得布洛林的影像逐渐清晰,梦露的影像逐渐变淡,直到实验结束时,显示屏上就只剩下布洛林的影像,病人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她觉得是自己的意念控制了这一切。而在一旁的医生也一目了然地知道当时她想到的究竟是谁。当然,这样的“读心术”的能力还非常有限,只有在找到了一些概念细胞,并且在事先就知道这些概念细胞所对应的是什么概念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