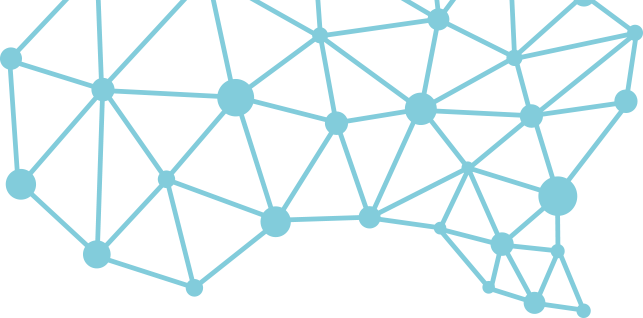
不可不知的视觉感受野
视觉感受野概念的提出

图1-11哈特兰。 196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
美国生物物理学家哈特兰(Haldan Keffer Hartline)受英国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Edgar Douglas Adrian)记录单个神经细胞活动的启发,对研究视觉神经元的单细胞记录很感兴趣,他发现蛙的视网膜是上天给他的一个很理想的标本。20世纪30年代初,在电子管放大器刚刚被引入到生理学研究中的时候,哈特兰以其对新技术的敏感性,从暴露出来的蛙视网膜表面挑起一小束视神经,然后把其中的纤维一根一根逐步剔除,直到最后只剩下一根视神经。这样就远在微电极技术发明出来之前,他就已经能够记录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了。
哈特兰发现,蛙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对光刺激的反应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只在给光和撤光的时候才有反应,或是在光强略有变化的时候才有反应;有的则在给光的整个时段内全无反应,而只在撤光的时候才有发放。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对有些神经节细胞来说,只有当小光点或小暗点在视网膜的很小一块区域里运动时,这个细胞才会有发放。
哈特兰发现对某个神经节细胞来说,只有当光刺激落在视网膜上一定范围的区域里时才能引起反应,或者说使其发放模式产生变化,他把这样的区域称为这个神经节细胞的“感受野”。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谢林顿(Charles Sherrington)于1906年首先提出的,他把能引起抓搔反射的皮肤表面称为该反射的“感受野”,哈特兰把这一术语借用到了视觉系统。不同细胞的感受野在视网膜上彼此交叠,并且这些细胞的反应模式可能各不相同,这说明在视网膜中有着相互作用,并且已经进行了相当复杂的信息处理。
感受野的结构和种类
匈牙利裔美国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库夫勒(Stephen W.Kuffler)是德裔英国神经科学家卡茨(Bernard Katz)和澳大利亚神经科学家艾克尔斯(John Carew Eccles)的学生,他把哈特兰的工作推广到了哺乳动物。利用自己和朋友塔尔博特(S.A.Talbot)发明的新型眼底镜,1952年库夫勒用很小的光斑或暗斑精确地刺激猫视网膜上的特定区域,结果发现猫的感受野并不是均匀的,而是有一定的结构,大体上表现出同心圆状的结构。库夫勒还发现有两类不同的感受野。一类是给光中心感受野,当在其中心区加上光刺激时,细胞有猛烈的发放,而在撤去光刺激时则没有反应;当把光加到感受野的外周部分时,细胞没有反应,但是如果把光撤掉,细胞就有猛烈的发放。他把这样的细胞称为“给光细胞”。另一类则正好相反:中心是撤光区,而外周则是给光区。他把这样的细胞称为“撤光细胞”。如果同时在中心和外周给光或撤光,则它们的作用正好对消。以前人们用的光刺激大多是明亮的闪光或是弥散光,它们都遍布这两个区域,其作用正好相互对消,因此看不到细胞有明显的反应。这实际上提示了,为了研究视觉细胞的特性,选择适当的光刺激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在库夫勒发表了这些新发现以后,他在一次学术会议的走廊里正巧遇到他仰慕已久的阿德里安。阿德里安立即停了下来,问了他一句话:“脑里的细胞也是这样的吗?”
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库夫勒的两位博士后休伯尔(David Hubel)和维泽尔(Torsten Wiesel)。他们后来和因对裂脑动物研究而声名大噪的美国神经科学家斯佩里一起分享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库夫勒本人则因为在1980年过早地去世,而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
一场不对等的竞争
休伯尔的父母都是美国人,后来移民加拿大,因此休伯尔一出生就拥有美、加双重国籍。他在麦吉尔大学主修数学与物理,读研究生时却转为医学,并且在195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1954年,他来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内科住院医生。但很快,他就被征召入伍,在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工作。1958年,休伯尔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开始了与维泽尔长达25年的合作,在沃尔特·里德研究所工作时,休伯尔已在猫的外侧膝状体和初级视皮层方面有了一些研究,他还发明了钨丝电极,并用其在脑中各处进行记录。维泽尔正是在到休伯尔那儿取经,学习钨丝电极的制备和应用时,认识休伯尔的。
当时休伯尔把钨丝电极埋藏在猫脑中,比较猫在睡眠和清醒时视觉通路中细胞的发放模式有什么不同,其目的是想阐明睡眠对皮层的影响问题。当他把自己准备从初级视皮层进行记录的计划告诉同事时,许多同事的反应都是:“为什么要研究纹状皮层呢?荣格(Richard Jung)已经彻底地对此进行过研究了。”
事实上,德国神经科学家荣格的实验室从1952年起就开始研究纹状皮层单细胞对光刺激的反应了。他们花了2年时间建立起了一套当时最先进的记录视皮层细胞的仪器,用的刺激光是弥散光。荣格研究组最终发现,初级视皮层的细胞按照其对弥散光的反应可以分成四大类:只在给光时有反应的给光细胞,只在撤光时才有反应的撤光细胞,在给光或撤光时均有反应的给光—撤光细胞,以及对弥散光刺激根本没有反应的细胞。荣格研究组将最后一类细胞称为A型细胞。
既然对象一样,休伯尔怎样和荣格竞争呢?要知道荣格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而休伯尔只有一套东拼西凑而成的老设备;荣格在视皮层上已经工作了6年,他的团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在视皮层单细胞上进行过记录的实验组,而休伯尔才刚刚进入视皮层研究的领域;荣格当时已经是视皮层生理学研究的权威,而休伯尔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博士后。不过休伯尔并不感到担心,因为当时他的目的是研究睡眠对皮层的影响,而对视觉的研究只是一种副业罢了。
最初,休伯尔采用的刺激也是弥散光,因为当猫睡眠时透过眼睑的光都是弥散的,为了进行对照实验,休伯尔对清醒猫使用的刺激也是弥散光。他很快就重复出了荣格的主要工作,并且在实验结束之后均标定了所记录的位置。而定位的结果表明有些荣格所讲的给光细胞是从白质上记录到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能排除荣格所讲的皮层细胞中,有些可能实质上是源自外膝体的神经纤维,而非皮层细胞。休伯尔发现有大量细胞对弥散光根本没有反应,应属于荣格所说的A型细胞。休伯尔想也许运动是比单纯给弥散光更有意义的刺激,于是他在猫的眼前挥手,结果发现有些细胞对手的运动方向有选择性,这是提示视皮层细胞在功能上比外膝体细胞要更复杂的第一个迹象。最后,他发现正是那些对弥散光不起反应的细胞才是视皮层细胞,而荣格所发现的“给光细胞”、“撤光细胞”和“给光—撤光细胞”实际上都是从外膝体发出的神经纤维。这样,荣格的发现除了视皮层细胞对弥散光不起反应之外并没有多大内容。
珠联璧合的美妙合作
前面说过,休伯尔的实验发现有大量细胞对弥散光根本没有反应,可见弥散光并不是有效刺激。因此,在1958年回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之后,休伯尔觉得是该改变一下刺激模式的时候了。他认为视皮层犹如一座金矿,正有待人们用适当的方式去开采。
休伯尔的原定计划是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芒卡斯尔(Vernon Mountcastle)教授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芒卡斯尔是研究躯体感觉的先驱,正是他发现了初级体感皮层中的不同神经元对不同类型的触觉有反应:有的神经元对皮肤表面的触觉有反应,有的神经元对深压有反应,但是几乎没有一个神经元对两者都有反应。另外,芒卡斯尔还发现这些不同类型的神经元组成柱状结构,从皮层表面垂直向下延伸2毫米左右。他认为每个这样的柱体都构成了一个整合的单位,它们很可能是皮层组织的基本形式。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他的这些先驱性的思想将对休伯尔和维泽尔有多大的启发。
但是时机不巧(从后果来说,应该讲是太巧了),芒卡斯尔的实验室正在改建,需时一年。有一天库夫勒打电话问休伯尔愿不愿意在芒卡斯尔的实验室改建完成以前,先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他的实验室里和维泽尔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休伯尔本来就渴望在视觉方面接受严格的训练,而他和维泽尔又意气相投,所以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休伯尔和维泽尔的工作计划并不难制定。还记得阿德里安向库夫勒提出的问题吗?“脑里的细胞也是这样的吗?”休伯尔和维泽尔的目标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自然”的想法是用库夫勒研究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去研究外侧膝状体或初级视皮层细胞。方法很现成,一切似乎都可以按部就班地去做:把微电极插到外侧膝状体或者初级视皮层的神经细胞里面去,然后用小光点一点点地在视网膜上探测,看它落在视网膜的哪些地方,所记录的神经细胞的发放模式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变化,并且把视网膜上的这些地方标出来,这样就可以得出这些细胞的感受野的相应结构。
休伯尔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以后,立刻就和维泽尔一起投入了工作。休伯尔以前对外侧膝状体做过一些工作,用的就是类似于库夫勒的实验方法,方法很有效,结果和从视网膜上的神经节细胞所得的结果也相仿,他确信那里的细胞也是中心—外周型的,所以他们决定一开始就直接研究视皮层。
因为当时休伯尔预计自己在库夫勒实验室的工作只有一年,显然他不可能像荣格那样先花两年时间建立一套完善的实验设备,那只能因陋就简了:他们所有的刺激和记录设备都是多年以前库夫勒为了研究视网膜设计的。光刺激器是用一台眼底镜改装而成,它可以把背景光和光点刺激投射到视网膜上去。仪器上有一道狭缝用于插入金属薄片,薄片上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小孔,这些小孔是用来透光的,就像放幻灯片那样。如果刺激是一个暗点,那么就用一小块上面粘有一个黑点的玻璃片来代替。这样的仪器对于做视网膜实验自然是很理想的,实验中猫脸朝上,做实验的人可以看到微电极插到视网膜的什么地方,也可以看到光点落在视网膜的什么地方,但是用它来记录皮层细胞就非常不方便了。因为对于皮层细胞来说,实验者事先根本不能预测它的感受野会在视网膜上的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只好在视网膜上到处去找,并且往往还记不清哪些地方已经刺激过了。一个月以后,他们决定把刺激投射到一块屏幕上,让猫看屏幕。由于他们没有其他的设备可以固定猫的脑袋不动,所以还是用那台老的仪器,猫脸依然朝上。这样他们不得不拿一条床单挂在天花板上作为屏幕,弄得实验室看起来有点像马戏场似的。有一天,芒卡斯尔走进来看到这种景象,大吃了一惊。
这样做实验自然不大方便,因为在整个实验期间,他们都不得不仰头朝天看着天花板。于是,休伯尔想到在芒卡斯尔的实验室里有一台猫头固定器闲置在那里没有用,而且在它上面还有眼科研究所的铭牌呢。这台固定器是研究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前在研究视皮层时用的,后来芒卡斯尔又用它来研究躯体感觉工作了好多年。休伯尔和维泽尔虽然心存顾虑,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要回这台仪器。为了看起来像回事,他们都第一次,也是生平最后一次穿上了实验室的白大褂,走进芒卡斯尔的实验室。虽然芒卡斯尔平时总是那么的友好和慷慨,但是要他放弃这件宝贝毕竟还是有点困难的,可不锈钢架上的刻字是无可否认的,所以最后他们得胜而归。
他们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很有戏剧性。休伯尔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回忆说:
我们最初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们做了一个月左右的实验。我们用的还是那台塔尔博特—库夫勒眼底镜,但是进展甚微:我们记录的皮层细胞对光点和光环根本就没有反应。有一天,我们记录到了一个特别稳定的细胞。……它一直工作了9个小时,其结果使我们对有关皮层是如何工作的这一问题的想法大为改观。在起初的三四个小时里我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后来当刺激视网膜靠近外周的一些地方时,我们得到了一些没有规则的反应。但是,当我们把中间粘有黑点的玻璃片插到投影眼底镜里面去的时候,用来监视神经脉冲发放的扬声器发出一连串像机关枪一样的声响。在经过一阵茫然不知所措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引起神经细胞发放的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反应和玻璃片上的黑点一点关系都没有。实际上,是我们在把玻璃片插到缝里去的时候,玻璃片的边缘在视网膜上投下了一条虽然比较暗淡但是却很分明的阴影,也就是说,在亮背景上的一条暗直线刺激了细胞的感受野。这就是引起这个细胞发放所需要的刺激。不仅如此,要这个细胞引起反应,这种直线的朝向还只能落在一个很小的角度范围里。
他们将这个特定的朝向称为该细胞的最优朝向,其变化范围只有15°左右,也就是大致相当于钟面上2.5分钟所张的角度,朝向在此范围之外的暗直线就不会引起该细胞反应。这完全是前人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机会永远只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一个真正的科研人员的头脑必须永远是开放的。如果他们坚持前人的传统观点(哪怕是权威的观点),认为小光点是最基本的刺激(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合乎逻辑”的,前人在视网膜上用它作为刺激所做的工作又是那样的成功,而他们自己在外侧膝状体上的工作也支持了这一点!),如果他们坚持认为视觉皮层细胞的特性也只可以用它们对小光点刺激的反应来研究的话,他们就会以为在插玻璃片时视觉皮层细胞的猛烈发放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也许是由不明原因引起的一种伪迹或噪声,那么一个重大的发现就会和他们擦肩而过,巨大成功的机会就会轻易溜走!后来休伯尔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这件事有时被当作“偶然性在科学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例子。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觉得我们的发现是事出偶然。如果要想有所发现,那么你就得花时间去发现,你就得对自己的研究方式不过于偏执,这样就不至于抗拒事先无法预料到的情形。另外有两个研究组之所以未能发现朝向选择性,只是因为他们太“科学”了:有一个研究组造了台只能产生水平光条的仪器,而另一个研究组则只能产生垂直光条,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比用动来动去的光点探测视网膜更有效。在科学研究的某个早期阶段,某种程度的马虎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关注的是电极推进器、密封小室和电极本身。我们很快就放弃用于视网膜定量工作用的眼底镜,而代之以猫可以用双眼直视的一块大幕布和一台幻灯机,我们也并没有对刺激的时程、运动速率或光强都一一定量化。我们给刺激或是撤刺激就用手放在幻灯机前面,也用手操纵幻灯机。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刺激的几何性质上,对此我们用卡片盒、剪刀和胶布来作系统的改变。当然也可以用电子学的或机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切,但是这样做无论从时间上来说,还是从经济上来说,代价都要高得多,并且还得牺牲掉灵活性。
为了确信他们的发现不是伪迹,休伯尔和维泽尔必须做进一步的实验。他们必须要能记录到更多这样的细胞,并且有不同的最优朝向。到了第二年的一月份,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他们确信真的发现了一种新现象,于是草拟了一篇摘要,准备投给1959年的国际生理学大会,当然这要先送给库夫勒审阅一下。第二天当休伯尔走进实验室的时候,维泽尔一脸懊丧地告诉他:“我想斯蒂芬不大喜欢我们的摘要。”很明显,库夫勒对这篇摘要并不满意,他在稿子上所加的评论和建议比正文还多!库夫勒喜欢文章简明扼要,最恨浮夸。在一开始的时候,写作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在经过11次修改以后,终于在1959年为《生理学杂志》( Journal of Physiology )所接受。杂志主编拉什顿(William Rushton)在接受函的开头写道:“祝贺您们写了一篇出色的论文”,并且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正是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奠定了他们日后荣获诺贝尔奖的基础。
简单细胞、复杂细胞和超复杂细胞
休伯尔和维泽尔把他们所发现的细胞称为“简单细胞”,这些细胞对线段的朝向十分敏感,不过为了使细胞有反应,这种有特定朝向的线段还必须落在其感受野的特定位置上。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另一类也对线段的朝向敏感的皮层细胞,和简单细胞不同的是,只要特定朝向的线段落在它的感受野里面,不管落在感受野内的哪个局部,它都会有反应。休伯尔和维泽尔把这种细胞称为“复杂细胞”。他们认为这些细胞的功能可能都是检测外界刺激的边界的朝向,也就是说,对象的轮廓线段的朝向。之后,他们又发现有些细胞还对线段的长度敏感——太长了不反应,太短了也不反应,这种细胞被称为“超复杂细胞”。他们的一系列工作表明,朝向敏感性是初级视皮层细胞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们的功能作用很可能是检测对象的边框。我们知道,图像的边框是最富含信息的地方。漫画家只要用寥寥数笔勾个轮廓就可以把人十分传神地画了出来。所以,检测轮廓对辨识物体的形状知觉是十分重要的。就这样,休伯尔和维泽尔为视知觉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形状知觉——提供了坚实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休伯尔和维泽尔根据他们的这些发现提出了一个猜想,认为视觉系统具有某种层次结构,对于神经元的感受野而言,越是远离视网膜的层次的神经元需要的刺激模式也越复杂。这种神经元对复杂刺激(比如说一张人脸)的反应,是基于把前面层次的神经元对构成这种复杂刺激的一些相对说来比较简单的特性组合起来产生的。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猜想有其合理性,但是这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现在已经知道脑中和视觉有关的脑区多达几十个,这些脑区并不是严格按照金字塔那样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也就说只有“低级层次”向“高一级层次”发出信息,并在那儿会聚起来;与此相反,在这些脑区之间有广泛的双向联结,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这里并没有一个“最后”的司令官决定一切。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猜想催生了我们在稍后要讲的对一些只对非常复杂的刺激起反应的神经元的发现。
神奇的视觉皮层功能柱
休伯尔和维泽尔发现,在初级视皮层有一块1毫米×1毫米的区域,其中所有神经细胞的感受野都集中在视觉空间的某个区域里,并且它们相邻细胞的最优朝向在0°—180°的范围内连续地作有规则的变化。有趣的是,在厚度为2毫米的垂直范围内,每个细胞的最优朝向都是一样的,他们称之为“朝向功能柱”。另外,初级视皮层里的细胞有的对来自左眼的刺激反应猛烈,有的则对来自右眼的刺激反应猛烈,它们各自靠近成群,并且在厚度为2毫米的垂直范围内每个细胞的主宰眼也完全一样。他们还发现,左眼主宰还是右眼主宰的细胞群也是交替排列的,组成了他们所谓的眼优势功能柱。
休伯尔和维泽尔发现初级视皮层的功能柱结构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没有发现初级视皮层中还有些细胞对朝向不敏感,而对光刺激的其他特性(例如光的波长)敏感。这可能是由于用传统的染色方法显示出来的初级视皮层的细胞结构显得相当均匀一致,人们也就容易想当然地认为其功能也就应该均匀一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休伯尔和利文斯顿(Margaret Livingstone)才发现在初级视皮层的功能柱中还有些小的斑块,其细胞对朝向不敏感,而对一定波长的光敏感。后来休伯尔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没有早一点发现这一点。尽管在他记录的大量细胞中,他确实也观察到有对朝向不敏感的。
诺奖桂冠的启迪
休伯尔和维泽尔的一系列工作为了解视觉信息处理的基本原理打下了基础,因此休伯尔和维泽尔荣获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科学研究中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错失良机的懊丧。从“起跑线”上来说,同休伯尔和维泽尔相比,荣格要遥遥领先得多,但是最后他没有作出多大有意义的发现,而被后来者远远超越。究其原因,他没有像休伯尔和维泽尔那样,先大致做一些预备实验以探索各种可能性,就一头扎进了一种方法。他未能及早领悟到,自己团队所用的刺激形式对视皮层细胞来说是无效的。尽管哈特兰曾经告诉过荣格,他曾经用在弥散光背景下移动小杆的方法寻找撤光神经元。荣格也对同事们建议过试试这种方法,但是大家都反对做这种一点也“没有系统性的、考虑不周密”的实验。大家认为还是建立一套复杂一些的仪器为好。后来荣格很懊丧地说:“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我对皮层神经元做了5年的研究,却错过了发现朝向特异性,我往往会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并且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不是去造那个定量化的机器,而是用一根棒以各种朝向动来动去,我们有可能在一个实验中就作出了这样的发现。”他总结教训说:“在进入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在以某种特定的方法做大量的定量实验以前,应该先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定性的探索性试验做一些尝试,以便找出最富有成果的方法。”有人把这种策略称为“有限马虎观点”。
如前所述,休伯尔也是持此种观点的,并身体力行赢得了诺贝尔奖。休伯尔在他的自传中总结说:
我们从事的科学研究看上去不大像在中学里学到的那种科学:科学就是一些定律、假设、实验证实、推广,等等。我们感到我们就像15世纪的探险家那样,就像哥伦布扬帆往西只是为了发现他有可能发现些什么。如果说我们有什么“假设”的话,那也只是有关脑特别是皮层的一种质朴的想法:有着种种有序复杂性的脑接收到输入的信息必须作出某些在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处理,其输出一定要比输入更精巧。因此,我们记录细胞是要看我们能够发现些什么。我猜想科学中的许多领域,尤其是生物科学领域,基本上就是在这种意义下进行探索。那些认为“科学就是测量”的人应该看看达尔文的著作里面有没有什么数字或者方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