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勤政善政的完美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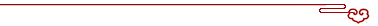
为官廉洁就有了当全职文官的资格,是庸官还是能官,就看“能”得是不是地方。有人推崇廉能之官,笔者不敢苟同。能官不一定能善政,对百姓还可能是祸害,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如北宋两位知名的能官:一位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范仲淹《岳阳楼记》提到的滕子京;一位是被包拯七次弹劾、“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好友王逵。他们都是历史上有记载的“能官”。
滕宗谅,字子京,与范仲淹是同科进士,“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与推行者,范仲淹十分赏识他的能。庆历三年(1043)因为“费(挪用)公使钱16万贯”,用以“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受到弹劾,御史中丞王拱辰“论奏不已”,宰相杜衍也主张严查。范仲淹相信滕子京不是腐败分子,“力救之”。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滕子京只要接受调查,便可分清是非黑白。况且还有范仲淹“横身遮护”,还怕什么。但是,他挪用16万贯公使钱确属事实。虽然他没有把这16万贯占为私有,只用在“犒赉诸部属羌”“馈遗游士故人”,也已触法违规。听闻被査,他“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为了不牵连朋友,将冒领公使钱所作用途的账簿烧掉,其毁灭证据的行为就是罪上加罪、错上加错,受到惩处,也是必然。
御史中丞王拱辰他们将滕子京当活靶,矛头指向的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的实施触动了上层贵族的既得利益,有错纵复杂的原因在其中。而滕子京等(还有苏舜钦的“监守自盗”“招妓饮宴”“对周公孔子不敬”)自律不严,行为不检,给人抓住把柄,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也实在是难辞其咎。
《宋史·滕宗谅传》说:滕子京为人“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无论是出于性格还是出于品格,也不能拿国家的钱去“好施与”。北宋对官员公使钱的使用有严格规定,逾越了规定就是犯罪。用自己的钱去“尚气”“施与”,如何“倜傥自任”都没有问题,但用老百姓的钱去“尚气”就不可以了,虽然他“及卒,无余财”,却也不能说是廉官,滕子京虽能而不足为范。
包拯七次弹劾的王逵,也是一位能官。他出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行事任性,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州县稍不徇从,即被捃拾,吏民无告,实可嗟悯”(包拯《弹王逵一》)。王逵在任荆湖南路转运使的时候就横施暴政,老百姓被迫上山逃避,揭竿对抗,造成国家的不稳定。
包拯再次弹劾,朝廷仍置之不理,反将该路提点刑狱调知泸州,让王逵临时兼管本路提刑司,使王逵更为嚣张。他怀疑是洪州知州卞咸吿发,将卞咸逮捕下狱,上下株连五六百人。包拯三次弹劾:“若命酷吏为之职司,而令一路之民独受其患。是一夫之幸,而一路(相当于一个省)之不幸也,窃恐伤陛下爱民恤物之心……以王逵所在残暴,猥滥之状,彰灼如是,而上下蒙蔽,曲加擢用,亦何以示惩戒于后哉……”
为什么包拯一而再再而三地弹劾王逵,朝廷仍然多方维护,不予惩办?因为王逵把横征暴敛所得的钱财,都送给了皇上和宰相首辅,以求进一步扬名显身。王逵的好友、时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与王逵交情很好。他说王逵“为人志意广博,好智谋奇计,欲以功名自显,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远近皆震。然当是时,天下久平,世方谨绳墨蹈规矩,故其才不得尽见于事,而以其故,亦多龃龉,至老益穷”。
曾巩不愧是个文章高手,把横征暴敛的王逵粉饰成了一个奇才。王逵为了功名自显,威令大行,远近皆震,把用残暴手段搜括来的民脂民膏,送给仁宗皇帝做私房钱,更多的是贿赂了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以求庇护与擢升。王逵自恃有皇帝和宰相的庇荫,希望借暴政而自显,没想到碰上了一位铁面无私的包拯,七次弹劾把他拉下了马。曾巩说王逵至老益穷,应是事实,因为他把搜括来的钱财都做了贿资,没有给自己留下。如果他没遇上包拯,自显之后何愁不肥。虽“至老益穷”,也不可能是个廉官。
廉、能、贪、腐、恶,是许多能官的宦途轨迹,初出仕时廉洁而有所作为,走得远了便出轨翻车了,滕子京错不及王逵,但走下去也会变成王逵。千余年来,这些能官的忏悔录累叠起来比《四库全书》还要厚,成为一篇篇奇文。为官者一旦以权谋私,以权谋利,失去了廉洁自律,其能便成为祸水,成为凶焰,百姓便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自古华山一条路,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一旦紫带横腰,想的就是扬名显身,光宗耀祖。为什么范仲淹对滕子京违规“力保之”,对滕子京的错误“横身遮护”?为什么曾巩对王逵的酷政多方粉饰、开脱?因为即使如范仲淹这样的政治家,如曾巩这样的文学家都认为,当了官“尚气”“自显”是天经地义的事,甚至横征暴敛、蠹耗下民、违法乱纪也可以宽免。在官官相护的人治社会中,给百姓造成的无穷人祸更甚于天灾。
包拯有两位前辈知州。一位是冯拯,字道济,太宗时状元及第,淳化元年或二年(990或991)任端州知州;一位是陈尧叟,字唐夫,端拱二年(989)状元及第,《肇庆府志》记载他在至道年间(995—997)知端州,宋史只记他被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两位状元任知州的时候,包拯还没有出生。
冯拯是个能官,他在端州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岭南封建化进程的政策,实施“括丁法”,试图将岭南诸路隐藏在土著豪强底下的农奴清查出来,变为国家户籍管辖下的人丁。这一措施如果见效,不仅可以增加国家赋税,而且保证了宋太宗于淳化元年(990)八月颁布的“禁岭南杀人祀鬼”等法令得以实施。冯拯的施政方略,被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治理岭南的圭臬。
可惜的是,“括丁法”没能够让土著豪强顺从归化,农奴也没能变为国家户籍管辖下的人丁。还是要“备峒寇”,组织军队上山镇压。这迫使土著豪强把埋在地下的铜鼓挖出来,聚众对抗。从太宗朝到仁宗朝,“岭南杀人祀鬼”等法令还是累禁不了。农奴制度的残余,还是顽固地不能向封建化转变。“括丁法”在强势地实施之下,也没见有大的、更说不上有彻底改变的成效。
陈尧叟也是一位能官,至道二年(996)在端州始筑基围,让西江北支淤成旱峡和耕地,其是有作为的。朝廷号召各州种桑枣,陈尧叟上书朝廷,说端州多山地,不宜种桑,唯种苧麻,也很实事求是。值得一说的是,端州山林瘴气,瘟病流行不绝。陈尧叟懂医理,编有《集验方》,他将《集验方》刻石竖于桂州驿,让百姓择方治病,也是一番好意。能官陈尧叟没有想到,能看得懂他的《集验方》的人,一般都不会用他的验方,有病找个郎中大夫看看,因病开方,按方施治,病就治好了。看不懂《集验方》的是大多数老百姓。即使看得懂,用哪一个验方,他们也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个验方能治好自己的病。陈尧叟的好意也就大打折扣。
古今的全职文官大都是我禁止你,我命令你,我指示你,我要求你……权有多大,位有多高,礼不下庶人,总要体现有权在握的强势,颐指气使地对待弱者(老百姓)。40多年后知端州的包拯,却能够向弱者示弱,与百姓情怀相通,从“下民”中汲取智慧,研究“下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最向往的是什么,形成自己的施政思维,实施他为民谋福祉的善政。下下人有上上智,借民智而施善政,目标是“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包拯做了与二位先辈同样的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包拯在与水疍山瑶的接触之中,懂得了用瑶药与中药结合治好瘟疫。他没有将药方竖碑刻石于驿站,而是按照从民间收集到的办法而用之于民,将药一一配齐,支起大铁锅把药煮好,请患病者来喝。他没有显摆知州的强势,而善用弱者的智慧去为弱者服务。这是他与前辈能官陈尧叟的区别。
治理端州的历任知州,上任的第一件大事是“备峒寇”,训练军队随时清剿镇压北岭山上的瑶民。包拯却认为,瑶民、汉人都是大宋的子民,应该平等对待,一视同仁。他让军队收起刀枪,扛起犁锄,排沥垦荒,扩大耕地面积。他减免赋税,吸引山上的土著豪强(渠帅)下山置地,成为佃主,洞丁(农奴)随之下山,为佃主耕作,成为佃农。包拯没有施行冯拯的“括丁法”,却让“水疍山猺(瑶),熟化奔走”,趋庭向化,真正结束了农奴制度的残余,顺利实现了农奴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化。
对比得出结论:廉政、勤政、善政是做一个全职文官的三重境界。
一个州一级的行政长官,率领群众挖几口水井,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为什么被后人誉为“神明之政”?他神在哪儿?明在哪儿?端州后有沥水,前临西江,水源丰足,为什么要挖井取水?为这挖井一事,包拯做过田野调查,进民户访问,踏破铁鞋,费尽心力,这是勤政。只有勤政才能走近百姓,发现问题。勤政是实施善政的基础。
包拯发现,端州疫情的反复是因为水源被污染了。西江河水滔滔东下,江湾的水却十分平缓。居民到江湾取水使用,用完的污水又倒回到江湾去,循环反复,致使疫病难除。他还发现,端州居民有蒸水的习惯,在饭将熟时,以砵盛水放进饭锅里蒸,水未滚沸就饮用,容易受到感染。他还了解到,州署用水,都是派船到羚羊峡江心取水,远离了污染源,因此少患疾病。而居民是不可能天天到江心去取水的。
包拯知端州三年,做了许多事情,如排沥垦荒、开办书院、修建驿站、只征贡数……但史籍志书的记录都很简括,唯凿井一事,记录甚繁。最早有元末明初郡人董源的《义井记》,继之有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袁枚的《子不语》、李调元的《南越笔记》、宋起风的《稗说》、张渠的《粤东闻见录》、范端昂的《粤中见闻》、檀萃的《楚庭稗珠录》、许奉恩的《里乘》,而至当代中山大学赵仲邑教授的《精庐小札》等。
包公七井,为端州居民“万灶所需,食之无疾”(当时端州也仅万余户)。从元、明、清至民国,那么多学者专家都说包拯凿井的事,就是因为包拯的善政。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肇庆七井》中说:“孝肃此举,端之人至今受福。大矣哉!君子为政,能养斯民于千载,用之不穷。不过一井之为功,亦何所惮而不为乎?《易》曰,君子以劳民劝相,言凿井之不可缓也。”
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万个弱者的脑袋,还顶不了一个八品州官的脑袋么?人没有生来蠢,只有当官蠢,因为一旦当了官,就进了衙门,一进了衙门就听不到民声,这是当官的最不喜欢听的大实话,也就成为变蠢的第一原因。
集民意而思政,集民智以善政,对当一个全职文官来说是真理,也是一句大实话。焦裕禄种泡桐,不是他聪明,而是他了解兰考人的愿望,集中兰考人的智慧而施行的善政。焦裕禄的善政是实现于人民政府要求全职文官要“为人民服务”的今天。而一千多年前的包拯能夙夜在公,勤政善政,在历朝历代的清官谱中,也是凤毛麟角,难能可贵。“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苏轼文集》),在贪污贿赂之风盛行于朝野的北宋,能够廉政勤政善政,殊为可贵。历史小说家二月河说,北宋的高薪养廉只养出一个包拯。这是对历史发出的感慨。
包拯在端州风景最优美、环境最清幽的宝月台建起了星岩书院,这是西江流域创建的第一座官办民助的书院。在当时,端州的经济环境有了改变,但还不是很宽裕。据专家考证,为了让端州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书院建起来,包拯捐出了他的公使钱,还捐出了一年的薪俸。因为他明白,要彻底改变端州的落后面貌,重塑一个新的端州,就必须兴文办学,让端州的年轻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管理地方的能力。
星岩书院的创建,引发了端州办学兴教的热潮,绵延至明、清、民国,成为西江书院文化的渊源之地。包拯的兴文办学,影响了端州一千多年。北宋元丰元年(1078),端州知州王洎将星岩书院改建为西石头庵;清咸丰五年(1855)为祀包拯,肇庆知府郭汝诚改建为龙图书院;清同治元年(1862)肇罗道蔡燮恢复为星岩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星岩书院归并端溪书院,改为肇庆府中学堂。至1950年成为高要县第一中学,1953年成为肇庆市第一中学。一千年来直到今天,端州宝月台成为一个文化区,星岩书院遗址建起了汉谋图书馆、端州图书馆、端州文化馆……一个善政的举措不仅影响一朝一代,而且影响了一千多年。时移世易,到了今天,重建星岩书院的呼声愈来愈高,这不仅是一座历史建筑的重建,更是端州人对包拯善政的敬仰和怀念。
廉能之官用的是权,廉政、勤政、善政之官用的是心。作为全职文官,只有勤政、善政,才能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向往什么,用权是绝对不可以的。只有用心,心相通了,权才能做到为民所谋,为民所用。最懂得感恩的是老百姓,政声人去后,民意笑谈中。人们千年说包拯,唱包拯,敬仰包拯,不是因为包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他做了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当全职文官,只想着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想尚气,想自显,都不可能芳名永垂。
且不说包拯一千年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受到敬仰,戏剧、曲艺、说唱、评弹历演不衰。单说一个小小的端州,就流传着许多故事、传奇。直到如今,我们在百姓的居所屋村,还能看到“包大人之神位”,这是包拯永远活在百姓心中的标志,也是人民对廉政、勤政、善政之官的祈求。引诗曰:
三年善政千秋誉,
直道清心百代师。
政声难得人去后,
万户千家说传奇。
(作者为肇庆名城与旅游发展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