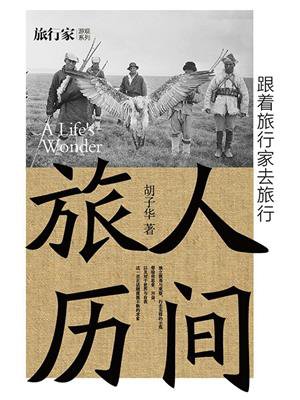冷战下的美苏漫游

John Ernst Steinbeck
约翰·斯坦贝克
约翰·斯坦贝克(John Ernst Steinbeck,1902-1968),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获得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愤怒的葡萄》是其主要代表作。冷战时期,斯坦贝克曾和著名摄影师卡帕前往苏联旅行,此行形成的图文信息成为了美国了解苏联的一道窗口。

左起分别为斯坦贝克所著《愤怒的葡萄》、《俄罗斯纪行》和《科茨海之旅》。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有股冲动想要到其他的地方去,当时成熟的大人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成长会让这股冲动平息下来。等岁月说明我已经长大成人时,大家又说治疗这种冲动的药方叫中年。现在我已经58岁了,但是什么都没用。船笛发出的巨响、喷射机的声音、引擎的预热声,甚至鞋子踩在路上的踢踏声,都能撩起我这种久远的冲动。”
早在20岁时,斯坦贝克就想像杰克·伦敦那样穿越太平洋,后因为经济原因未能实现。1940年,因《愤怒的葡萄》带来的声名之累,他逃去科茨海远行和探险。1947年,冷战的铁幕日益合围,为了了解苏联的真实面貌,斯坦贝克和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一同前往莫斯科,再转斯大林格勒,从乌克兰田园走到格鲁吉亚海滨,并写下了《俄罗斯纪行》一书。1960年,已几近年迈的斯坦贝克,一个人带着一条狗横跨美国,行程一万多英里、跨越了三十四个州,其后出版游记《横跨美国》。
正如传记作者杰克逊·本森(Benson)所说的那样:“斯坦贝克本质上是一个记者——他喜欢旅行。”而在他一生的旅行中,冷战时期的苏联之行和美国横跨旅程是浓墨重彩的两个篇章,交相呼应又呈现出不一样的帝国景象。
苏联:永远出乎意料的旅程
在赫尔辛基机场,当跑道上一架老旧的、触地时尾轮爆开的C-47俄国飞机,像蚱蜢那样弹跳着进入斯坦贝克的视野时,这趟苏联之旅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上面下来一批刚从俄罗斯拍卖会上回来的美国皮货采购商,他们全都显得神色萎靡,声称这架飞机一路上几乎从未超过地面一百公尺,而它将载着斯坦贝克和随同摄影师卡帕飞往斯大林格勒。
事实上,在之后的整个苏联旅程中,所有的飞机航程都让他们吃惊,机上没有安全带,乘客得自带食物,而且飞机起飞的时间,始终叫他们拿捏不准,因为它们就像滴溜溜转的骰子,起飞前永远不可能知道那是个什么数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必须在飞机起飞前很久就赶到机场候着。“不管你是在什么时节旅行,必定得在天亮前冒着凄寒夜色赶抵机场,喝上好几小时的茶,等候飞机起飞。”
从莫斯科去第比利斯,一架本该在20分钟内起飞的飞机却停了两个多钟头,只是因为机员突然想搭车去海边游泳。而从格鲁吉亚返回莫斯科,一开始被告知为他们准备的专机将在一个小时后起飞,之后加了35分钟,接下来是再多45分钟,再去打听,指挥官说,有个土耳其政府代表团要前往莫斯科参加建城八百周年庆典,如果斯坦贝克准许的话,他们要共乘专机。
“我们很大方地答应:‘让他们登机跟我们一起去。’可是有个小问题:他们还没到。他们还在第比利斯,大约半个钟头后才会出门。我们再回到餐厅,再喝两杯茶,再吃大饼干。朝阳已升,天气转热,俄罗斯巡逻机起起落落。疲惫袭人,困倦难当。快到一个钟头时,我们再去找指挥官,土耳其人在哪里? 唔,他们搭的火车还没到第比利斯,大概是在沿线某个地方耽误了,指挥官建议我们再等半个钟头。”终于在两个半小时之后,土耳其人的行李送到,但还不见人,因为土耳其人搭了一夜的火车,觉得有点风尘仆仆,于是决定先到旅馆洗个澡,吃些早点,略事休息。于是再等,终于等到土耳其人到了以后,他们却反过来不让斯坦贝克他们登机。只得再协商、争吵,最后才勉强挤上飞机飞到了莫斯科。
经此一事,“我们已知道且已臻于人类器官能忍受的最大程度。”而事实上,在苏联此类考验耐性的事件并不在少数。在餐厅用餐,单是上菜就得花两个半小时,这让他们觉得惊愕的事情,在俄罗斯餐厅却属稀松平常。因为在苏联,“所有东西和每一笔交易都在国家或国家批准的专卖控制下,统计系统极为复杂。因此,侍者问客人点菜后会很仔细地写在本子上,之后不是去要求食物,而是去找统计,统计将所点食物再做登记,然后才发张便条给厨房。到这里还得再次登记,要求才算完成。好不容易发出食物,所发食物也得记在便条上交给侍者,侍者拿着便条到统计那儿,登记所要求的某某食物已发出,再发便条给侍者,侍者拿便条回厨房领食物送到餐桌,这时他本子上已登记着要求哪道菜、哪道已进厨房、哪道终于送到餐桌上。这个统计过程相当花时间,甚至比料理食物所花时间还要多出许多,你再怎么对餐点迟迟未到表示不耐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是没办法的事。这是必要过程。”
在苏联旅行,车子永远不能从基辅直接开到斯大林格勒,或从斯大林格勒开到斯大林诺,尽管它们隔得很近也不行,每回都必须先折返莫斯科再出发。而且苏联司机开车的方式也很独特。苏联是个庞大的统计系统,司机得根据所行驶的距离配发汽油,所以必须利用各种可能的技巧,让配油能跑满这一程。为节省汽油,他们会在车子全速开一阵子后再利用山丘地形放空档,让车子滑行。“在我们看来,这种做法令人相当紧张。以六十英里时速奔驰的车子,陡然间松开离合器,任车子滑行到踽踽而行,再猛然加到时速六十英里,然后放空滑行,如此周而复始。”
美国:一座荒原的雏形
1960年,斯坦贝克带着一条狗踏上了横跨美国的旅程。记录这次旅程的游记《横跨美国》在Lonely Planet系列《美国》一书中被列为是最有代表性的美国游记之一。然而它本身对热衷于游玩的读者而言,却并不会有多大的助益,因为在斯坦贝克的行程路线中刻意避开了景点和常规路线。黄石公园是他行程中少数几个景点之一。然而,即使是去那里,他也几乎是进去不多一会儿就开车出来了,因为他的狗看到熊变得很狂暴。事后,他对黄石公园很满意,也只是因为黄石公园的熊让他见识了他的狗居然有好勇斗狠的一面。
事实上,斯坦贝克进行这次旅行是想了解当时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我打算去了解自己的国家。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国家的情趣、味道与声音了。真正体会到这些感觉,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要一个人旅行,取道南部的公路往西走……从这趟行程中得到我亟需的收获——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语言、观点、看法以及改变。”所以相比名胜,斯坦贝克选择目的地时有着自己奇怪的逻辑。比如他去北达科塔州的法戈(Fargo),是因为它在美国地图中的位置。把美国地图东西向从正中间对折时,他发现法戈就落在地图中间的折线上。而在横跨两页的地图册中,法戈往往会失落在装订线上。于是他决定去那里看看。仅此而已。

斯坦贝克横跨美国旅行的野营车。
“大家对我的名字已经很熟悉,我的亲身经验告诉我,人一旦知道了你的名字,不论他们喜不喜欢你,不论是害羞或是其他在公开场合所显露的态度,反正他们的表现跟平时不一样。”因此,在这趟旅行中,为了了解到人们真实的状态,他不到饭店登记住宿、不跟认识的人见面、不访问其他人。于是,他定制了一辆三吨半的客货两用车,装了一个车顶房:一间小屋子,里面有双人床、四嘴炉、暖气、冰箱、储藏室、防蚊虫的纱窗,使他能够像把房子背在背上的随性乌龟一样自给自足。
旅途中他接触了很多活动房屋的居住者、像远洋水手一样的卡车司机一族、每年定期穿过边境到缅因州劳动的加拿大雇农队伍等特殊人群。他会在一个刚退房未及整理的房间里翻垃圾偷窥并想象房客的秘密。他溜进当地的酒馆与教堂,不动声色地偷听当地人的谈话内容。他研究地图但不喜欢地图。“地图毕竟不是真实的情况——它们也可能是专制的君主。我认识一些非常热衷地图的人,这些人可以路过乡间却视而不见,还有一些人就像是身在囚车中,完全依循地图所示找路。”为此他还经常迷路,但对他而言,迷路是吸引注意力、得到协助以及进行对话的最好方式。
这趟旅行虽然目的严肃,但斯坦贝克保持了最大的随性。或许正如他所言:“每趟旅行、冒险或探险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所有的计划、安全措施、方法以及强迫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不是我们在主导旅行,而是旅行在带领我们。导游、旅游行程、订位都会毫无转圜又无法避免地彻底消弭旅行的个性。只有认出这些道理,才能放松,并顺其自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旅行就像婚姻:如果想控制,那么一定会出错。”
然而,这么一趟漫长的旅程下来,结果是令人沮丧甚至疲惫的。他发现的是美国的一个荒原雏形:“我看到的是一种病态,一种浪费的疾病。大家都有欲望,却没有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建立起来的力量都像是存在尸体里的瓦斯。我不敢想象一旦瓦斯爆炸,会有什么结果。我一直觉得我们缺乏令人强壮的压力以及让人伟大的痛苦。现在,压力是负债,欲望是为了更多的物质玩意儿,痛苦是无聊。加上了时间的酝酿,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满之地。”
当印第安村落把一个地方弄得太脏乱时,他们就会舍弃并迅速迁居。可我们呢?
我们无路可退,他说。
无处不在的“俄罗斯人”
1946年,丘吉尔宣称东欧各地已经垂下铁幕。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敌意,并迅速弥漫各处,长出很多变形。在美国旅行时,斯坦贝克曾与人进行过一次有意思的对话,事关为什么大家天天拿俄国人出气。
“这里有人认识俄国人吗?”
“当然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有用。就算你口沫横飞地数落俄国人,也没有人说得出你的错处,所以我们把俄国人当作其他事情的出气筒。嗨,我还记得大家把所有事情都算在罗斯福先生头上的那个时代。安迪·拉森有一次因为他的母鸡得了哮喘,而脸红脖子粗地在那儿骂罗斯福。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那些俄国人身上背的包袱真重。有人跟老婆吵架,也算到俄国人头上。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俄国人。我敢打赌,即使在俄国,他们也需要俄国人。也许他们把他们的俄国人称为美国人。”
1947年,斯坦贝克决定去苏联旅行,原因也不外如是。那时冷战刚开始,报纸上有关俄国的消息每天不下数千言。斯大林的想法、俄国参谋总部的计划、军队素质、原子武器和导弹实验等,全都是由不在当地的人所写,他们的资料来源绝不是无可非议。于是,他想去苏联看看那里的人穿什么?餐厅中上的是什么菜?有什么食物?他们怎么做爱,怎么处理死亡?他们谈什么?他们也跳舞、唱歌和演戏吗?小孩子是否要上学?
临行前,各式各样的忠告、告诫和警告纷至沓来,值得一提的是,大半来自不曾到过那儿的人。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该带食物去,否则准会饿死。“我们发现,好几千人都患了莫斯科病,也就进入了听信荒诞意见和拒绝一切事实的状态。当然,我们也发现俄国人同样也患了华盛顿病。我们发现,在我们丑化俄国人之际,俄国人也在丑化我们。”在苏联的一次小丑表演上,他们的小丑一律自称是美国人,观众甚至等着看斯坦贝克他们是否会被这调侃惹恼。事实上,美国的小丑也自称是俄国人。
或许正因如此,斯坦贝克不论是在《俄罗斯纪行》还是《横跨美国》中都一再强调:“我不敢说我已经掌握了真实,我只是如实记下我所看到的。”而这就是他在旅程中能做到的最真实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