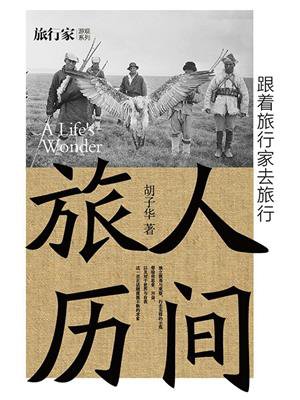怎样理解美洲大地

Alejo Carpentier
阿莱霍·卡彭铁尔
阿莱霍·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1904-1980),古巴著名小说家,也曾长期生活在巴黎,他将超现实主义与本土化相融合,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人物。他痴迷于旅行,回到拉美之后,曾逐个游遍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

卡彭铁尔关于美洲重要的小说作品有《消逝的足迹》、《光明世纪》等,呈现了

熟悉拉美小说的读者,可以如数家珍般报出以下名字: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略萨……,但多半不会记得卡彭铁尔,虽然他经常被视作“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更是20世纪美洲作家中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马尔克斯曾说:我们大家都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但事实证明,他们所写的不仅不是同一本,而且往往相互混淆。如果说马尔克斯写出了一个停止的美洲,一个带着腐殖气息的美洲,那么卡彭铁尔写出的恰恰是美洲的出生时刻。相比马尔克斯看到的内陆美洲,卡彭铁尔发现的则是一个从沿海到内陆充满形变、动荡和共生的美洲。
卡彭铁尔是那个时代少数痴迷于旅行的拉美作家,他甚至逐个游遍了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屿,这也锤炼了他“海洋美洲”的新视野。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视野将会为他赢得越来越重要的名声。
神奇还是现实?
卡彭铁尔的父亲是法国建筑师,母亲是俄国籍的大学语文教师,自小深受欧洲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之后,因为反对马查多的独裁统治,他逃往法国,在巴黎一住十年,并与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作家过从甚密。毋宁说,身处法国和古巴之间,卡彭铁尔需要反复地确认自己的位置,而美洲之旅正是这样一次摆正。
1947年,卡彭铁尔乘坐一架用于地理测绘的飞机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交界处的奥利诺克流域上空飞行——在当时,这是任何商业航行都不会途经的地带——那片土地上的壮美景象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震撼:森林掩映下,240条金色的河流围绕着一片海拔1200米的高原,高原四周是无法攀登的孤绝峭壁,上面耸立着三块世界上最古老的岩石,它们形同从天上抛下来的几何教具,歪歪斜斜地插在土地上,每块高达3000米,恍若史前时代的巨物。
为了实地体验这种风光,卡彭铁尔来到了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市,在那里苦苦等待一艘拉纤船,这艘船将带他沿着奥利诺克河溯流而上,进入他迷恋已久的原始地区。当时的拉美就和前些年的中国一样,陷于一种不无狂热的造城冲动。玻利瓦尔就是这样一座不断被扩建的现代城市,但这种扩建相当艰难。为了使城区向外延伸,当地居民不得不长期同沼泽、黄热病、各种各样的昆虫,以及地下庞大的植物根系抗争。只要稍有懈怠,那些顽强的地下根系就会从四处弓起背脊,摧垮墙壁,毁坏建筑。偶尔,从这座大楼林立的城市周边还会跑来一头阔步漫游的老虎,为此惊慌的新市民们不得不临时组织起闹哄哄的、不无滑稽的围猎,手忙脚乱地把它打死在中心广场。
卡彭铁尔足足等了8天,约定的船才姗姗抵达玻利瓦尔。这是一艘平底船,只有一个小马达,来玻利瓦尔是为了往上游牧场运送牲畜。挤满了各种瘤牛和猪群后,这艘小船上几乎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晚上,卡彭铁尔只能把吊床悬在牲畜的上方,然后伴着各种叫声、各种屎尿臭入睡。
卡彭铁尔沿途在欣赏两岸风光时,会不停比对洪堡在一百多年前描写的美洲景象,他发现书中所写与自己看到的许多情况极为相似。那些河边的小村镇和外界几乎没什么往来,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电报。一路溯流而上,戴着羽毛和鹰嘴的印第安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卡彭铁尔的视野,不过衣服越穿越少,直至完全赤身裸体。沿岸看到的一切也慢慢脱离了现当代历史,似乎因为征服新大陆的是中世纪的人,这里的生活节奏、航行方式、灯盏和灶具,马和狗的重要性等,也全处于一种中世纪的形态。
尽管沿岸的居民是很好的木匠、猎人和渔夫,知道怎样取火,且善于制造陶器,但自然仍显得严酷。在航行过程中,卡彭铁尔也为此吃尽了苦头。“最让我惊讶不已的还是原始森林中那无穷无尽的拟态变化。在这儿,一切全都似是而非,完全是由一个假象把真实掩盖了起来的世界,而真实却往往令人起疑。一动不动地张着嘴巴躲在沼泽底下等待猎物的鳄鱼,看起来倒像是一截爬满木蜂的朽木。藤条像蛇,而蛇呢,倒更像是爬藤;水草密结如毡,遮没了下面的流水,仿佛是生长在陆地之上。森林是一个虚假、险恶、披着迷彩的世界,那里的一切全都是伪装、计谋,假象、拟态。”到后来,对卡彭铁尔而言,出发前的对原始森林的期待已经变成了恐惧,尽管这恐惧也带着新奇。
文明还是野蛮?
从小的欧洲式教育,加上在巴黎长达十年的居住和生活,卡彭铁尔与布勒东、阿拉贡和艾吕雅等超现实主义作家过从甚密,对欧洲文学那30年时兴的各种挖空心思臆造神奇的手法早已十分熟悉:迷恋黑森林魔法师、幽灵和变狼狂;或流连于集市上的杂耍和畸形人;或者干脆变戏法般把一些不相干的东西聚合在一起等。重新回到拉美之后,他发现在这片土地上,神奇不需要臆造,神奇就是现实本身。
在奥利诺克之旅结束后,卡彭铁尔据此完成了《消逝的足迹》,小说描写一位西方音乐家深入南美洲去搜寻原始乐器,却爱上了一位印第安姑娘,并借由淳朴的原始生活反思了西方发达文明的罪恶。整部小说无论从主题到趣味,都像是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一个跨时代翻版,作为旅行的产物,它在法国获得最佳外国小说奖似乎也重现了《阿达拉》当时在西方所受的追捧。
夏多布里昂被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旅行作家。1791年,他到美洲旅行,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阿达拉》的完成。《阿达拉》在凄美的爱情中所展示出的那个未受文明污染的、天真且道德完备的美洲世界,让不少西方读者印象深刻。长远来看,《阿达拉》的重要性无异于一次文化上的“美洲大发现”,夏多布里昂借此成功地把美洲的地理坐标楔入了“完美野蛮人”这样一个乌托邦的模糊概念——在此之前,这个乌托邦只是“远方”的模糊代名词。自此,这个顽固的欧洲文化幽灵就一直盘桓在美洲大地上,经久不去。

美洲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状态: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摄/陈桢)
夏多布里昂一生有两次重要的旅行,他把1791年的美洲之行视作对原始自然的考察,把1806年的东方之行(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看成是一次人文世界的巡礼,这种粗糙且粗暴的对位法代表了当时欧洲主流的地理认知观念。“美洲人身上的一切揭示了他们是还未达到文明状态的蒙昧人,而阿拉伯人的一切却显示他们是重返蒙昧状态的文明人。”夏多布里昂固有的欧洲中心主义使得他既看不上东方,而美洲呈现出来的自然与社会的混合状态也让他不无失望。他原本想借美洲之行写一部“关于自然人的史诗”,最终也因此未能如愿。
时隔一个多世纪,《消逝的足迹》却部分地践行了夏多布里昂写“自然人史诗”的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夏多布里昂的原始主义想象。卡彭铁尔笔下以罗莎里奥为代表的土著人不再显得愚昧、落后,相反,他们有一整套自己的文明,包括艺术、神话,甚至还有史诗。或许,对卡彭铁尔而言,其中不乏为拉丁美洲辩护的意味。但《消逝的足迹》作为一次委内瑞拉之行的产物,依然充满了异国风情的夸张笔调,它所展现的视角也完全是西方化、游客化的。因此,小说发表后,在委内瑞拉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它被认为是失去了拉丁美洲血脉的一本书。
西方的目光还是西方的革命?
异域风情和民族主义就像“文明与野蛮”主题下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异域风情的背后,任何一个美洲人都不可能忽视的事实是,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这片大地上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可在神奇与现实之间,卡彭铁尔发现了一个不时跳出来的找不准位置的自我。这种情形在马尔克斯身上也许更为明显。
对很多文学爱好者而言,《百年孤独》好比拉美地区一份最为成功的旅游讲解手册,而马尔克斯充当了一名同样出色的导游——通过扮演一位部落时代的遗老。在1982年的诺贝尔奖授奖辞中,马尔克斯——作为拉美地区的文化英雄,而非他本人——批评了欧洲人对这片土地的打扰和干预,但通过那一长串对拉美大地的外来观看和内部观看的列举,他显然懂得拉美的文化形象正是这两种目光交织的产物。在交通日益便利的时代,想象性的目光具有了越来越深刻的塑造力。正如今天,我们亲眼看着我们的乡镇被游客的想象塑造,房屋、道路、植被、言谈都可以变得十足的景观味。同样,在接近拉美文学大爆炸的零碎资料中,我意识到其中他们有一种急于向欧洲打开孔雀之尾的自得,以及由此带来的隐秘的羞耻心。
毋宁说,《百年孤独》的好在于它的聪明,它几乎集结了西方对拉美的全部想象,也抓住了拉美人阴郁的情绪,既显得异域风情,又不无民族主义,它是一块八面玲珑的意愿磁石。这块磁石,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愿意承认的,也是拉美独立战争后的独裁者愿意看到,并加以鼓励的。《百年孤独》就像是长城、金字塔那样的标志性景观,披着历史和文明的外衣,却不过是一层光滑的、打了蜡的现实表面,它既不展示这片土地的过去,也不展示这片土地的现在和未来,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地区理解的简便法,而诺奖作品的身份使它接受起来更加心安理得。
但与马尔克斯的主动迎合不同,卡彭铁尔是一个反省者。在遍游加勒比海地区之后,卡彭铁尔写出了《光明世纪》,其中提供了一种观看美洲的新视野,不是马尔克斯似的内陆美洲,而是海洋美洲。它基于一个现实,即拉美不只有一成不变的原始森林,它还通过海路与西方一早建立了永恒的通道,因此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不一致的现实,它既承受着西方的侵略,也共享西方的革命,并因此充满形变、动荡和共生。
在《光明世纪》这部描写加勒比海地区大革命的作品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关于拉美加勒比海地区的风情描写,也充分感受到了“暴力”的存在、蔓延和恐怖。毋宁说,革命作为西方和拉美接触的第三种方式,恰恰是对异域风情和民族主义的一次新综合。“法国大革命”对美洲之所以重要,正在于作为世界革命,它既超越了美洲的民族主义,也赋予了美洲的主体身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欧洲而言,拉丁美洲始终只是个被创造物,是大航海时代的一次偶然发明,是一块可供“乌托邦”建设的空白纸张。在这片大陆上,“野蛮人”的历史和文明也只是作为不驯服的自然的一部分来处理。但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拉美独立战争正是对这种无主体状态的一次有力纠正,借用帕斯的说法是:“幸亏法国革命的原则,美洲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状态:不是过去,而是未来、梦想。”而《光明世纪》正是写出了拉美的这个出生时刻,一如《百年孤独》为拉丁美洲奏响了挽歌:整个布恩迪亚家族的灭绝和马孔多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