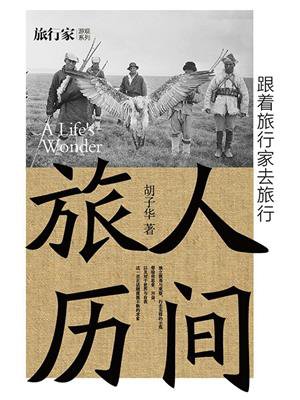失败的西非大地

Henry Graham Greene
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 1904-1991),英国小说家,有极强的宗教意识,向内挖掘灵魂的挣扎与救赎。但他在世界各地的旅行,则从外部给他的小说混合了侦探、间谍和心理等多种有趣的戏剧元素。

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有着鲜明的地域性,重要的小说作品有《权力与荣耀

“在非洲内陆地区,时间压根儿就不存在,最好的表在这种气候的侵蚀下也很快会坏掉。……我从玛莎商店买了六只手表带在身上,结果全部都用坏了。只有一只手表陪我一直熬到了海岸线,但很久以前就走走停停,记的也不是真实的时间。为此,我不得不在天黑时反复把手表调到六点半。坐在凯拉洪的卡车上,我仍想着可以按照时间表来计划行程。我本来计划从凯拉洪径直前往首都蒙罗维亚,大概两个星期内就可以到达。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四个星期后,我们还在一个从未听过的地方。”在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西非之旅中,时间的可测量和可记录都失效了。这也成了非洲时间的一种象征,它并不像进化论所预示的那样一个劲儿地朝着憧憬式的未来直奔而去,而是在西非不停地打转,形成一个难解的漩涡。
从这个漩涡中浮现出来的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面目:旅行者自我塑造的异国氛围如同打扮的一种节日气氛,恍如奈保尔笔下西非集市上那条色彩斑斓的棺材街,人们用光怪陆离来消解悲伤;摄影师们善于用戴轭的公牛和裸胸的孕妇来营造效果,并处理掉背景里大量的垃圾、嗡嗡飞掠的苍蝇,以及众多在那里闲荡,有着粗暴眼神的年轻人;新闻工作者在编辑的刺激下,热衷于从反面喂给大众地球上野蛮行为的证据:贫困、疾病、战争和死亡,在那里,记者不断面临如下的道德险境:沉迷于哗众取宠,从而忽略受害者的人性。换句话说,那些带着末日视角的记者们很难忠实地记录当地情景;还有纷涌而去的无数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去到那里时不时地落泪和悲叹,但于事无益;那里还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专家,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因为那里众多的问题成了热门的学术资源,而这甚至会模糊研究的目的性:为写出精彩的论文,还是为当地探索问题的解决之道?
格林喜欢冒险,他的旅迹遍布五大洲,旅行和创作在他身上有着严丝合缝的对照:墨西哥和《权力与荣耀》,西非和《问题的核心》,海地和《喜剧演员》,哈瓦那和《哈瓦那特派员》,越南和《沉静的美国人》等。奈保尔说,只有当你对一个地方有了足够的理解后,你才能把它写进一个故事里。西非作为格林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它的意义正如多年之后格林自己所声称的那样,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
自然:新时代的原始主义
20世纪30年代,海明威正在非洲东部的草原上四处追猎狮子、犀牛和羚羊,那里的自然是迷人的、享乐的,相比这种带着“男性印记”的动物愉悦,另一个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却在西非的密林里陷入了动物的恐慌,那里的自然是幽闭和恐怖的。
“老鼠会蜂拥而入每一个茅屋。它们在夜半时趴在我们头上吮吸头油。”路上从修女那里听来的近乎荒诞的告诫在格林的旅程中很快就成了严峻的现实。“我从未习惯过木床板上的老鼠,我甚至害怕飞蛾。这是遗传。我和我母亲一样,都很害怕飞禽,不敢触碰飞禽,更不敢把它们放在手心去感受那跳动的心脏……但在非洲你不碰到飞禽的几率就跟你碰到超自然现象般稀奇。你无法逃避它,它就匍匐在那墙上,从门里飞进来,在草地里穿梭,你没法回头,也无法忘记。”不仅如此,在这里,每天都要注射奎宁预防疟疾,所有的舷窗都要挂蚊帐:这些东西对于他们来说犹如桌布般自然。这是格林在来到西非之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那是1935年,英国的统治已经涉足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那时候来自帝国的旅行家们通常都充满自信,认定非洲人会尊敬英国人、帮助英国人,就连语言不通也会增添乐趣。而当他们回到英国,他们就可以在各种猎奇性的沙龙里趣味横生地谈论这趟旅行的惊险,并借此出书、成名。
事实证明,对原始的审美会极大地掩盖原始的不舒适。格林在西非的这一路不仅充满了血泪经验——千万不要赤脚踩在地板上,因为这样会在脚趾甲里染上潜蚤;千万不要把东西放到箱子外面,因为全都会被啃得精光,要么是蟑螂,要么是老鼠,它们无所不吃:衬衫,袜子、梳子、鞋带……同时在精神上也不断放大着与自然搏斗的记忆:“每当我疲惫不堪、身体每况愈下的时候,非洲都会以这种形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啃衣服的蟑螂、地上的老鼠、喉咙里的灰尘、脚趾里的潜蚤,还有身上纠缠不清的蚂蚁”。踏上非洲不过14天,格林就患上了热病,情绪变得很不耐烦:“现在我需要的只是药物、洗澡和冷饮等,而不是这片充满树林和枯叶的庞大森林。”在旅途的第十七天,他几乎快要放弃了:“我对这里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感到恼怒……这就像是一个噩梦。我已记不得自己为什么要来。”他在巴萨镇写的日记中甚至把这次旅行称为“愚蠢的旅行”。
隔着大半个世纪,另一位来到非洲的旅行家保罗·索鲁几乎是带着戏谑的语调在调侃格林这个“幸运的旅行家”:“他一生都备受呵护,自己也非常恐惧,而且身患狂躁抑郁症,他总是需要出租车等待着随时呼应,而如此内心烦躁的灵魂竟然也能完成这般挑战,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他是个地道的城市人,不喜欢运动,而喜欢独处,喜欢安宁。他的恐惧不仅为他自己,也为读者带来了更加栩栩如生的非洲体验。”与索鲁同时期在西非漫游的还有一位来自《大西洋》月刊的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他对格林的密林感受却有着更多的认同。格林笔下的西非森林,除了偶尔一瞥头顶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经常是一走就是七八个小时,非常的沉闷、乏味。行者必须时刻注视脚下,避开随时可以绊倒的树根和石头。遇到小溪,只能背着人过去,因为哪怕踩在最浅的水流里也非常危险,里面遍布几内亚蠕虫,它们会寻找你身上的任何伤口钻进去,在里面产卵。如果没有医生,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找到蠕虫的尾部,用火柴棒把它像棉线一样卷着拉出来,如果拉断了,脚就会溃烂。所以可想而知,这样的场景是多么乏味且悚然。格林在回顾这段密林旅程时说:“我想森林里应该也有一些美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眼睛早已经失去了审美的能力。最终连巨大的燕尾蝶也觉得毫无看头,与身上爬动的黑蚂蚁并无差异。”
对读者而言,这样的森林不再是生命力的勃发,而是生命力的消耗。我想海明威大概也会像保罗·索鲁那样嘲笑格林在大自然审美方面的无能。然而,卡普兰却认为保罗·索鲁在某种程度上也低估了密林对西非的切实影响,他在利比里亚曾反复经历了那些多得无法穿透的树木,在这片无法反射光线又没有地平线的森林里,人们对于前景的视觉会自动消失,混沌与不明大量增加,因此人们会一直担心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身处这样的环境,人更容易传播令人兴奋的谣言,最轻的针扎或撞击都会导致惊慌。我曾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看过一次非洲木雕艺术展,除了惊讶于木雕上极度放大的人的贫乏与动物性特征,再有就是面具上十分丰富而夸张的神情。卡普兰认为这些面具暗示着森林在地方性心理状态上的角色。而随着西方帝国力量席卷而来的所谓文明并没有改变这里的原始,相反,暴力借由毒品、酒精、武器而扩大,从而在这片土地上创造出新时代的原始主义,这比原先那种古老的、仪式化特色的原始文化更加致命。
2009年,奈保尔这个尤爱凑热闹的旅行家也来到了西非,他延续了格林的一些动物恐惧,它们成了疾病的一大传播源:“吃蝙蝠造成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因此,日暮时分阿比让天空中黑压压的蝙蝠不仅是非洲西部视觉艺术的一部分,而且还是等着扑向人间的一场可怕瘟疫。”在某种程度上,这何尝不也是卡普兰所说的“新时代的原始主义”。
人群:眼睛的愉悦与怜悯
对于格林而言,抛开动物恐慌的各种折磨,西非之旅同样充满愉悦。这种愉悦多半来自女人。旅途中,格林几乎是逮住一切机会观察并描述女人,使用的还是那种近乎透视的目光。在弗里敦,当一名年轻女子靠近他乘坐的汽车时,他窥见“她光裸的乳房很小,很结实,呈圆锥形;圆滑的大腿如猫咪一样柔软”。在塞拉利昂,他看到“一群妇女沿着火车涌上来,巨大的黑色乳头犹如箭靶的中心”。到达利比里亚及法属几内亚边境之时,他这样描述一名颇具当地原始形象的女子:“一块鲜艳的布围着她的臀部,阳光透过棕榈树洒在她黑色悬坠的乳房上”。在与利比里亚总统见面时,他念念不忘的是总统身边那位女秘书:“……她是我在利比里亚见过的最美的女人,我情不自禁地一直盯着她看。”身陷丛林时,他会根据村庄中的妇女来评价村庄。在他困厄之时,回忆达喀尔整洁的妓女给了他极大的安慰。这块土地对他而言,时而像是恐怖的原始地狱,时而又是不受束缚的伊甸园。
格林秉性中不乏浪荡子的气质,离开非洲之后,他到过越南,深深迷恋于胡志明市堤岸区内遍布的鸦片馆和妓院。他在《沉静的美国人》中对这些地方的细致描绘使得看过的游客对胡志明市总是充满了一种肉欲的想象,这甚至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他们在越南的一本便携式导游手册中写道:“格林,格林,格林!要知道,胡志明市可不是只有一个格林!要到哪一天,人们才不再提起格林?”
同样遭此待遇的还有巴西的哈瓦那,格林到达那里后,很快喜欢上了那里,认为那里是一个“任何恶癖都能被允许、任何行当都能生存的城市……花上一块二毛五,就能看到最下流的脱衣舞表演,还有最最黄色的电影。”坊间甚至传言,他生前曾写过一份清单,用密码记载了他嫖过的47个妓女和其中具体的细节。回到这次西非之旅,它无疑是开启了格林游记中的女人主题。保罗·索鲁认为他对非洲裸体妇女的反应,不仅是体现了格林观念上的解放,另一方面也暗含了格林受到的诱惑。或许,保罗·索鲁对这种愉悦也并不陌生,在非洲旅行结束之后,他一度也非常想重返非洲。“从非洲传出来的消息都是坏消息,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去那里。只不过我不是为了看那儿的惨状、纷争,也不是为了报纸上的屠杀和地震的报道,我只是想要重温身在非洲的愉悦。”
这种愉悦对于到过西非的游客而言多半是真实和熟悉的,那里的惨状似乎只属于在那里生活的人。格林追求愉悦,甚至不乏色情的成分,但他同时也直面那里的灰暗:“白人到来之后,当地人的生活几乎丝毫没有得到改观,他们仍然遭到热病困扰,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新的疾病,削弱了他们对旧病的抵抗力。他们仍然喝着污浊的水源,仍然遭受蠕虫的侵袭”。这就是他同时在遭遇的一种罪和怜悯。作为一个白人,他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种宗教,好用来衡量我的罪恶。”在他关于非洲的小说《问题的核心》中,他描述了一个滞留在西非的殖民地官员,因为怜悯而犯罪,又因为犯错而深化怜悯,并最终在这两种力量的撕扯中选择了自杀。事实证明,怜悯于事无补,而罪只如同怜悯下的一种酒精。“人就像一株枯萎的植物,你想要通过酒精让它恢复生机,它开始立刻张开花瓣振动了一下,但是一会儿酒精散发后马上又萎蔫了,变得比以往更加死寂。”毋宁说,对于格林而言,这次西非之旅的冒险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化的。
国家:一座大陆的抵制
格林在利比里亚旅行时,他反复遭遇了一种破旧以及怀旧的诱惑,“这里极度破旧不堪,全世界再也没有像这样的地方了,但是这种破旧不堪却非常诱人,仿佛这种诱惑力会暂时地弥补对失去的一种怀旧情感,塑造一个更为古老的舞台”。与这种场景的怀旧相比,在格林和巴克莱总统的一次交谈中,那位总统先生高谈阔论地向他描述了一种国家的未来,那是一个遍布道路、飞机、机动车等带来的繁荣景象。而总统自己就是这种光辉前景的幕后老板,不光媒体行业归入总统麾下,最重要的是,选票的打印和发行也归总统管控。1928年,金总统回利比里亚选举时,以六十万票的压倒性胜利打败福克纳先生,而总投票人数其实还不到一万五千票。所以,当格林把游人的面孔重新转向前方时,他对西方的文明失望了。
“自己的国家”在西非曾被当做一种希望提出来。在这个未来式的构想中,格林认为当地人通过它在污秽和贫困中已经形成一种爱国主义。这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格林也不得不意识到他们只是在模仿西方:“从始至终,这些带有美国混血的奴隶就独具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当利比里亚共和国成立时,他们颁布了《独立宣言》,带着美国白色光滑大理石般的外观。那年是1847年,但在宣言中写的却是18世纪,它属于美国,它的措辞都像是昂贵坟墓上的墓志铭。”
在模仿不久之后,西非大陆很快就因水土不服发展出了自己的抵制。因为在西非,国家并不是民族和地域上的自然发展,而是摈弃传统的临时拼凑物。它直接产生了非洲大陆上一大批暴力的僭主,比如在利比里亚,窦总统在1980年闯入前任的房间,挖出了他的肠子和右眼。他的后任强森又于1990年割掉了窦总统的耳朵,并将他的死刑过程拍成录影带四处售卖。历史学家达维森甚至认为“国家”是非洲人正在忍受的一个来自西方的痛苦的诅咒。它的效用就如同格林随身携带的那些银币:自从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传到了这里,人们便拒绝接受带有女王头像的钱币,因为他们认为既然女王已死,这些钱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这在格林的西非旅途中是深有体会的:“在弗里敦,这是一个英式首都。英国人一手打造了这个城市,像锡皮棚屋、阵亡将士纪念日海报,山头还有一些漂亮的平房,有大窗户和电风扇,服务相当完善。英国人在这里种下丑陋的文明之后就开始逃离,拼命地逃离。弗里敦所有丑陋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带来的:商店、教堂、政府办公楼,还有两家酒店。如果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如果这一切都只是英国殖民下一个虚构的闹剧,那么弗里敦会变得更加美好。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模仿白人的滑稽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这就像是大猩猩的茶会,玩笑总是完全倒向一方。有时候,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自己荒唐滑稽的行为,因此这种被羞辱的感觉非常强烈。”
在西非的一名美国外交官曾在一封信中坦言:“我们价值体系最大的威胁来自非洲。”卡普兰根据其在西非遭遇的一切,更加精确地指出:这里出现的迷思,要么太地方性,要么太普遍性,以至于无法维持国家性。为此,他声称这是一片失败的土地。这种失败既是国家的失败,同时也是西式文明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