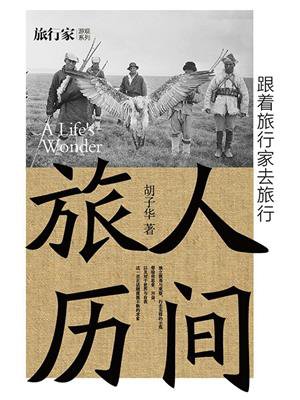自序

旅行为了结结实实的疲乏
关于旅行,在我们周边已经充斥着太多浪漫化的想象和致力于描述得更美的谎言。出于逆反,我惯于把游记当成一种辞藻的排泄物。这种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教育里的体裁偏见,当然也跟游记书写中常见的过度描绘和多愁情绪有关。
之后有两年多时间,我进入《旅行家》杂志当旅行记者,写游记就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没什么工作经验,甚至连旅行经验也少,只好重新捡起游记来读,而且是常规性地读,试图从中找些工作自助的方法。我从那些书里总结了不少的旅行警句,诸如旅行需要在场景中专注,用身体浸入式地去感受;关注当地的地理、资源、重要议题,以及来自外部的误解;观察者应当像变色龙,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等。每一条警句看上去都很正确,实践起来通常还是不得其门,经验无法速成,加上目的地快速切换,最终只好任由自己安于一种碰运气的旅行法。
关于旅行记者,一个有意思的吐槽是这样的:一旦进入套装流程之后,就像维吉尔引着但丁游历地狱,每一层地狱的看守者作出配合。在中国当下的媒体生态中,纸媒市场已经很难允许一个杂志记者还能像半个世纪前的旅行家那样长时间地、完全自主地“奢侈”漫游。事实上,直到我离开《旅行家》杂志,也很难说自己在哪一次旅行中真正理解了一个地方的真实,大多数时候留下的其实是一地的残影,隐约察觉到了重要之处,但总得不到廓清。
尽管如此,我对游记和旅行的兴趣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发觉越是在全球化驰掠席卷的今天,对地方性知识的实地勘察就越发显得重要。换言之,这本描述旅行家行纪的小书,正是对我早先那种轻浮的游记观念的一次有效纠偏,也是我关于游记和旅行的一次重新理解。书中每个人的旅行方式和旅行目的都千差万别,有人只身匹马,有人则沿途招募兵工,有人行李寥寥,有人几乎是带着移动的小型军火库在旅行。同样,吸引他们走向未知之地的“塞壬”歌声,也各有不同。有人旅行为了得到物质上的回报:黄金、文物、标本等;有人希望通过填补地图空白获取历史声望;有人上路为了放松,有人奔波为了研究,有人甚至是为国刺探情报的间谍。
与此相应,他们各自所秉持的旅行观也大相径庭,有时甚至是互相驳斥的,在阅读他们的过程中,我时而接受这一种,时而接受那一种,但整体而言,和他们一样,都认同旅行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自我教育。旅行作为另一种知识路径和教育方法,其实一直是一项古老的传统。泰戈尔一直把旅行当成一种更有效的学习,他生前梦想着建一所旅游学校,让学生们可以花五年的时间走遍整个幅员辽阔的印度,也真正去理解印度,并希望借此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知识。
对任何人而言,倾听一个新的声音都是困难的,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身份认同更是难上加难,而旅行提供的机会,通常比其他机会更为便利,也更为直接。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面对面交谈,从不一致的人和观点那里汲取活力,这种教育就如同不断往原先的自我中塞进新东西,使它变得越发宽广、结实。这一过程不会是舒舒服服的,它充满挤压和拒斥,而人必须克服惯性,才得以在忘我中建立自我。这也正如荣格所说: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在野外也只会遇见自我,而这瞎子的旅行就是白白浪费时间。
正因如此,阅读这些旅行家,更多地吸引我的并不是他们所及之地的风光,也不是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是他们旅行中所遭遇的困难、挫败,以及他们沿途不断被砥砺和修正所产生的身心疲乏。在旅行中,这种自我疲乏是可怕的,但一直得不到它,又是充满遗憾的,它就像一种苦酒,将在回味中不断变甜。我并不反感旅行中的印象收集者、攻略复制者,以及永远追求在别处的“灵魂派”,我也认同旅行完全可以是舒适、轻松和快活的,但对“作为日常生活的犒赏”的旅行,我始终不感兴趣,某种意义上,旅行更像是为了得到这种结结实实的疲乏。但这种疲乏无法通过苦行获得,而只能通过自我更新。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章,写于在《旅行家》杂志工作期间。首先应该招认的是,在众多出色的旅行家之中,之所以写了这些,而没有写另一些,并不是经过精心选择的结果,而是将它视为一个敞开的序列,不断得到增补。比如同样是在印度旅行,我写了马克·涂立而没有写奈保尔;同是在新疆探险,我写了普尔热瓦尔斯基而没有写斯文·赫定;同属人类学家,我写了马林诺夫斯基、格尔茨却漏过了列维·施特劳斯,这完全是出于偶然,而非优劣对比,至于完全略过了中国旅行家,则多少是一种遗憾,诸如庄学本、曾昭抡这样出色的中国旅人,是很值得阅读和介绍的。
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本书,尽管它还存在很多缺点,但它的不成熟对我恰恰是一种纪念。对我而言,与其说它是工作的产物,倒更像是友谊的产物,它总让我想起那些一再帮助我、陪伴我的可爱同事们。我很庆幸能与他们共处那一段时光,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感谢他们,感谢一直坚守品质的《旅行家》杂志!
最后,还要感谢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老师能奖掖后进,在百忙之中赐序,这也为拙作增添了不少光彩。再次感谢!
胡子华
2016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