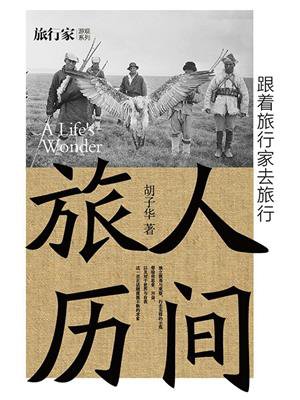法兰西载负我远行

Chateau Briand
夏多布里昂
夏多布里昂(Chateau Briand, 1768-1848),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在那个崇尚异国情调的时代,夏多布里昂的旅行、写作与荣耀都紧密相关。夏多布里昂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19和20世纪旅行的引领者。

左起分别是夏多布里昂所著《墓畔回忆录》、《阿达拉》和《前往美洲:夏多布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开创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国另一位浪漫主义文学代表雨果在其少时就曾立志:“要么成为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也不是。”
然而,正如夏多布里昂自己所言:“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是从《阿达拉》的出版开始的。”1801年,小说《阿达拉:荒原中的两个野蛮人之恋》甫一面世即蔚为风行,夏多布里昂也瞬间成为法国大红人,全国各地表达爱慕的信件像雪花一样拥向他的寓所。
其实早在1784年,夏多布里昂就开始痴迷于虚构自己文学上的“女精灵”,为此“在前半生的荒漠里,我不得不臆造一些人物来点缀我的生命”,但始终未能成功。而1791年的美洲之行,途中壮丽的景色风情、丰富的人物形象都给夏多布里昂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冲击之一就是产生了像阿拉达这样一个“用我自身的养料塑造的生命”。
有趣的是,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并不是为了成为文学家,而是为了成为旅行家。在他的时代,长达几个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所打开的世界空间极为广阔,而技术上日新月异的进步也使得个人探索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向往异国风情的旅行浪潮正方兴未艾。在夏多布里昂的旅行中,我们不仅可以从风土人情和社会风貌中感受到时代的脉搏,也可以了解在国家视角下他对制度文明的优劣比对,从这个角度而言,夏多布里昂确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位旅行家,甚至可以说是19和20世纪旅行的引领者。
在惶恐与野心中出发
“离开这个世界,到一个土地和天空都陌生的世界去。我对祖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同样感到迷茫:谁将沉没?法兰西还是我自己?有朝一日,我还能看见法兰西和我的亲人吗?”当夏多布里昂向着前来送别的母亲挥手,脚下的船只正加速着将他推向大海深处。
远航船本身就像一种风景。船上的乘客熙熙攘攘,置身大海,他们的命运却在陆地上。有些人去寻找财富,另一些去寻找安宁;有的返回他们的祖国,有的离开他们的故乡;还有人是为了了解他方人民的地理、风俗和艺术。而在这条看不见村庄、城市、尖塔,既无圆柱又无里程碑,唯有波浪当界石、海风当驿站、星辰做方向的海路上,对那里正等待着他的命运,夏多布里昂是一无所知的。
彼时,法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局势十分混乱。夏多布里昂离开法国前往美洲旅行,原因之一就是他感到了革命的危险,他认为在当时的法国,“只要有一个贵族姓氏就可能受到迫害。你的看法越正直、温和,就越遭人怀疑、被人追究。我决定急流勇退。”
除了避乱,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去那里寻找“西北航道”,即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航道。他相信在离开的世界和前往寻求的世界之间,祖国仍是载负着他的海水。而一旦成功发现这条航道,“我就能荣幸地将法国人的名字传到那些未知的地方,给我的祖国在太平洋上增加一块殖民地。”
出发之前,夏多布里昂在法国籍籍无名,但受到了当时法国的大人物德·马尔泽尔布的鼓励。在和这位大人物交往时,他们经常伏在地图上,相互观摩北极圈的曲线,一起推算从白令海峡到哈得孙湾的距离;他们还阅读了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瑞典和丹麦诸国航海家和旅行家写的各种游记和故事;他们打听着从陆路到北极海岸的路线,分析沿途需要克服的困难:严寒的气候、野兽的袭击和食物的匮乏等。
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旅行者,大多数法国旅行家都热衷于单独行动。他们极少是被政府和公司雇佣的,或者得到它们的资助,而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在夏多布里昂看来,“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他们国家的援助下,完成我们国家孤立无援的个人所开创,但半途而废的事业。”
于是,这位大人物对夏多布里昂说道:“如果我年轻一些,我会同你一道去,这样我就看不见眼前的这么多罪行、卑鄙和疯狂。可是,在我这个年龄,应该留在我们居住的地方,一直到死。有船的时候,别忘了给我捎信,将你的进展和发现告诉我。我要让部长们关心这件事。很可惜你不懂植物学!”听了这番话之后,夏多布里昂深受鼓舞,不仅翻阅了卢梭的《词典》、《基础植物志》,以及图纳福尔、杜阿梅尔、贝尔纳·德·于西厄、格洛雅甘等人的相关著作,还时常跑去法国植物园,丰富自己的博物学知识。
其实,在旅行中寻找成功的野心,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新的倾向,所以夏多布里昂前往美洲时,除了前途未卜的惶恐,还有成功在望的兴奋。他甚至将自己和拿破仑对比,“寻找西北航道这个计划并非来自我的诗人天性。当时谁都不关心我。我那时和拿破仑一样,是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少尉。我们同时从我们的卑微地位出发,我到孤独中去寻找我的声名,而他到人群中去寻找光荣。”
寻找野蛮人
经过漫长的航海,看见陆地从海底冒出来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在巴尔的摩,夏多布里昂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有那么好一会儿,他抱着胳膊四处打量,内心百感交集。“我要在这片原野上进行哪些探索?”毕竟在这里,他谁也不认识,也压根儿没人认识他。和船长、水手们吃过告别餐后,他在凌晨四点改坐上马车,开始颠簸在这片新大陆上。
可在巴尔的摩,以及别的美国城市,夏多布里昂的失望情绪越来越深。“美国的城市普遍缺少公共建筑,尤其缺少古代建筑。古老的天主教在欧洲筑造起高耸入云的穹顶和尖塔,然而新教却没能在美洲大地兴起欧洲那种建筑。这是因为新教不崇尚想象力的表达,况且其诞生的时间也不久。在费城、纽约以及波士顿,几乎没有什么建筑比围墙和房檐更高,这种整齐划一的高度看起来简直毫无情趣。美国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块从属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多是沿袭别处,而不是自发形成的,所以你能感觉出当地居民并非原住民。这里的社会拥有美好的现在,但却没有过去。这里的城镇是新建的,连坟墓也是昨天才有的。”
夏多布里昂对美国的想象,从头到尾似乎都不是将之看作一个未来之国,而是一个类似罗马那样的过去之城。他是带着寻古的热情踏上美国的土地的,他满心希望在这里看到古代人民的热情和像罗马那样原始而朴素的影子。可他看见的却尽是身着华服之人,他们乘着奢华的马车往来于闹市,其间言谈轻佻;各地赌场肆意横行,更有剧院、舞厅之喧嚣不绝于耳。
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在费城,我几乎以为自己身处一座英国城市,没有什么迹象暗示着我已由一个君主国来到了一个共和国。”在停留半个月见到“偶像”华盛顿之后,他就匆匆离开这些城市,急于继续旅行。“我来这里要看的不是美国人,而是某种同我了解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某种与我的思想的惯常秩序更加协调的东西;我非常想投身这个事业,但除了我的想象力和我的勇气,我对此毫无准备。”换言之,他开始迫切想要接近这片土地上的原始人:印第安人。
抵达奥尔巴尼后,他通过和印第安部落做皮毛生意的斯威夫特先生雇佣了一个懂各种印第安语言的助手,踏上了印第安丛林之行。和印第安人的接触,确实激起了夏多布里昂的旅行热情。当时,欧洲人对印第安人的记叙要么单单介绍他们的律法和风情,而不涉及他们那些怪异的习俗,因为这些往往让文明人感到不适。另一些欧洲记叙者则一概忽略印第安人的律法和民俗,而只展现他们“野蛮”的生活习惯。这样一来,人们所看到的就全变成了烟雾缭绕、肮脏不堪的棚屋,只不过这些“猩猩”会讲人话罢了。
在北美南部的丛林中,夏多布里昂出入于各个印第安部落,和当地人一起生活,用极大的兴趣和耐心了解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他并没有像一开始想的那样能够给每个部落写一部历史。但从留下的记录来看,夏多布里昂对印第安人的了解极其完备,他分门别类地记叙了他们的婚嫁、生育和丧葬仪式;丰收、节日、舞蹈和游戏;年历、时辰的划分和自然历;医药、语言、狩猎、战争、宗教和政府等。某种程度上,已近于一份严格的人类学研究。
永恒的法兰西
夏多布里昂认为自己记录的是野蛮人的历史状态,而不是当下现状。因为现实是北美洲“野蛮人”的人口正在锐减,当时有一些旅行家推测,在落基山一带居住的印第安人已不足十万人。在易洛魁语中,印第安人称自己为“永恒之人”,可事实上,“这些野蛮人部落,他们曾在某个未知的年代登陆并占领了美洲,而如今他们又将消失在这片相同的海岸上”。
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导致印第安人人口锐减的原因众所周知:饮用烈酒、恶习、疾病、战争,而这些都是现代人的入侵带来的。随着部落人口的减少,印第安人独有的文化、知识和传统也不断衰败。他们的宗教传统变得更加混乱,传教的加拿大传教士将外来的宗教思想与当地原住民的本土思想混在了一起,通过粗糙的寓言故事来传播被扭曲的基督教教义,而大多数野蛮人佩戴十字架只不过是为了装饰。
夏多布里昂还指责美国人和英国人用礼物收买、用恶习腐化,以及用武器迫害印第安部落。当欧洲人刚刚渗透到美洲的时候,野蛮人的衣服和食物都是打猎得来的,彼此之间从未进行过任何买卖交易。但欧洲人很快就教会了他们用猎物交换武器、烈酒、各种家用器具、粗布衣服以及个人装饰品。欧洲人就这样通过贸易将文明引入了美洲野蛮人部落。但夏多布里昂认为这种文明非但没有启发他们的才智,反而将他们变得更加野蛮和残忍。这些印第安人开始变得阴险奸诈、自私自利,生活上放纵堕落、四处行骗,而原本整洁的茅舍如今也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这样一来:野蛮人的习俗和礼仪自然而然地随着宗教和白人的统治而退化消亡了,所有属于他们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卷走了。
在夏多布里昂的记叙中,只有法国人仍深受这些原始部落欢迎。他们依恋法国,对法国人有很深的感情,将法国人视为“世界上最聪明、最勇敢、最杰出的民族”。这当然是夏多布里昂的自况。事实上,夏多布里昂一直对法国放弃海外领地感到惋惜。“在非洲、亚洲和南太平洋诸岛上,在南北美洲的大陆上,数以百万计的人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我们用自己的勇气和天才获得的战利品却被夺走了,只能在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的一些小村庄里听到拉辛、考伯特和路易十四的语言,而且还受到外来语言的支配。尽管法语依然残存在这块大陆上,但也不过是我们倒霉的命运和错误决策的见证罢了。”
由此可见,夏多布里昂的态度与法国另一位后来者托克维尔十分相似,他们一边批判殖民给美洲带来的危害,一边又试图为法国寻找新的殖民地;一面强调民族平等,一面却又想使某些民族归顺于法国。他只看到占有这些领地对法国有利,却未曾想过是否对当地居民有利。正如他在游记中坦承的那样:“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来是在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地回到他身上所拖带着的那个世界去。”而这个世界,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就是法兰西。

夏多布里昂面朝大海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