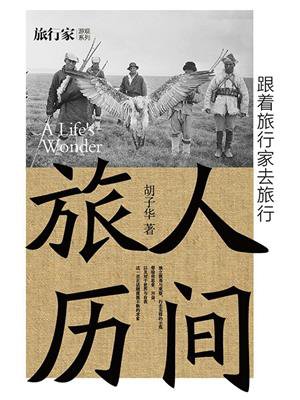关于历史的三种视力

Victor Hugo
维克多·雨果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19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法国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着突出的位置。虽然雨果的旅行多落脚在古老的欧洲,但他的声名却跨越大洋,在世界各地激起极大的反响和热烈的颂扬,并被人们称为“人类良心的最出色代表”。

雨果直接的游历体验和观察多记录在《莱茵河》、《见闻录》等散文随笔式的作

1885年5月22日,雨果逝世,全巴黎30万男人、儿童和妇女一路随着车柩拥向先贤祠,沿途观看的人群更有百万之众。灵柩经行街道的窗户、露台,以几百、几千法郎被抢租一空。在标志着帝国勋业的凯旋门上,挂着一方致哀的大黑幔,全巴黎所有能象征绝望和哀痛的东西都被用上了。
雨果,这个一度近乎半神的人物,这个“人类良心的最出色代表”,在今天我们重新谈起他时,全然把他当作一个老掉牙的人物,一个古老得满身灰尘簌簌的过时者。不少雨果的中国读者,依然还惯性地在他身上搜寻一些类似感动的情绪,或者传授给孩子,用以实现一种不真实的“道德教育”。
从旅行家的角度来理解雨果,反而会是一种助益。雨果是他那个时代一个极其频繁的旅行者(旅行也是他用以调节他和情妇朱丽叶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他的游记是他给友人书信中的一些闲谈之笔,除了少数几篇,写得也并不好看,过多情绪,描写又芜杂得有些枯燥。而他旅途中真正的观察恰恰藏在他的小说里。《巴黎圣母院》里的巴黎观察,《悲惨世界》中的各种“多余的话”,这些看似对小说形成干扰、也不断被读者跳读的部分,才是雨果小说的精华所在,也是雨果作为旅行家的精到之处。
莱茵河:朝向过去的视力
“被感动,就是在学习。”雨果最初在旅行中寻求的只是一些外在事物的震撼,一些新鲜感。出于个人性格,他喜欢壮美的事物,因此,大山大河的自然形态,以及大教堂、市政厅、博物馆等历史遗址,成了他旅途中最为热衷的景观。
对雨果,莱茵河是一条最符合旅途想象的河流,既有自然之壮阔,又不乏思古之幽怀。对莱茵河,雨果也是一个最好的游历者和记叙者。之前,在荷马那里,莱茵河似乎属于灰暗之国,只是可能存在,但不为人知。在维吉尔笔下,它不再默默无闻,却成了一条冰河。对于莎士比亚来说,莱茵河是美丽的,但仅此而已。之后,莱茵河变成了时髦的旅游地,是埃姆斯、巴登和斯帕的无所事事者的散步圣地。
从1838年到1840年,雨果曾经三次游历莱茵河地区。在这三次旅行经历中,刨除过多琐碎和过于多愁善感的枝桠,雨果确实比其他众多文学前辈们更深地发现了莱茵河的筋骨,并开掘出一份开阔的“莱茵河传记”。
最早出现在莱茵河畔的是凯尔特人,这个半开化民族被视为好战和野蛮的代名词,罗马人称他们为高卢人。此后,罗马人一步步取代高卢人,沿河建立了堡垒、城市、殖民地和自治区,分布在悬崖上监视的古罗马军团的士兵也开始连点成线。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中,这条长而牢固的罗马殖民线便如同链条一样连接、加固在莱茵河之上。
旅途中,雨果发现从康斯坦茨湖到七山脉,几乎莱茵河的每个河脊上都有一处城堡遗址,尽管有的现在已经消失了。与此同时,教堂及其遗址几乎也出现在莱茵河的每个转弯处。莱茵河这幅兼具军事与宗教的双重面貌,令雨果感到吃惊。
“人的想象力同大自然一样,不接受空白的存在。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大自然便使鸟儿们啁啾不休,使树叶沙沙作响,使成千上万的声音窃窃私语。而在历史朦胧的地方,想象力便使幽灵出现,使幻想和表象共存。寓言在消失的历史空白区生存、成长、结合、开花,就像英国山楂树和龙胆树生长在倒塌的宫殿裂缝中一样。”雨果发现,早在罗马这只神鹰刚刚展翅之时,就在莱茵河的峭壁上产下了另一只蛋——基督教。许多无名殉教者聚集山林,有人建了隐修院,基督徒圣热泽兰曾在树林中的一根柱子上站立了三年,对抗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女神雕像,最后他终于“用盯视的方法使雕像崩溃了”。
这一时期发生在莱茵河的事件像幽灵一样留下了大量幻象。雨果认为是莱茵河在经过了一个历史时期之后,进入了一个神奇与传说的阶段。恺撒、查理大帝和拿破仑这些莱茵河上的巨人泰坦,他们在某一时刻将世界掌握在手中,然后死神使他们松开手指,一切都从手中失去了。而这些有血有肉的形象开始变得虚幻。查理大帝有了各个年龄层的版本,孩童、青年、老年。罗兰在传说中,不是死于整个军队的攻击,而是出于对莱茵河的爱恋,死在龙南斯威尔特修道院前。这些掺杂在神奇故事中的历史人物,成了怪诞的冒险家,仅仅是用脚后跟接触了实际生活。
在莱茵河的旅途中,雨果走访了纽伦堡城和斯特拉斯堡。他认为14世纪纽伦堡大炮的诞生和15世纪斯特拉斯堡印刷业的出现,这两者的结合才中断了莱茵河军事与宗教混乱交叉的局面,传说消失,文明重现,历史才恢复了形象。
风俗:旅途中的“恶”风景
在雨果参观博物馆、教堂、市政厅这些壮景所带来的愉悦中,常常也夹杂着一些“恶”风景,让他败兴。
小费,被雨果视作一只极其厌恶的“蚊子”,“它时时刻刻都在伺机咬您一口,不是咬您的皮肤,而是咬您的钱包”。对他来说,设立过多名目的小费使得看似友好的满面春风的微笑和热情而诚恳的接待,更像是一种心机的经济。
“在驿站院落里,在路上从未看过您一眼的赶车人来为您打开车门,怡然自得地向您伸出了手:小费。过了一会儿,驿站马车夫也来了,由于警察局的条令禁止他这样做,他嘟嘟囔囔地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意思是:小费。人们取下了车顶遮雨布,一个奇怪的人上了车,将您的箱子和旅行袋放到地上:小费。另一个奇怪的人将行李放在手推车上,问您去哪家旅店,推着车跑在您的前面:小费。又来了第二个人,他想干什么?是将您的东西拿到房间里的那位。您对他说:‘好的,我临走前给您,像给其他的仆人们一样。’那位回答说:‘先生,我不是旅馆里的人。'——小费。您走了出去。看到一座教堂,一座美观的教堂。应该进去看看。您在周围转着,您观看着,您寻找着。门是关着的。一位老妇人看到了您的窘态,她走过来,指给您一个小窗口旁的门铃。您明白了。当您正要踏进教堂门槛时,您感到袖子被人拉住了,是乐于助人的老妇人:小费。您进入了教堂,您观看着,您欣赏着,您啧啧称赞着:‘这幅画上怎么遮着绿帷幕?'‘因为这是教堂中最漂亮的一幅。’教堂执事说。‘我想看看。'——教堂执事转身而去,几分钟后又同另一个极为沉闷、悲哀的人一起回来了。是主管帷幕的人,此人按了一下弹簧,帷幕打开了,您看到了名画。看过后,帷幕又关闭了。帷幕主管人向您致以意味深长的敬意:小费。……”
当然,在这过程中,政府的“小费”更被雨果深恶痛绝。
“护照,一般去西班牙你要做两种旅行,你本人的旅行和你的护照的旅行。不过,在西班牙一份护照所做的旅行多么可怕!它一刻也安静不下来。时时刻刻它会飞出你的衣袋,打开,不见了,又去追。
它是在……?
接着在警署。
接着在市长家里!
接着在市政厅。
接着在……

上图为雨果在考察滑铁卢战场时住的酒店。
下图为雨果画的旅途风景画。
每次交一枚半个比塞塔。为了去西班牙,你在巴黎已经交了一法郎,在巴约讷交了五法郎给领事,在伊伦入境时又交了一法郎!现在,每移动一下,都得付十个苏给宪警,到了每一个城市,每进一扇城门都得领签证。如果你改变主意和改变所进的门,就得领新的旅行签证。十个苏——在西班牙你得随时花十个苏。昨天我被一个奥德里的警察逮住,让我跟他走遍全城来到治安法官办公室。警察认定我是无辜的,但仍然向我索要十个苏,以酬其辛劳,以报答他给予我的光荣。
可怜而又高贵的西班牙啊!刚才有一个怪模怪样的流氓在街上盯住我大叫:老爷!我回头,看到了这个可怜虫,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苏给他,他拿了这个苏,问我要护照。我原把他当作乞丐,但他却真正是个公职人员。什么样的国家就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不过他又是个乞丐,因为他拿了这个苏。他向我查问护照,但并不拒绝布施。”
当然,雨果记录这些并不仅仅是出于旅途的不快,更重要的是,雨果认为,比起记述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记述风俗所负的使命同样严肃。历史学家记录国家大事件,诸如王位之争、王子的诞生、国王的婚姻、战事、议会等。风俗的记录者却深入内部,窥见人与人的暗斗、隐秘的暴行、成见、约定俗成的不公道、心灵的秘密演变、民众的细微惊悸等,这些涉及了另一种真实。
你需要果敢,成为历史的塑造者
1843年,雨果在西班牙进行了一次长达近两个月的旅行。期间,他参观了大量的修道院,那种阴森可怖的氛围给雨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拱顶烟雾弥漫,穹窿因浓重的阴影而朦朦胧胧;下面是巨大的神坛,黑暗中,用铁链吊着高大的白色耶稣受难像;乌木架上陈列着魁伟的基督裸体象牙雕像;那些雕像不仅血迹斑斑,还血肉模糊,既丑陋又富丽堂皇,臂肘露出白骨,膝骨露了皮肉,创伤翻开血肉,头戴银制的荆冠,用黄金钉子钉到十字架上,额头流的血是镶嵌的红宝石,眼里流的泪是镶嵌的钻石。钻石和红宝石仿佛湿漉漉的,引来多少戴面纱的妇女匍匐在下面哭泣。那些女人满身被苦衣和铁针鞭刺破,乳房被柳条兜紧束,双膝因祈祷而磨破,一个个全是以天使自居的幽魂。”
那些女人有思想吗?没有。她们有愿望吗?没有。她们爱吗?不爱。她们活着吗?没有。雨果思忖,修道院作为培养人的学堂和方式,在10世纪是好的,到了15世纪就成问题,进入19世纪则十分可鄙复可悲了。而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出色的国家,正是受到修道院这种“麻风病”的侵害,仅剩下了两副骨架子。
在离布鲁塞尔八公里处,雨果见到了维赖尔修道院旧址。在靠迪尔河边,有四个半在地下半在水中的石室,残留一扇铁门、一个粪坑、一个安了铁条的通风孔;洞口外高出水面两尺,里边离地面六尺。四尺深的河水擦墙而过。牢里地面终年潮湿,隐修的人就以这湿土为卧榻。有的石室墙上还嵌着一段枷锁,或卧不够长、立不够高的石匣,把人放在里面,上边再盖上石板。十足一个坟墓。
尽管在当时,修道院还颇有风潮,里面还充斥着乱弹琴的好材料,可供大量是非者舞弄喉舌。雨果认为,旅行家,也是社会观察家,应当走进这阴暗的地方,这是他们实验室的组成部分。相应地,他们还负有一种职责:为人的灵魂而工作,维护神秘而反对奇迹。“至于我们,该尊重的就尊重,而且处处宽容,只要过去肯承认已经死了。如果它还要活在世上,我们就打击,将它打死。迷信、虔诚、伪善、成见,这些鬼魂,虽已成鬼,却死活不肯离世,鬼气中还有牙齿和利爪;必须向它们开战,展开肉搏,永不停歇地跟它们拼杀;要知道,永生永世同鬼影搏斗,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命数。”
在旅途中,雨果常对不少历史遗迹的破坏深感惋惜,但他并非是一个守古护旧者,他对修道院的鞭挞,正如他对反抗专制的巴黎巷战,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起义的声援一样,是出自一种对历史发展的判断。而且,在这判断之上,他始终也是一个历史行动者,他漫长的流放生涯,或许也是他旅行的另一个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