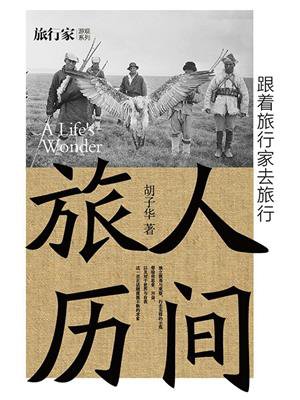为了故事的旅行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威廉·毛姆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英国最受读者欢迎的现代小说家之一,其作品对人性和社会的剖析十分冷峻、犀利,其近于挑剔嘲讽的英式幽默往往让读者又爱又恨,其中不少素材都源自他的旅行收藏。

左起为《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追寻自由》和毛姆小说《面纱》。
对毛姆作品的评价,成了20世纪评论家和读者之间趣味的一个巨大分歧。不仅评论界不认可毛姆,不少小说家同行似乎也持此态度,D·H·劳伦斯就认为毛姆的小说虽然“能把一些人物和地方写得很出色,但仔细推敲,又不免显得虚假”。尽管如此,毛姆的小说、戏剧、游记等作品却在世界各地广受追捧。1951年毛姆去土耳其旅行,他的船一靠岸,一名警官立马赶来充当他的卫士,出版界的记者和读者蜂拥而至;1959年毛姆前往日本,码头上聚集了几千人夹道欢迎,他在东京丸善书店的即席演说,现场由于观众太多,把美国驻日本大使都挤倒在地。
毛姆对此有两个自我判断,一个是自认作“二流作家中排在前面的一个”,另一个是强调自己“只是个讲故事的人”。关于前一个判断,考虑到毛姆的自我骄傲和终其一生对评论家们的不屑,或可视作是他以退为进的一记妙招;然而后一个判断则充分显示了毛姆的诚实。换言之,故事性正是毛姆作品广受读者欢迎的一个秘诀,也正是旅行为毛姆提供了大量的故事以及故事中浓郁的异域风情。为了寻找故事,毛姆遍走远东、中亚、北非、墨西哥以及南太平洋中的英属与法属岛屿等地,因此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世界旅行家。
为了故事的旅行
本雅明有一个关于讲故事的人和小说家的区分:“讲故事的人从经验——自己的经验或从他人那里听来的经验——中获取他要讲的故事。他转而又把这种经验转变为听故事的人的经验。小说家则封闭自己。小说的诞生之地是孤独的个人。”
毛姆是一个热衷于讲故事的人,如果不是口吃,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交圈里的宠儿,或者讲台上绘声绘色的演说家。正是口吃这一残疾把毛姆从口头逼向印刷文本,成为一个介于小说家与讲故事者中间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毛姆作品在评论界遭受的冷遇和读者的热捧,另一方面也厘清了毛姆在写作与旅行之间的互生关系:依赖旅行获得故事以及故事中异域风情的华彩,又通过出版故事赢得名望和金钱,从而可以无所顾忌地旅行。
旅行为了故事,这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毛姆旅行的特质,既紧张兮兮又趣味横生。1924年10月,毛姆到墨西哥城旅行时,正巧碰到D·H·劳伦斯也在那里。俩人见了面,但互不喜欢。毛姆认为劳伦斯是一个病态人物,劳伦斯则觉得毛姆“能把一些人物和地方写得很出色,但仔细推敲,又不免显得虚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毛姆这人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没有什么趣味,那种担心自己在圣诞节前写不出以墨西哥为背景的伟大作品的劲儿,真叫人好笑。”
这种旅行中的紧张状态对今天任何一个旅行记者而言,都可能是极其熟悉的。但毛姆作为旅行家的了不起之处正在于即使在习以为常的旅途中,他也能创造出新趣味,并发现新的故事。在创作的前二十年时间里,毛姆一直觉得印度是吉卜林的天下,他认为所有关于印度的好小说都被吉卜林写完了,因此他一直回避写印度,既不关心印度艺术,也不去印度旅行。直到1937年12月,那时毛姆正在构思一部年轻人弃家出走皈依印度教哲学的小说。毛姆一贯主张创作要来自真实的旅行和生活,为获得第一手材料,他决定去印度旅行一趟。
毛姆怀揣一份从邻居那里得到的给印度各个土邦邦主的介绍信,踏上了印度的旅程。从1938年1月到4月,毛姆“遇见了各种古怪的人——印度人、信奉瑜伽的人、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术士以及那些不知是什么人的人——看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事物”,其中体验最深的是在南端马都拉一座建于17世纪敬奉西瓦女神的大庙中,那些宗教仪式中光着上身的男人们,在胸口上涂抹着牛粪烧成的白灰,一个个脸向下,身体成俯卧姿态,这种对西方一无所知的真正的印度带给了毛姆“一种神秘而可怕的东西”,也即他自感发现的一个没有英国人的印度。这次旅行不仅构成了一本名叫《客厅里的绅士》的游记,其后对印度旅行的不断反刍也为其名作《刀锋》积累了实地经验。
相比吉卜林、福斯特,乃至后来的奈保尔,毛姆似乎不那么“现代”或“先锋”,其印度小说《刀锋》也没显示出过多的表达“印度”的野心,但是一如既往的好看,气氛十足。
人是最深的风景
毛姆自认不是一个“勤勉的观光者”,每当他的向导或朋友极力主张他去拜访名胜古迹时,他都会产生一种顽固的想撵走他们的冲动。对于风景,他总是宁愿自己四处闲逛,以一种偶然的方式去发现。1919~1920年,在毛姆旅行中国期间,我们熟知的那些风景名胜在他的游记里几乎消失殆尽,相反,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人群却都成了他笔下的细致风景。
“我从来对景点没有很大兴趣……我喜欢的都是些平常的景观,果树丛里的一栋木头房子,椰子树环绕的小海湾,或者路边一丛竹子。我更在乎的是人群和他们的独特生活……回想旅途中遇到的那些人,每一个都有让我感兴趣的故事。我感觉自己像照相机里的底片,最终成像是不是绝对的真相,对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够利用我的想象力让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可信的协调的个体。这个过程是个令我着迷的游戏。”纵观毛姆全部的旅行,人永远是最深的风景,因为正是旅途中的人集聚着最多的故事。
事实上,毛姆因为口吃,一度与人交际紧张,加上他对人的敏锐,使他易于识破人的弱点,所以在谈话中经常会变得刻薄和乏味,惹人不快。但在旅途中,毛姆会生出一种巨大的热情,能够四处去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甚至包括那些他反感,以后不愿再见面的人。
为了见一个旅途中听闻的智者,毛姆可以坐火车转汽车再骑驴去找,当他提着一篮子水果出现在泥泞的马路上,最终见到智者时却因为过于疲惫而昏厥。旅行中国时,为了拜访辜鸿铭,他赶到成都,四处托人搭线介绍。他坐民船溯扬子江而上,走了1500英里的水路,接着又凭两条腿走了400英里旱路,沿途目的全是为了见人。其中既有中国的官员、戏剧家、船工和其他市井民众,也有那些在华的英国人。他们当中有长期在华工作的海关人员,也有初来乍到每天去英国俱乐部看伦敦报纸的年轻职员,还有那些阅读卢梭、向往社会主义却脚踹人力车夫的人;那些口头称爱,心里却怀着怨恨的牧师;那些沾沾自喜的皇室代表团成员;还有那些只是想为伦敦客厅复制一些中国艺术品的英国妇女……诸如此类,构成了他中国之旅中最绝妙的风景。
在西班牙旅行时,毛姆刻薄地认为那里的文学和艺术都很贫乏,声称西班牙人在艺术领域毫无建树,只产生了一位了不起的作家和一位最一流的画家,建筑的典范也都有赖于摩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设计。然而,毛姆通过旅途感受到西班牙之所以伟大的奥秘,就在于那里的人。“在西班牙,人就是诗歌,是绘画,是建筑。人就是这个国家的哲学。这些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人生活着,感受着,行动着,但他们并不思考。他们追求并发现的是生活,是骚动的、热烈的、多样的生活。激情是他们生命的种子,激情也是他们绽放的花朵。他们的卓越之处很伟大,但却在不同的方向:那是一种性格的卓越。在这一点上,我想无人可以超越他们,只有古代罗马人才能与他们匹敌。这个精力旺盛的民族似乎将它所有的活力和独创性都投入了一个目标:一个唯一的目标:人的创造。他们并不擅长艺术,他们擅长的是一个比艺术更加伟大的领域——人。”
对毛姆而言,旅行的妙处正在于既可以感受一种精神自由,又可以收集各色各样的人物,以备后用。“我关注、寻找特立独行的人、古怪的人和当地名人。很快我就能够判断一个地方是不是想告诉我什么,如果是的话,我就守株待兔,否则就过路不停。旅途中的一切体验我都照单全收。”深知旅行对写作重要性的毛姆,曾于1946年设立了毛姆奖,用于奖励优秀的年轻作家,鼓励并资助他们到各处旅行。
旅行如何成就故事
旅行中国时,毛姆遇见了一位极其热爱旅行的英国浪游者。他起先在伦敦工作,后来通过担任商船的伙食管理员到达了智利,并从那里设法到了南太平洋的法属马尔贵斯群岛,在土人中间住了六个月后,又旅行到了大溪地,然后乘坐一艘运送中国劳工的老式木船到了厦门。在中国,他在粗略掌握了汉语之后,在一家药厂工作,有三年时间,为了兜销药丸,他从这省漫游到那省,屐旅处处。在攒足八百块大洋后,这位浪游者果断放弃工作,开始了一场横越中国的旅行。在旅途中他装扮成一名穷苦的中国老百姓,扛着铺盖卷儿,撇着旱烟管,和跑长路的人拥挤在土炕上,沿途吃着中国饮食。他很少乘火车,绝大部分靠两条腿步行,坐牛车或搭民船,他从陕西到山西,攀登上狂风怒号的蒙古高原,冒着生命陷在土耳其野蛮部落中间。经年累月困守在沙漠的游牧民族中,和运着砖茶的沙漠商队跋涉过干旱不毛的戈壁,整趟旅程长达四年。
毛姆企图从他那里听到他对旅途中的人和事物的绝妙观察,并从中辨别那些丰富多彩的旅行经验如何影响了他。然而一番交谈下来,毛姆却发现这位浪游者的冒险事业从未从心灵深处触动过他。这位浪游者虽然亲眼看见过各式各样的事物,却只是乱糟糟似地看着这一切,他的经验仅仅停留在肉体上,从来没有翻译成为灵魂的经验。因此,所有他做过的这些冒险的经历,似乎只说明了他脾气古怪而已。“这就是为什么这位浪游者有那么多东西可写,而他却写得那么令人厌倦。致以写作重要的事情是,不怕没有丰富的材料,而是怕没有丰富的人性。”
“我知道有些作家作冒险之旅,但随身带着他们伦敦的房子、他们的一众朋友、他们的英国趣味与名望;待到返家,他们惊觉自己与出发之时全然相同。”对毛姆而言,旅游经历除了制造一点谈资,本身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如何借助旅行丰富自己的个性。因为一个小说作家越了不起,就能创造越多的人物,而这个数目受制于那个自我,所以“作家启程旅行,必须留下的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并不断去接纳更多的人。
旅途中,毛姆认为“人比书有趣,但有个缺点,你不能跳读。为了发现精彩的一页,你至少得浏览全书。你不能把它们放到书架上,等你想读的时候才拿出来。你必须得趁机阅读,就像流动图书馆的一本书,它在你手里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如果这时你没心情读,或者正处在匆忙之中,那么你就错过了它们要给你的最好的东西。”正因如此,毛姆对待旅途中的人,要耐性得多,也敏锐得多。换言之,任何一个在旅途中和毛姆交谈的人都是危险的,也许你不经意的一句话就会让你成为他书中一个难堪的角色。正如美国作家依修伍德说的那样,毛姆让他想到贴满标签的旅行箱,然而只有上帝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旅行时,很多热情的在华英国人款待了毛姆。然而,进入毛姆眼中,那些成天赴宴的人只是因为他们无事可做,他们相互之间也厌烦得要死;那些和他接触的传教士口中不断诉说中国人的善良,心里其实恨着中国人,而且凡是他的意志上所爱的,他灵魂上都厌恶。绝大多数旅行者在旅途中只能做到敏感,而毛姆做到的却是敏锐,而无论如何,敏锐要比敏感重要得多,这也是毛姆强调旅行时要放下自我的原因。正是这些敏锐的观察让旅行的故事开始成其为故事,这些遇见的原型人物才能进入作品成其为人物。“作家并不是复制他的原型,他从原型身上提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吸引他注意的某些特征,点燃其想象力的气质倾向,从而构建他的人物。”毛姆作品中的人物大多也都实有其人。
除此之外,旅途中大量与人的相遇也在向毛姆揭示,正常其实是最罕见的,那是人们根据人性的共性编排出来的一幅画,而这些人类共性要在一个人身上找到是很难的。这使得毛姆对待旅途中的人更宽容,也为自己提供了修复:“在知识分子圈里混会使人圆滑,因为你是一袋子石子中的一块。而跟旅途中这些奇奇怪怪人的接触让我丢掉了那种圆滑,让我的边角又长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