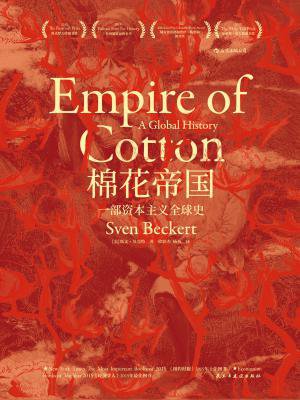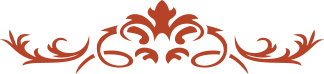
绪 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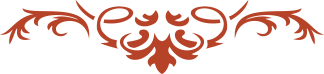
1860年1月底,曼彻斯特商会的成员聚集在该市市政厅举行年会。在当时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的中心聚集的这68人中,最显要的当属棉花贸易商和棉产品制造商。在过去的80年里,这些人把周围的农村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囊括农业、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全球性网络的枢纽。商人们将原棉从世界各地运到英国的工厂,这些工厂拥有当时世界三分之二的纱锭。一大批工人把棉花纺成线,织成成品织物,然后经销商把它们销售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去。
这些出席年会的绅士们兴高采烈。商会主席埃德蒙·波特(Edmund Potter)提醒他们注意到本行业的“惊人增长”以及“全国的普遍繁荣,尤其是曼彻斯特地区的繁荣”。他们的讨论话题非常广泛,涉及从曼彻斯特、英国到欧洲,从美国、中国、印度到南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棉产品制造商亨利·阿什沃思(Henry Ashworth)更是喜不自胜地庆贺道:“这是前所未见的商业繁荣。”

这些自鸣得意的棉花贸易商和棉产品制造商有理由沾沾自喜:他们站立在一个世界性帝国——棉花帝国——的中心。他们统治的工厂里,成千上万的工人操作着巨大的纺纱机和轰鸣的动力织布机。他们从美洲的奴隶种植园获得棉花原料,再将其工厂的产品贩卖到世界各地最偏远的角落去。虽然他们自己的职业可以说平淡无奇,就是生产并贩卖棉线和布料,但是这些棉花商人却以惊人的从容在讨论世界各地的事务。他们拥有的工厂嘈杂、肮脏、拥挤,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讲究;他们生活的城市为燃煤蒸汽机的煤烟所熏黑;他们呼吸的空气中夹杂着人们的汗臭味和秽物的恶臭。他们运转着一个帝国,但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帝王。
仅仅100年前,这些棉花商人的前辈们还会觉得“棉花帝国”的想法不可想象。在那个时代,人们仅仅种植小批量棉花,在壁炉边纺织;在联合王国,棉花加工业最多是个边缘行业。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欧洲人知道美丽的细平布(muslins)、轧光印花布(chintz)和纯色棉布(calico),法国人将这些布料统称为“印度货”( indiennes ),它们从伦敦、巴塞罗那、勒阿弗尔、汉堡和的里雅斯特的港口进入欧洲。欧洲农村也有男女纺纱织布,但产品难以和东方来的织物匹敌。在美洲、非洲,特别是在亚洲,农民将棉花分种在马铃薯、玉米和高粱之间。他们用棉花纺纱织布以满足其家庭自身的需要或他们统治者的需要。几个世纪来,甚至1000年来,生活在达卡、卡诺、特奥蒂瓦坎和其他地区的人们已经能够生产棉质布料并在布料上印染漂亮的颜色。他们生产的织物一部分行销全世界。有些布料非常精美,同时代的人称之为“风织品”(woven wind)。
在过去,妇女们要么在农舍里坐着矮凳用小型木质纺车纺纱,要么坐在小屋前用纺纱杆和纺纱钵纺纱;然而在1860年,一切都改变了,数以百万计的机械锭子——由蒸汽机驱动,由受薪工人(其中许多是孩子)操作——每天运转14个小时,产出数百万磅纱线。棉花不再由家庭种植并被纺成纱线织成布料,而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在美洲种植园里种植,供应数千英里之外的需求极大的工厂,而这些工厂又距离布料的最终消费者数千英里;在世界各大洋装载着美国南方棉花或英国棉纺织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驮运西非棉纺织品的骆驼商队。到1860年,刚才那些参加集会庆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的棉花资本家把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整合的棉花产业看作理所当然,虽然他们所帮助创造的世界仅仅是新近才建成的。
然而在1860年,未来和过去一样难以想象。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世界棉花产业会发生剧烈变迁的话,这些棉产品制造商和贸易商也会嗤之以鼻。到1960年,大多数原棉以及大量棉线和布料再次出产于亚洲、中国、苏联和印度。在英国、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新英格兰,只有极少数的棉花工厂保留了下来。此前的棉花产业中心——曼彻斯特、米卢斯、巴门和洛厄尔等——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并为失业工人所困扰。事实上,在1963年,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棉花贸易协会之一的利物浦棉花协会(Liverpool Cotton Association)拍卖了办公家具。
 棉花帝国,至少由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已经崩溃了。
棉花帝国,至少由欧洲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已经崩溃了。
本书讲述的是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兴衰的故事。但是由于棉花的中心地位,本书研究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缔造和重塑的变迁过程。运用全球尺度的分析框架,我们将会了解,在如此短的时期内,欧洲那些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和有权势的政治家是如何通过将帝国扩张和奴隶劳动与新型机器和受薪工人结合起来,重塑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的。他们所创造的特别的贸易、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形式颠覆了千年以来世界上原有的各个分散的棉花世界。他们给棉花产业注入活力,投入改变世界的能量,并随后以其为杠杆改变了世界。欧洲的企业家和政治家掌握住这一古老作物的生物学馈赠,掌握了亚洲、非洲和美洲传统棉纺织技术,占据了其巨大市场,建立了有着巨大规模和能量的“棉花帝国”。不过讽刺的是,这些令人震撼的成就也唤醒了最终使他们在自己创造的棉花帝国中被边缘化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终生操劳,在慢慢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大片棉花田里耕作,从顽强的棉花作物上摘下数以亿计的棉铃,把棉包从车上搬到船上,再从船上搬到火车上,还通常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从新英格兰到中国的“撒旦工厂”中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为了攫取肥沃的土地而发动战争,种植园主将不计其数的人置于枷锁之下,雇主缩短了他们的工人的童年,引入新机械导致古代产业中心的人口减少,而工人,不论奴隶还是自由人,都为了自由和维持生计的工资而斗争。那些凭借一小块土地维持生计、在粮食作物旁种植棉花的男男女女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生活方式的终结。他们抛下农具,前往工厂。在世界其他地方,许多自己织布并穿着自己生产的衣服的人,发现他们的商品被无休无止的机器产品淹没。他们离开了纺车,进入田野里,陷入了无休止的压力和无尽的债务陷阱中去。棉花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奴隶和种植园主、商人和政治家、农民和商人、工人与工厂主不断进行全球斗争的场所。在这一点,还有其他很多方面,棉花帝国开创了现代世界。
今天,棉花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很难认识到棉花也是人类的一个伟大成就。在你阅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也许你就正穿着由棉花织成的某种衣物。很有可能你从没有在棉枝上采过棉铃,未曾见到过原棉的纤细纤维,也从没有听到过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噪声。对于棉花,我们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将它的恒久存在视为理所应当。我们贴身穿着它。我们睡觉盖着它。我们把婴儿裹在它制成的襁褓里。棉花应用在我们平时花的纸币上、早上用来醒脑的咖啡滤纸上、做饭用的植物油中、盥洗用的肥皂里以及人类战争中的火药里。事实上,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因发明结合了硝化甘油和硝化棉的无烟火药,于1887年获得英国专利。棉花甚至是你手中的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成分。
从公元1000年至1900年,在大约900年的时间里,棉花产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业。虽然现在棉花产业已经被其他行业超越,但是其依旧在就业和国际贸易领域保持着重要地位。棉织产品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2013年,全世界出产了至少1.23亿包棉花,每一包大约有400磅重。足可以为地球上每个人生产20件 T 恤衫。这么多包的棉花如果堆叠在一起,将可以堆成一座四万英里高的巨塔;如果将其前后相接,可以绕地球一圈半。从中国到印度再到美国,从西非到中亚,棉花种植分布在世界各地。人们将生产的原棉牢固地打成包,运往世界各地的工厂去,这些工厂雇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最终的产品又随后被卖到世界各地,从偏远的农村商店到沃尔玛超市都能看到。事实上,棉花可能是为数不多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买到的人造商品之一,这既证明了棉花的效用,也证明了资本主义在迅速推动人类生产和消费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绩。正如最近美国的一则广告相当准确地宣称的那样,“棉花是生命的质料”(Cotton is the fabric of our lives)。

如果可能,不妨设想一下,世界上如果没有棉花会如何。清晨醒来,你睡在垫着皮毛或稻草的床上。你穿着羊毛衣服,或者根据气候或你的财产状况,穿着亚麻甚或丝绸衣物。你的服装很难清洗,要么是由于太贵,要么是由于你自己动手太费力气,因此你将不怎么经常更换衣物。这些衣物会气味难闻,还使人感到瘙痒。它们大多是单色调的。因为与棉花相比,羊毛和其他自然纤维并不容易染色。而且没有棉花将导致你身边满是绵羊,因为如果要生产与现在世界棉花消费量相当的羊毛,就要养活70亿只绵羊。这70亿只绵羊需要占用7亿公顷的土地来放牧,约为今天欧盟地表面积的1.6倍。

确实难以想象。但是在欧亚大陆最西端的边缘,没有棉花的世界存在了很长时间。这个地方就是欧洲。直到19世纪,棉花尽管不是未知的,但在欧洲纺织品的制造和消费中仍处于边缘位置。
为什么是欧洲这个和棉花没有什么关系的地区缔造并支配了棉花帝国?1700年时,任何一位理性的观察家都会认为世界棉花生产将仍以印度或中国为中心。而且事实上,直到1780年,这些国家生产的原棉和棉纺织品数量远大于欧洲和北美。但是随后事情发生了变化。欧洲的资本家和国家以惊人的速度占据了棉花产业的中心。他们利用他们的新地位启动了工业革命。中国和印度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则越来越屈从于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棉花帝国。随后这些欧洲人以充满活力的棉花产业为平台,创造出一系列其他产业;事实上,棉花产业成为更广泛的工业革命的跳板。
1835年,利兹一家报纸的业主爱德华·贝恩斯(Edward Baines)称棉花产业为“工业史上无可比拟的奇观”。他声称分析这一奇观要比研究“战争和王朝”更值得“让学者们费心”。我赞同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紧随棉花的是现代世界工业的起源、快速而持久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生产力增长以及惊人的社会不平等。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策制定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者都曾试图解释这一切的源头。特别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缓慢经济增长后,一小部分人在18世纪末突然间变得更加富足。学者现在将这几十年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这是仍支配着今日世界结构的巨大分裂的开端,这是工业化国家和未工业化国家、殖民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分裂。人们很容易提出宏大的论述,其中一些极度悲观,而另一些则充满希望。然而,在本书中,我要用全球性、从根本上是历史性的方法来探究这个谜题:我从考察所谓“大分流”初始阶段崛起的工业开始我的研究。

对于棉花及该产业非常具体且常常残酷的发展过程的集中研究,使我对那些对许多观察家而言视为理所当然的若干解释产生了怀疑。实际上,这一研究挑战了一些新近的和不那么新近的论断:欧洲爆炸式的经济发展是因为欧洲更加理性的宗教信仰、欧洲人的启蒙传统、欧洲人居住的气候环境及大陆地理情况,或者是因为优秀的机构或制度,如英格兰银行或法治。这些属性的确重要且通常不易改变,然而却不足以解释棉花帝国的历史,也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结构的持续变动。而且这些解释通常也是错误的。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并不像人们通常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自由、精干、有着可靠且不偏不私的机构的国家。相反,英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拥有巨大的军费开支,几乎持续处于战争状态,有着强大且持干涉主义的官僚体制,税负高,政府债台高筑,实施保护主义关税,而且也并不民主。专门研究某一特定区域或国家内部的社会阶级冲突的“大分流”理论也同样有瑕疵。相反,本书以全球的视野展现欧洲人如何将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去塑造——常常以暴力的方式——一个全球性生产复合体,并随后利用资本、技术、各种网络和棉花机构来促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而正是这些技术和财富的增长定义了现代世界。通过回顾过往的资本主义,本书描述了资本主义运作的历史。

与大多数撰写资本主义历史的著作不同,《棉花帝国》并不致力于仅仅解释世界的一部分。本书将在全球框架下理解资本主义,这也是唯一能恰当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方式。全球范围内资本、人员、货物和原料的流动,以及世界上遥远地区之间联系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大变革的真正核心,因此它们也是本书的中心主题。
世界如此彻底而迅速地重建,只是因为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贸易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出现才成为可能。奴隶制、对原住民的剥削、帝国扩张、武装贸易、众多企业家对人民和土地主权的主张,是它的核心。我把这个系统称为“战争资本主义”( war capitalism )。
我们通常认为资本主义——至少就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全球化的、大规模生产的资本主义——是1780年左右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但是16世纪开始发展的战争资本主义在机器和工厂出现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战争资本主义繁荣于战场而非工厂;战争资本主义不是机械化的,而是土地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基于对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和劳动力的暴力掠夺。通过这些暴力掠夺,欧洲人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新知识,这些反过来又加强了欧洲的机构和国家——这一切都是欧洲19世纪及之后非凡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许多历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商人”资本主义或“重商”资本主义时代,但“战争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更好地表达了其野蛮性与暴力性,以及它与欧洲帝国扩张的密切联系。战争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但是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它发生于一系列不断转移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又嵌入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在世界某些地方,它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
一提到资本主义,我们会想到受薪工人,然而资本主义的前期阶段并不基于自由劳动,而是基于奴隶制;我们会把工业资本主义与合同和市场联系在一起,但早期资本主义常常并非如此,而是依靠暴力和强制劳动;当代资本主义赋予产权以特殊地位,但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大规模攫取和有保障的所有权一样常见;近代资本主义建立在法治和得到国家支持的强大机构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尽管最终需要获得国家力量的支撑来建立世界范围的帝国,却往往是建立在私人个体不受限的行为基础上的——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以及边疆地区资本家对当地原住民的统治。这种高度侵略性、外向型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效果是,欧洲人能够支配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棉花世界,并将它们整合到一个以曼彻斯特为中心的单一帝国之中,随后创造了我们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全球经济。
正是在战争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演化出了更为人熟知的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是由强有力的国家塑造的,而国家拥有强大的行政、军事、司法和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起初,工业资本主义仍然与奴隶制和土地掠夺紧密相连,但是随着它的制度——从受薪工人到财产权——得到加强,这些制度使世界上许多地区的劳动力、原材料、市场和资本能够以不同的新形式进行整合。
 这些新的整合模式驱动着资本主义革命进入到世界上更多的角落。
这些新的整合模式驱动着资本主义革命进入到世界上更多的角落。
随着现代世界体系的成熟,棉花主导了世界贸易。棉纺织厂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欧洲和北美其他制造业工厂数量。几乎整个19世纪的美国经济都由棉花种植主宰。新的生产模式是在棉花生产中首先出现的。“工厂”本身就是棉花产业的发明。同样,美洲奴隶制农业与欧洲制造业的联系也是棉花产业的发明。由于几十年来棉花产业是欧洲最重要的产业,所以它也是巨额利润的源泉,并最终滋养了欧洲经济的其他部门。棉花产业实际上也是几乎所有其他地区——美国、埃及、墨西哥、巴西、日本和中国——工业化的摇篮。同时,欧洲对世界棉花产业的控制导致欧洲以外绝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一波“去工业化”浪潮,产生了一种融入全球经济的不同形式的新整合。
工业资本主义的建设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然后在19世纪初扩展到欧洲大陆和美国,赋予了接受工业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中的资本家巨大的力量,但也在棉花帝国内埋下了进一步转型的种子。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扩散,资本自身更多地与特定的国家捆绑在一起。国家在这一过程获得了更为中心的角色,成为最为持久、强大且扩展迅速的机构,劳工群体的规模和权力也大为增长。资本家对国家的依赖,以及国家对人民的依赖,赋予了那些在工厂的地板上夜以继日工作、生产资本的工人以权力。到19世纪下半叶,工人以工会和政党的形式集体组织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缓慢地提高了工资并改善了工作条件。反过来,这又增加了生产成本,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低成本生产者创造了机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工业资本主义的模式已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受到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精英的追捧。由此,棉花产业离开了欧洲和新英格兰,回到了其发源地:全球南方。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这里对棉花帝国所做的论断不适用于其他商品。毕竟,在1760年前,欧洲人已经在广泛地贩卖多种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商品,包括糖、大米、橡胶和靛蓝。然而,与这些商品不同,棉花有两个劳动力密集的生产阶段,一个位于农田,另一个位于工厂。糖和烟草没有在欧洲社会形成大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棉花做到了;烟草没有导致庞大的新型制造业企业的崛起,棉花做到了;靛蓝的种植和制作过程没有为欧洲制造商创造巨大的新市场,棉花做到了;美洲的水稻耕作没有引起奴隶制和雇佣制的爆炸性增长,棉花做到了。因此,棉花产业跨越了全球,不同于其他任何行业。由于棉花产业以这些新方式将各大洲织在一起,它为理解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典型的极大的不平等及全球化漫长的历史和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等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们难以看到棉花产业重要性的一个原因是,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它常常为那些煤矿、铁路和巨大的钢铁工厂的形象——工业资本主义更有形、更巨大的证明——所遮蔽。我们常常紧盯着城市而忽视农村,紧盯着欧洲和北美现代工业奇迹,而忽略工业与世界各地原材料生产者和市场的联系。我们往往倾向于把奴隶制、攫夺剥削、殖民主义等事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抹去,渴望塑造出一个更高贵、更纯洁的资本主义史。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是大部分当代生活的基础;我们不仅仅在经济上,同样也在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投身于资本主义制度。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更容易被忽视。
相比之下,19世纪的观察者已经意识到棉花在世界重塑过程中的作用。其中一些观察家歌颂新全球经济令人惊讶的变革力量。1860年,曼彻斯特《棉花供应报道》(
Cotton Supply Reporter
)相当激动地声称:“在本世纪数量众多且庞大的机构中,棉花业似乎注定担当领导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展……棉花及相关商业活动已经成为诸多现代‘世界奇迹’之一了。”

当你看着棉花作物时,它看起来实在不像世界奇迹的候选。棉花朴实且不起眼,形状和尺寸有很多种。在欧洲缔造棉花帝国之前,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种植的棉花品种彼此大不相同。南美洲一般种植海岛棉(
G. barbadense
),这是一种低矮枝密的灌木,开黄色花,生产长绒棉;印度的农民一般种植树棉(
G. arboretum
),这是一种6英尺高的灌木,开黄色或紫色的花,生产短绒棉;非洲长的是一种和树棉很像的草棉(
G. herbaceum
)。到19世纪中叶,陆地棉(
G. hirsutum
)在棉花帝国中占据主导地位,也被称作美国陆地棉。这一变种棉花起源于中美洲,1836年时安德鲁·乌尔(Andrew Ure)是这么描述它的:“高约两到三英尺,后分叉成枝,上面长满密密麻麻的茸毛。叶子的背面也长满茸毛。叶子有三到五浅裂,最上面的叶子则是完整的心形,叶柄柔软;靠近树枝末端的花开得很大,且通常颜色暗淡。蒴果为卵形,四室,几乎有苹果般大,能产出像丝一般柔软的棉絮,在市场上享有盛名。”

这蓬松的白色纤维就是本书的中心。这种植物本身不会创造历史,但如果我们仔细地聆听,它将会告诉我们世界上以棉花为生的人的故事:印度织工、亚拉巴马的奴隶、尼罗河三角洲各市镇中的希腊商人、兰开夏高度组织化的手艺工人。棉花帝国正是由他们的劳动、想象力和技艺建成的。到1900年,大约1.5%的世界人口——成百上千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从事棉花种植、运输或者棉产品制造。正如19世纪中叶的马萨诸塞州一位棉产品制造商爱德华·阿特金森(Edward Atkinson)所言:“没有任何其他一种产品,对这片土地的历史和制度有着如此强大而邪恶的影响;可能也没有任何一种其他产品,这片土地的未来福祉要更依赖它。”阿特金森所谈论的是美国及其奴隶制历史,但他的评论可以应用到全世界。

本书追随着棉花从田地到船只、从商铺到工厂、从采摘者到纺纱工到织工再到消费者的历程。本书不会把巴西的棉花史与美国的棉花史分开,把英国的棉花史与多哥的棉花史分开,或是把埃及的棉花史与日本的棉花史分开。要理解棉花帝国及与之相关的现代世界,我们只能将诸多地方和诸多民族联系起来,而非分别看待;他们影响塑造了棉花帝国,反过来又为棉花帝国所影响。

我关心的主要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棉花,这一19世纪最主要的全球商品,把那些似乎截然相反的事物——奴隶制与自由劳动力、国家与市场、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工业化与去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然后以一种近乎炼金术的魔法将其转换为财富。棉花帝国依赖种植园和工厂、奴隶和受薪劳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铁路和蒸汽船——简言之,依赖一个由土地、劳动力、运输、制造业以及贸易组成的全球网络。利物浦棉花交易所(Liverpool Cotton Exchange)对密西西比棉花种植园主有巨大的影响,阿尔萨斯地区的棉纺织厂与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紧密相连,而新罕布什尔或达卡手摇纺织机的未来取决于多种因素,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之间的铁路建设、波士顿商人的投资决定以及华盛顿和伦敦制定的关税政策。奥斯曼土耳其国家对其农村地区的力量会影响到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发展;美国最近获得自由的奴隶的政治行动也会影响到印度农村棉花种植者的生活。

从这些变幻无常的对立之中,我们看到了棉花如何使资本主义的诞生成为可能,又如何促成了其后续的再创新。当我们考察数百年来棉花及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交叉相织的道路时,我们会一再地发现,任何资本主义形态都不是永恒或稳定的。资本主义史上每一个新时刻都创造了新的不稳定性,甚至是冲突,促成了巨大的空间、社会和政治的重组。
关于棉花的著作有着悠久的历史。实际上,棉花产业可能是所有人类工业门类中研究得最为充分的。图书馆里关于美洲种植园,关于英国、法国、德意志地区和日本棉花产业开端,以及彼此联系的商人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试图将这些多样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还很少,也许最卓有成效的努力还是近两个世纪以前的事了。爱德华·贝恩斯在1835年撰写《大不列颠棉花产业史》(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时,他总结道:“请允许作者表达……他的主题引起的兴趣不仅来自他所尝试描述的工业分支的重要性,也来自它所建立的这个国家与地球每个部分之间的大范围的相互交流。”
 虽然不全同意他的结论,但我也分享着贝恩斯的热情,赞同他的全球视野。
虽然不全同意他的结论,但我也分享着贝恩斯的热情,赞同他的全球视野。
作为利兹一家报社的编辑,贝恩斯生活在棉花帝国核心附近,他不可能不对这些事物采取全球视角。
 然而,当专业的历史学家转而研究棉花时,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棉花产业历史的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层面。然而,只有全球角度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宏大的调整,所有这些地方故事不过是整体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变迁、由民族主义精英推动的国家强化项目的扩散、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其他等等。
然而,当专业的历史学家转而研究棉花时,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棉花产业历史的地方、区域和国家等层面。然而,只有全球角度才能让我们理解这一宏大的调整,所有这些地方故事不过是整体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变迁、由民族主义精英推动的国家强化项目的扩散、工人阶级集体行动的影响以及其他等等。
本书利用了大量关于棉花的文献,但将其置于一个新的研究框架之中。因此本书对关于全球化的对话做出了一些贡献。这些对话充满活力,但常常持现在主义(presentist)立场,因而僵化且缺乏历史视角。有些人兴奋不已地声称发现了资本主义史的新的全球化阶段,《棉花帝国》一书挑战这些看法。本书认为,资本主义自起初就是跨越全球的,而世界经济的流动空间格局是过去三百年的共同特征。本书还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历史中,全球化的过程与民族国家的需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相互冲突,而是彼此加强。如果这个所谓的新的全球化时代是对过去的革命性背离,那么这个背离并不是关于全球性联系程度的,而是在于资本家第一次能够从那些特定的民族国家解放出来,而过去正是这些民族国家使他们能够崛起。
《棉花帝国》是历史学家更广阔对话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在一个跨国家的,甚至是全球的空间框架里审视并重新思考历史。历史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与民族国家并肩出现,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学家从预设的国家视角出发,往往没有对跨越国家边界的联系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满足于可以从研究特定民族国家领土内的事件、人物和过程所得到的解释。本书则致力于更广泛地关注跨越政治边界的网络、身份认同和过程,来平衡历史研究的这些“国家”视角。

通过侧重棉花这一特别的商品,并追踪其种植、运输、融资、产品制造、销售和消费的过程的历史轨迹,我们能发现不同的人与不同的地方之间的联系,而如果我们从事的是更加传统的局限于国家边界的研究,这些联系将仍然处在边缘地位。本书不再关注特定事件的历史,比如美国内战;或特定地区的历史,如大阪的棉纺织厂;或特定人群的历史,如西印度群岛种植棉花的奴隶;或特定的历史进程,如农村耕种者向工业受薪工人的转化。本书以一种产品的传记为一扇窗,探究关于我们世界的历史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并重新解释一段影响至关重大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

我们即将踏上一段穿越人类五千年历史的旅程。在本书中,我们将通过关注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物——棉花——来揭开一个巨大的谜团:现代世界起源于何处?让我们先从一个位于今天墨西哥的小村庄开始我们的旅程,在这个与我们的世界迥异的世界中,棉花正在欣欣向荣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