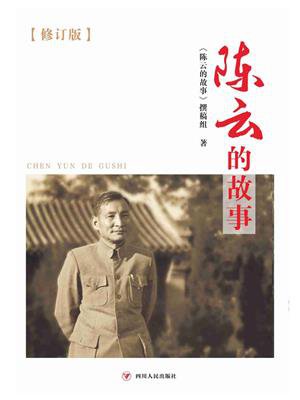“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一条名为“市河”、俗称“三里塘”的小河穿镇而过,河面时有扁舟荡过,孔孔石桥连接两岸,一派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与恬静。这里就是陈云的家乡。
对于家乡,陈云的感情是炙热的;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将小小的青浦练塘写进了整部党史。不过,陈云的童年并不美好。
陈云的父亲陈梅堂,母亲廖顺妹,还有一位大他8岁的姐姐陈星。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家庭一样,陈云的父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能借住在陈徐祠堂里,靠给人打工帮佣度日。1905年,陈云即将诞生的时候,族人认为生孩子“玷辱”祖宗,于是不再允许他们在祠堂居住。几经周折,陈梅堂最终在开米行的闵家租到两间简陋的小屋。6月13日,陈云就在这间小屋中降生了,小名阿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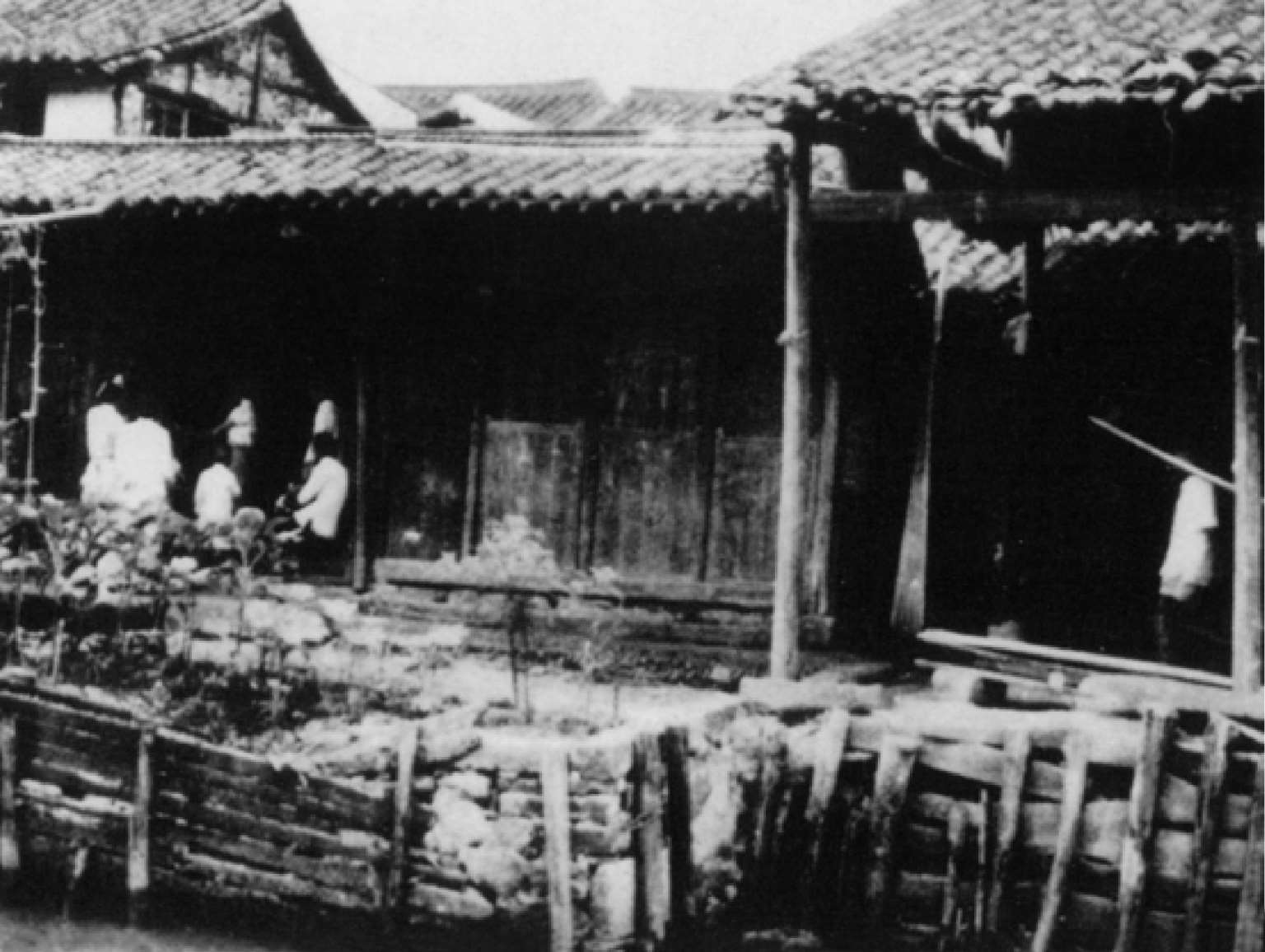
陈云故居
遗憾的是,幼子出生的喜悦未能持续太久。陈云出生不久,母亲就瘫痪在床,两岁时父亲因病溘然长逝,4岁时母亲也过世了。陈云和姐姐成了孤儿,只得靠外婆抚养。谁知两年后,外婆也一病不起。临终前,她叮嘱陈云的舅父廖文光,一定要把陈云姐弟抚养好。从4岁到14岁,是舅父母为陈云撑起了一片亲情的天空。6岁那年,廖文光将陈云立嗣为子,改名廖陈云。但陈云仍喊廖文光为舅父。
廖家家境贫苦,拮据度日。尽管如此,廖文光夫妇依然尽其所有抚养陈云姐弟。他们原来经营裁缝铺,后来因为生意清淡,改开小夜酒店,主要是晚上卖点心和小菜,供做生意和听评弹的人宵夜。陈云乖巧懂事,自幼就在店里帮工,做些劈柴、洗菜、淘米之类的杂活。
幼年孤苦的经历,养成了陈云内向、沉静、早熟的性格,但他还是一位聪颖少年,是读书的好材料。1913年,舅父母把他送进上塘街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陈云进入练塘镇贻善小学读三年级。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
陈云有出息,是舅父母在贫苦中的一丝欣慰。然而,陈云快乐的学习时光未能持续很久。
建成于2000年的上海陈云纪念馆也坐落于市河边,馆长徐建平介绍了当年的情况:
当时,因为陈云的舅舅没有孩子,所以他就把希望寄托在陈云身上了,花了家里的一些积蓄给陈云去念书,读了一年私塾,后来又读了两年小学。但当舅舅自己有了一个儿子后,就没有更多的钱去供陈云继续读书,所以陈云只有回到家里面帮着带他的表弟,要抱小孩,还要做家务,没办法再继续上学,他很渴望上学。
后来在一位亲戚的资助下,陈云进入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但一个月后,因为没钱再次辍学。然而,短短一个月,异常刻苦的陈云基本掌握了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账,这成为他受益终身的技能。
对于舅父母的养育之恩,陈云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并尽可能去报答。到上海工作后,陈云拿到第一份薪金,就带舅父母到杭州去玩了一次。他克勤克俭,把几乎全部工资寄给家里。对于这个脆弱的家庭来说,似乎最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随着陈云的成长,作为长子的他必将承担起照顾家庭的重任,舅父母也深深地信任着陈云。
但是,当陈云投身革命后,这一最初的愿望变得遥不可及。
1927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陈云被迫离职,回到家乡领导农民运动。舅父很为他担心,一再劝他:“生意没了可以再找一个,找到了生意后给你成一个家吧。”听了舅父这一番话,陈云心中如针刺一般。辗转反侧多日,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继续革命的征程。
陈云曾说,尽管他时刻未忘报答舅父母,但确实没有尽到长子的责任。离开家乡后,为了避免连累家人,他6年没有与家里通信,甚至1937年舅父过世时,陈云也不在身边。这些往事,每每触痛陈云的心弦。
徐建平说:“他的舅舅1939年去世,当时陈云在延安,他知道他舅舅去世的消息后也很悲痛。他说我是舅舅、舅妈带大的,所以他就托了当时在国统区的周恩来把在新疆时候省下来的两百块钱津贴寄到了上海,给他的舅舅来做丧葬费。”
子欲养而亲不待,其中的心路历程,如陈云后来所说:
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是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
“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启非不孝于其父也。”正是少年时期的磨难、舅父母的艰辛求生,使陈云很早就认识到:“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他把报答舅父母养育之恩的情感与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结合起来,投身于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从而使“小我”的恩情报答升华为“大爱”。
陈云兑现了他的诺言,倥偬戎马二十载,革命胜利,全国千百万家庭也迎来了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把舅母接到了北京。
徐建平馆长介绍:“后来他把舅妈接到了北京,给她养老送终,对他舅妈的感情也是很好。他不仅是个革命家,也是个孝子,对舅舅、舅妈的养育之恩他感觉到是要报答。”
“我出生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更是陈云晚年常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