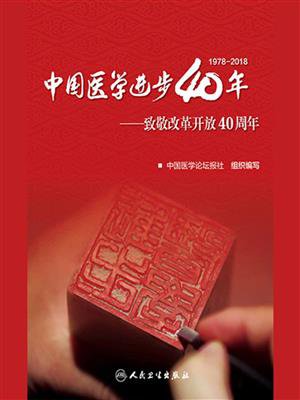王泰龄:奋斗70载的“90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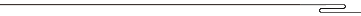
“放心吧,从细胞核的形态和细胞排列来看,这是横结肠管状腺瘤伴随轻度不典型的增生,是不会恶化的。”王泰龄耐心地跟一位前来询问病理结果的患者家属说。对王泰龄来说,这只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可对于病人而言,这是明确诊断,能重燃生的希望。
面前的这位“90后”,耳聪目明,腰板很直,声音爽朗,精神矍铄,至今已从事病理工作整整70年,现在仍每天坚持工作12小时,奋战在肝病病理会诊的第一线。今天,王泰龄饶有兴致地与我们分享了她如何与病理结缘,如何成长,以及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过程。

91岁高龄的王泰龄教授仍奋战在病理会诊一线
一、名家引路,精益修行
现在,91岁高龄的王泰龄仍保持着每天阅读文献的习惯,“和专业有关的得抓紧看,多看文献,就会知道天下之大”。这个习惯的养成与她学医的引路人刘世豪不无关系。
刘世豪教授(1900—1974年)是协和内分泌奠基人,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我的父母亲和刘教授一家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我年少时,我们两家在北戴河度假期间住在一个院里,我是早上9点去沙滩游泳,刘教授都是看书到10点半,才去海边。他连休假都带几箱书。那会儿,我觉得他言语不多,但就这个学习精神,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后来,我到北京读高中,平时住校,周末都住在他们家,刘教授对我选择医学的影响很深。”王泰龄情不自禁地说。
“1948年,我在协和医院做实习医生。开始我本来想搞外科,可是外科教授说,‘小祖宗,没有女孩搞外科的’,那我就想到妇产科,觉得能施展拳脚。妇产科林巧稚教授是我的老师,那时候,协和医院要求实习医生在做妇产科医生之前,都要先去病理科轮转一年,打好基础。林教授也特别重视病理,手术结束后都要和病理科医生一起阅片。后来在工作中,我越来越意识到,病理学是各临床学科发展的基础。刘世豪教授也建议我做病理。”
王泰龄自从到协和医院病理科以后,胡正详教授(我国病理学奠基人之一)给了她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胡教授让我认识到,医学就像一棵大树,树根是各基础医学,病理科就是树干,树枝就是内外妇儿等学科。病理科要把根的营养送到树叶,也要从树叶吸收营养,也就是说病理必须结合临床。”
王泰龄1950年毕业(此时已经在协和医院病理科做助教),那时的她非常自信,觉得已经有能力给学生上课了。有一次,胡正详让她给学生讲炎症。“我们的病理学课程都是胡教授亲自讲授的,我原原本本听了两遍,差不多都背下来了。胡教授问起备课情况时却严肃地问我:‘你看了几本书?’我说:‘上课的内容您都讲过了,我照着您讲还不行吗?’他说:‘不行,你去把这些文献全部看完。’这时候离上课还有二十多天,他让技术员推个小车陪我去图书馆,把当时相关的二十几本书全部借回来,要我把这些材料都看完才能讲课。”这个教训让王泰龄印象特别深刻:只有自己真正弄明白了,才能教别人。
跟随刘世豪、胡正详两位教授的学习经历,给王泰龄奠定了扎实的病理学基本功,养成了阅读专业期刊和文献的习惯,以及树立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到最好。最好的标准就是,严谨、认真、坚持,再把眼光放得高一点。
二、默默耕耘,驰骋微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国的病理学很落后,全国从事病理工作的还不到50人。许多院校想建立病理科,但苦于没有人。“胡教授就倡导:一是出书,二是积攒病理切片,还带领我们举办全国病理师资培训班。第一届高级师资班的学员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高年资的内外科临床医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的杰出病理学家。”

第一届高级师资班学员合影(第一排左起:佘铭鹏,刘永,胡正详,王德修,王泰龄)
王泰龄在长春工作期间(1953—1984年),除了留大体、切片标本,同时还开展尸检和临床病例讨论。她特别强调,对于认识疾病,尸检是非常重要的途径之一。“我记得,有一年一位北京医院住院期间的苏联专家突然死亡,为查明死因,胡教授带我去做尸检,结果发现是动脉瘤破裂引起的大出血。”
这段时间,是王泰龄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忆时,她声情并茂,兴致勃勃。“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愿意回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人心齐,目标明确,工作效率特别高,工作积极性也比现在年轻人高。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984年,王泰龄调任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主任,负责组建病理科。“八十年代,我受命负责全国的病理技术,中日友好医院率先在我国成功开展免疫组化技术,做免疫组化时将冰冻切片改为石蜡切片。后来,病理学会制作了一系列小册子,在全国范围内把这项技术开展起来。”1992年,她还和刘彤华、佘铭鹏、严庆汉四人受邀赴日参加首届中日病理学会。此后,中日友好医院病理科与日本女子大学、日本大学、千叶大学和金泽大学建立学术交流,联合培养研究生。
王泰龄特别珍惜时间,最让她高兴的,就是每天都能过得很充实,多做一些工作。她退休后,致力于肝病病理的临床和研究工作。自20世纪90年代,先后为我国《肝炎防治方案》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慢性肝炎病理分级分期标准,重型肝炎、脂肪肝及酒精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等病理诊断标准。

1984年中日友好医院正式开院,王泰龄教授为病理科首任主任
三、芥子须弥,显微流芳
“病理科大夫并不比临床医生高明,只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显微镜直接观察到病变,而临床医生要‘隔着肚皮’分析病情。我觉得最有兴趣的就是,从病理分析疾病的临床过程,帮助临床确诊。我习惯把患者病情发展过程列一个曲线,有助于分析病情变化。”
说到这儿,王泰龄向我们展示了1例刚整理好的会诊病历,里面有一页记录肝生化变化趋势的表格。这是1例肝移植术后的肝穿病理会诊,患者肝生化中多项指标反复升高,经过好几年也弄不清楚病因。王泰龄和她的学生梳理了患者移植术后(2004年)至今的肝生化指标变化特点以及影像学信息,再结合肝脏病理改变,最后发现肝内病变是门脉小支闭塞引起的肝实质缺血性坏死。”
“这就说明一点,病理必须结合临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王泰龄让我们看书架上摆放着的一个个厚厚的文件夹,“你们看,我保留了所有来我这会诊的病例切片和临床资料,目前是6900多份。我希望在最短时间内,尽快把我了解的各脏器病变规律,告诉年轻医生,为他们提供学习肝病病理的平台。”
改革开放40年里,我国病理学科发展很快,全国各大院校、地方院校也很重视病理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随着中国医疗覆盖面的越来越广,县一级的基层医院也必须有病理科,王泰龄觉得,病理科还需要更多的人才。“我国的病理发展与国外还是有差距,国内真正的前沿报道还是不多。实际上,咱们国家病种多,病人多,假如我们好好总结,我相信,几年以后应该是全球都看中国的资料。”讲到动情之处,她脸上露出了少女般的憧憬。
(作者:杨力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