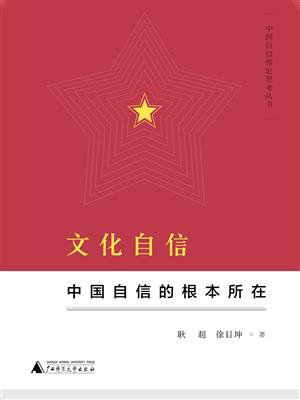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化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文化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理论没有作过完整、系统的论述,也没有直接阐述过“文化自信”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踏上历史舞台,就充满了文化自信。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就是大学者、大思想家,他们在与论敌的论战中,总能够占据上风、揭示真理。尽管当时无产阶级不占统治地位,革命队伍非常弱小,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言人、无产阶级精神领袖,展现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在不少马克思主义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文化观或者说文化哲学不断地被提及和阐述,这些关于文化的最基本的理论,展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自信,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源头,是我们系统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理论基础。
(一)揭示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社会,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诸多方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诸多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相互关系。辩证系统地梳理这些关系,能够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奠定外部关系分析的基础。
首先,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具有决定作用。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把作为完整社会系统的社会形态区分为三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部分——法律的和政治的以及社会意识形式即观念的,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文化”的概念,但是精神生活、社会意识形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化。“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在这里,马克思把作为完整社会系统的社会形态区分为三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又把上层建筑区分为两个部分——法律的和政治的以及社会意识形式即观念的,揭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虽然在这里没有提到“文化”的概念,但是精神生活、社会意识形式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化。“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或者说社会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物质交往是交往的最初形式,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作为社会的精神活动与思维方式的文化交往就出现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果划出文化发展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的东西,或者说社会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物质交往是交往的最初形式,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扩大,作为社会的精神活动与思维方式的文化交往就出现了。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如果划出文化发展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文化交往,产生于经济与政治交往的过程,一定主体的文化及文化自信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着一定的物质和实践基础。
。文化交往,产生于经济与政治交往的过程,一定主体的文化及文化自信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有着一定的物质和实践基础。
其次,作为上层建筑、精神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文化,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
 可以看出,社会意识对客观世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意识不仅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改造它。如果社会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就可以指导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加以改造。相反,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又为其提供动力与支持。生产力落后,文化缺乏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就难以谈得上先进。文化落后,生产力也就难以保持较好发展,甚至受破坏、走弯路。
可以看出,社会意识对客观世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有着巨大的反作用。社会意识不仅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而且能够改造它。如果社会意识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就可以指导人们通过实践能动地加以改造。相反,人们就会做出错误的行动,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文化发展以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为基础,同时又为其提供动力与支持。生产力落后,文化缺乏繁荣发展的物质基础,就难以谈得上先进。文化落后,生产力也就难以保持较好发展,甚至受破坏、走弯路。
再次,文化发展有它的相对独立性。在承认经济基础对文化的决定和制约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地位是最终意义和抽象意义上的。经济和政治对文化的最终决定意义并不能够否认在某些时期某些阶段文化的决定作用。文化绝不简单的就是经济和政治的派生物和附属品,文化发展有着相对的独立性。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恩格斯也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恩格斯也指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
 。拿这里恩格斯讲的德国来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详细分析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后提出: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与英法两国相比,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政治上,德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而在文化上,“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18、19世纪,德国先后涌现了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说,像这一时期的德国那样,虽然经济政治落后,但文化发展超前,这是其独特之处。认识到文化发展的超越性,我们就要走出庸俗唯生产力论的误区,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致力于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
。拿这里恩格斯讲的德国来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详细分析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后提出:在经济上,德国是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农业国家,与英法两国相比,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在政治上,德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而在文化上,“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在18、19世纪,德国先后涌现了像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产生了德国古典哲学。也就是说,像这一时期的德国那样,虽然经济政治落后,但文化发展超前,这是其独特之处。认识到文化发展的超越性,我们就要走出庸俗唯生产力论的误区,改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致力于推动文化的繁荣发展。
最后,文化观念与经济基础等因素对人类历史发展共同发挥作用,它们之间是有机统一、不容割裂的。恩格斯指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
 可以看出,在有机的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基础虽然居于主导,但是经济基础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它离不开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不是两个过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绝不是一种外在的、单向的、机械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的、派生的反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多维的、交互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
可以看出,在有机的社会系统中,各种要素都具有重要的地位,经济基础虽然居于主导,但是经济基础并不是独立地发挥作用,它离不开系统内部其他要素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的作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不是两个过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绝不是一种外在的、单向的、机械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也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的、派生的反作用;它们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多维的、交互的关系,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
(二)科学定位了文化发展的历史性和时代性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注重从社会结构中来分析和把握文化,也注重考察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时代条件。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
 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恩格斯也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
 可以看出,文化发展受到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制约,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背景,都不是空中楼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伴随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相应形成了五种文化形态。一定社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时,要注重考察它的具体社会经济形态,明确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推进文化建设时,就必须立足现有的时代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可以看出,文化发展受到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制约,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空背景,都不是空中楼阁。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伴随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相应形成了五种文化形态。一定社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影响和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时,要注重考察它的具体社会经济形态,明确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分析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随着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文化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不断推动社会进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推进文化建设时,就必须立足现有的时代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三)科学分析了“世界历史”趋势下的民族文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见,指出了世界文化的普遍交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历史将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趋势将逐步显现。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技术在加速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以铁路、轮船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将大大缩短印度等东方国度和西方之间的距离,将把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文化知识等,传送到所有经过的地方,依靠这种普遍交往的工具,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见,指出了世界文化的普遍交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必然结果,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历史将向世界历史转变,全球化趋势将逐步显现。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技术在加速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认为以铁路、轮船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将大大缩短印度等东方国度和西方之间的距离,将把西方国家的先进设备、文化知识等,传送到所有经过的地方,依靠这种普遍交往的工具,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也要看到,这种“世界的文学”,绝不是指单一的文学,绝不意味着各民族文化的消失,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全世界文化的统一。这种“世界的文学”,不排除有其“普遍”的成分,但更多指的是各民族文化摒弃狭隘、交相融合、互鉴互补,在进一步创新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它依然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化共同组成。西方文化不是唯一的标准,各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化,也没有一无是处的文化。任何以自身文化为标准去衡量其他文化,从而判断其他文化优劣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文化来源于实践,发展于交往。一种文化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要靠交往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
 ,只有在普遍交往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只有在普遍交往中保持应有的文化自信,“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
 。这说明,人的发展离不开交往实践,离不开对他人的学习与借鉴。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要继承和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如果一种文化拒斥“世界历史”,自我封闭而缺乏开放性和交往的积极态度,那它就没有比较和鉴别,就难以创新和发展。
。这说明,人的发展离不开交往实践,离不开对他人的学习与借鉴。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各民族的文化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要继承和弘扬自身民族文化,离不开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如果一种文化拒斥“世界历史”,自我封闭而缺乏开放性和交往的积极态度,那它就没有比较和鉴别,就难以创新和发展。
(四)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马克思晚年通过对东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特殊性的认识,指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方式具有多维性,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价值和意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途径具有多样性。在《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提出要注重分析印度古代社会土地公有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驳斥了关于所有原始公社建立形式同一的论调,阐明了人类文明模式、文化发展多元多样的思想。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同样是马克思晚年重大的文化理论成就。马克思提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
 。马克思认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道路,俄国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和波折。东方各国由于一直保持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可以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认为,并非所有国家都要走西欧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道路,俄国在各方面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可以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灾难和波折。东方各国由于一直保持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和专制国家等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可以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