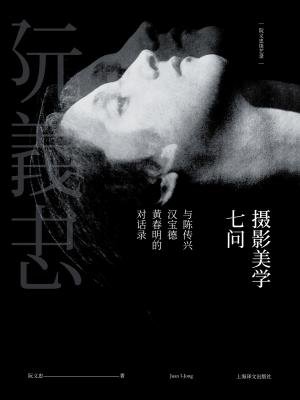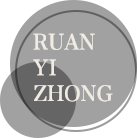
打开摄影在台湾的死结
阮义忠 :你离开台湾十年而甫一回来,对本土的摄影环境,有着什么最强的感受?
陈传兴 :普遍看来,从摄影家的表现形式来说,都显得很单薄;而由观赏者的立场来看,几乎都欠缺摄影史的观念。每一位创作者好像都想突破,大家都在尽量吸收资料。而看照片的人,都只从个人熟悉的背景及风格去接受影像。尽管这样,我还是对摄影在本地迅速普遍化与日渐专业的趋势深受刺激。不过,我对一个在域外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特殊现象,感到十分诧异而不可解:台湾的摄影家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沟通,不同风格的人几乎是互不往来的。而在其他地方,人文摄影和纯摄影的创作者,他们并没有把界线划分得那么明显的,大家是好朋友,互相刺激、互相吸收、互为借镜。因此影像的表现形式就显得十分丰富而多样……
阮 :这是不是台湾创作者表现形式会陷于单薄的病因?
陈 :我们的摄影家太急于把自己的风格固定下来,好像急于为自己的影像贴上一个标签一样,以便让大家靠标签去认识自己的风格;而贴上之后,又怕把它撕掉。
阮 :急于建立风格的努力,会造成什么缺失?
陈 :很容易把自己的创作潜能局限住了,而僵死在一个框框里,并且比较不容易容纳别种风格,“自动排除” [1] 了很多表现的可能性。
急于建立风格,也许在表现技巧上可能会有很快的突破,但一点也不能丰富自身的美感经验,到最后甚至会看不懂不是自己风格的影像。因此,有些风格极强的摄影家,就变得极端自我膨胀,其实这是没有信心的缘故;就本质来说,这种自我膨胀是不安和焦虑的病态现象。
阮 :如何才能打开这个死结?
陈 :大概可循的办法有三个:一,汲取外面的资讯;二,摄影家彼此互相沟通;三,摄影教育的普及化。
阮 :正确的摄影批评之建立是不是也该算上一份?
陈
:这倒是个大问题,台湾一直没有所谓的摄影影像批评。批评会不会出现,全赖创作本身的气候是否已经成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看:由社会经济层面来说,一定要让摄影普遍被大众所接受,承认它是一种视觉艺术;从知识层面来说,要建立台湾的摄影史,使摄影在本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清晰的脉络可循。有了这两点,气候才会形成,正确的批评才会出现。

[1]
自动排除(Forclusion):由Lacan所引进,在精神分析理论里这术语用来称呼一最基始的排斥行为,将某些不想见到的现象、事物以表征符号方式逐出象征秩序之外。此种行为经常会衍生出一些后遗效用,最极端的就是被逐出者以“幻象”方式(Hallucination)重返出现在现实世界对排斥主体构成威胁;此外尚有一些较间接性的和缓形式,如以“崇物主义”(Fétichisme)方式让排斥者成为一崇祭对象。在文化、社会层面我们也发现此种“自动排除”现象之存在,它附生在,举例来说,本土主义之夸大形式上,它将一些本土文化里(不可避免)的一些盲点、缺失改装成为一极端巨大之“崇物”(Fétiche),借此来回避。但究竟偶像之下也有阴影,崇祭之物也会对归教者造成威胁与不安。类似的情形在摄影创作行为里,那些一味迷信好相机、以为依赖较精确的机器就可有好作品的心理即是一种“科技崇拜”之现象,借用科技之象征秩序来弥补其创作想象行为之贫乏。
参见“Forclusion”条例在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J. Laplanche, J. B. Pontalis. 6e édition. PUF Press, 1978),页163—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