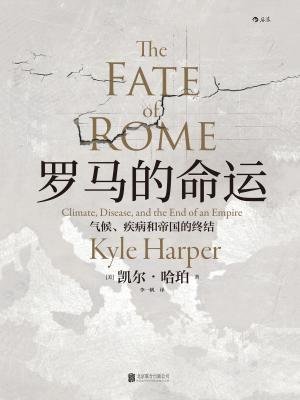伟大的医生与伟大的城市
帕加马的医生盖伦(Galen)出生于129年9月,哈德良(Hadrian)皇帝统治时期。盖伦虽然不是上流社会出身,但属于“上层中产阶级”,对于这个阶层的人来说,帝国意味着繁荣和机遇。盖伦的出生地帕加马坐落于距爱琴海不远的内陆,小亚细亚的群山之中,是那种在罗马统治下繁荣的城镇,也是培养盖伦这种医学奇才的福地。帕加马是希腊传统的重镇,让盖伦接触到丰富的希腊医学文献,包括庞大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帕加马有一座为治愈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阿波罗的儿子,他的权杖被一条蛇缠绕,是医学最著名的符号)修建的著名神殿,是疾病康复者的灯塔。在盖伦的时代,这座神殿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了,并且正处于它最辉煌的时代。“所有亚洲人”蜂拥而至,并且就在盖伦出生的五年前,哈德良本人也亲自造访了神殿。

在帕加马,盖伦的天才为他赢得了受人尊敬的角斗士医生的职位。但帝国的和平为盖伦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他游历了地中海东部,穿越了塞浦路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四处搜寻当地的药物和疗法。他还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学习过,在那里,看到真实人类骨骼的机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里的医生在给学生讲授骨骼学时采用了直观演示的方法。即使没有其他原因,只为了这个,也要来拜访亚历山大里亚。”在医学技艺上,罗马帝国在各个方面都为盖伦提供了非比寻常的丰富经验。一个拥有惊人天赋的人必然会忍不住要到伟大的首都去试试运气。

盖伦在162年来到罗马,这是皇帝马可·奥勒留和皇帝卢修斯·韦鲁斯(Lucius Verus)共同统治的第一年。盖伦喜欢引用一句话:“罗马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希波克拉底(活跃于前400年前后)从没见过的罕见疾病,对盖伦来说却是家常便饭,“因为罗马城里的人是如此之多”。“每天可以发现一万人患有黄疸,一万人患有水肿。”这个大都会是人类苦难的实验室,对于像盖伦这样有抱负的智者来说,也是一座大舞台。他的事业发展得极快。

来到罗马后不久,他治好了一位哲学家的发烧,“尽管曾被嘲笑”,因为他在冬天“想要治好一个老人”;他因此声名鹊起。一位名叫弗拉维乌斯·波提乌斯(Flavius Boethus)的叙利亚人,曾做过代表帝国最高荣誉的执政官,他热衷于观看盖伦“演示声音和呼吸是如何产生的”。盖伦对于视觉盛宴有很高的品味,在罗马人面前活体解剖了一头猪,用大师的手法,通过阻断神经来开启和关闭猪的喊叫,让他的观众看得如痴如醉。盖伦治好了波提乌斯患重病的儿子和妻子;这位有权势的人给了盖伦一小笔财富,更重要的是,成了盖伦的保护人。从此,盖伦进入了上流社会。一个个轰动一时的成功接踵而至。一位著名作家的奴隶受了伤,在肋骨下形成了致命的脓肿。在手术中,盖伦切除了受感染的组织,使跳动的心脏暴露在视线中;虽然盖伦自己也颇为悲观,但这个奴隶活了下来。

30多岁的时候,盖伦就成了一个活的传奇。“伟大就是盖伦的名字。”

然而,这一切都没能让盖伦为我们称为安东尼瘟疫的死亡事件做好准备。166年,也就是盖伦在首都的第四年,东部的瘟疫开始向这里蔓延。流行病在罗马并不罕见。起初,发烧和呕吐的浪潮似乎只是季节性死亡又一次熟悉而可怕的发作。但很快人们就会发现,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在他的杰作《医学方法》中,盖伦生动地描述了他在“这场疾病刚刚发生时”,治疗一个被感染的年轻人的过程。轻微的咳嗽开始加剧,病人从喉咙里溃疡的地方吐出暗色的结痂。很快,疾病的典型症状出现了:黑色皮疹将患者的身体从头到脚包裹起来。盖伦认为有一些疗法可以削弱这种疾病的力量,但这份名单只是纯粹绝望的尝试记录:高地牛的牛奶、亚美尼亚的泥土,还有男童的尿液。他所经历的死亡事件不仅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传染病,也是罗马帝国历史上的一次断裂。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阿波罗神实施的一种新的黑暗惩罚。但对科学家盖伦来说,这就是“大瘟疫”。

这一章的目的是审视从盖伦的成长时期,到大规模流行病降临之前的罗马帝国。吉本认为,这段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最繁荣”的时代。当然,这份赞美中不乏对罗马世界大师的仰慕。但是,将2世纪中叶称为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并不是一个武断的或是出于美学的判断。在物质方面,罗马帝国为令人惊叹的全盛期奠定了基础,这段全盛期是历史中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协力推动社会发展的时期之一。帝国本身既是这种发展浪潮的前提,同时也以其为基础。帝国的政治框架与其社会机制是相互依存的。
与此同时,我们将强调,“罗马治下的和平”从来都不是没有阻力的统治成果;衡量帝国实力的标准不在于是否缺少限制和挑战,而在于帝国是否拥有对抗挑战和压力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更有必要找出安东尼时代时常被看作是历史转折的原因。传统的答案提及边境之外更强大的敌人,还有不断上升的财政-政治矛盾,这些都是原因,但还不够。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罗马的全盛期出现于一段不稳定且短暂的有利气候时期。更重要的是,帝国的结构为一种新出现传染病的到来提供了生态条件,这种疾病拥有史无前例的暴虐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帝国的历史轨迹被自然力量从外部改变了方向。当然,我们不必相信如果没有这些干扰,帝国就能永世长存。但帝国经历的特殊命运与气候最优期的结束和大规模流行病的冲击是密不可分的。在关于罗马命运的所有论述中,它们都占有稳固而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