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实主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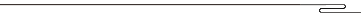
在一个现实主义世界里,竞争、和平、发展是具有根本性的国际政治问题,国际领导力因而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管控竞争、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现实主义世界里的国家间竞争归根结底是安全竞争。安全竞争实乃国际关系的常态,这是主流现实主义的观点。什么是安全竞争?因为安全竞争已被视为国际政治中的常识,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多余,给出清晰回答的学者当然也不多。有学者认为,竞争就是“可能导致军备竞赛和联盟形成的单边军事力量建设(military buildups)”。
[1]
然而,这个界定的“单边色彩”过于浓厚,无法准确反映竞争作为一种双边或多边互动模式的基本性质。因此,安全竞争可定义为:国与国之间在国际关系中为满足基本的安全需要或谋求安全优势而形成的一种双边或多边关系模式。从战略选择看,安全竞争的基本战略包括内部军力建设、外部结盟借力和普遍军备裁控。从竞争态势和结果看,安全竞争既可能长期保持和平,也可能导致战争灾难。战争的发生可以归结为三种“失败”:威慑战略的失败、国家对安全竞争管理的失败、自我克制的失败。其结果,国际关系史总是在战争与和平的相互交替中前行。战争是和平的中断,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伤害最大、最可憎恶的国际政治现象。但战争并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而是人类工具理性的表现之一,是实现特定目的的高成本手段。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战争是“一种迫使我们的对手来满足我们的意愿的暴力行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行为,更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的继续,是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的政治”。
 因此,围绕和平与发展的宗旨,行之有效地管控安全竞争、防止战争暴力是现实主义世界里国际领导力的根本要求和终极价值。
因此,围绕和平与发展的宗旨,行之有效地管控安全竞争、防止战争暴力是现实主义世界里国际领导力的根本要求和终极价值。
1.战争与和平原因分析:政治家的反思
和平和战争是安全竞争的基本表现。和平是常态的安全竞争,战争是恶变的安全竞争。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寻求和平的安全环境就必须厘清战争的根源。许多从事对外政策实际工作的政治家对战争原因进行了理论性的反思。这里以艾森豪威尔和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为例进行阐述。
作为战后美国唯一战功赫赫的将军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战争的痛苦有着无出其右的亲身体验,因而他对战争原因的思考也是深刻的、有说服力的。艾森豪威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曾以它的痛苦和破坏造就了著名的胜利和著名的人物,它虽暂时解决了国际争端,但从未以公平和正义来保障和平。战争是愚蠢的、残酷的、昂贵的。然而战争一直连绵不断。各国在自卫的名义下付出了人的代价,并且在恐惧与竞争的促使下继续承受着规模越来越大和花费越来越多的军备负担”。战争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总结了如下三点:第一,强国的霸道激起反抗,譬如罗马帝国和拿破仑法国。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当军事机器发展到这样巨大的规模或可怕的程度以至使一些拥有它们的强国变得狂妄自大时,这些强国常常由于横行霸道而迫使别的国家在绝望或完全无望之余诉诸武力。”第二,通过战争寻求本国军事野心的经济支撑,譬如日本帝国。艾森豪威尔说,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野心需要如此巨大的费用,以致国民经济无法继续负担;于是政治领袖就求助于战争,希望借战争来补偿本国的损失。”第三,战争的根源在于政府,而非人民。艾森豪威尔说,战争问题的答案“不应到各国人民中间(除了被故意引入歧途者外)去找,而是要到各国政府(特别是其哲学是从根本上敌视别国、其目标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的政府)的盲目狂妄自大和相互冲突的野心中去找。”

威廉·富布赖特是美国最出色的擅长外交事务的政治家之一,曾长期(1959—1974)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号称“国会山的首席智者”, [2] 约翰·肯尼迪当选后曾有意邀请他出任国务卿,因为他是身边“最能干的人”。 [3] 美国著名的“富布赖特项目”便是他发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权力的傲慢》一书是富布赖特作为一个从事对外政策实际工作的政治家对战争原因的深刻反思,他的基本理论逻辑可概括为:权力的傲慢导致大国战争。富布赖特写道,“对大国战争历史的反思越多,我越倾向于认为领土、市场、资源、保护和维护基本原则等被作为这些战争原因的因素不过是某种深层次的人性力量的解释或借口,而不是根本原因”,他把这种深层次的人性力量称之为“权力的傲慢”,即那种各国都有的“一种证明自己比别的国家更大、更好、更强的心理需要”。 [4] 富布赖特认为,1870年的普法战争、1898年的美西战争、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战争,无论其表面原因是西班牙王位的继承问题,抑或是将古巴从西班牙暴政之下解放出来的努力,还是奥地利王储被刺事件,其深层原因无一不是“权力的傲慢”。譬如,1870年普法战争的原因从表面看是两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夺,但战争的“根本原因”显然是法国对德国统一的抵触。战争的结果是:第一,德国如愿以偿,完成了统一;第二,法国惨遭羞辱,失去了阿尔萨斯—洛林;第三,德国崛起为欧洲头号大国。富布赖特认为,德国的统一是“可以不通过战争方式”来完成的,但德国崛起为欧洲头号大国却“只能通过战争实现”。因而,普法战争的深层原因不过就是“德国人要打倒那些趾高气扬的法国人,为在柏林树立一个新的纪念碑找个有力的借口”。 [5] 富布赖特对此的哲学反思是,“战争的原因与后果更多地是因为病态而不是因为政治,更多地是因为傲慢与痛苦的非理性压力而不是因为优势和收益的理性算计。” [6]
富布赖特用一个在华盛顿流传的故事来佐证他自己对人性在大国战争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的观点。这个故事说的是五角大楼的军方知识分子曾做了一个实验,将1914年夏天的若干事件赋值编成数据输入计算机,计算机经过计算和分析后向实验者报告“不存在战争危险”。富布赖特认为,这个故事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计算机比人更理性;第二,人类冲突和国家权力动机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出于经济需求,也不是因为历史的驱动,不是由于均势的作用,而在于人类头脑中常怀的期望与恐惧。 [7]
2.大国战争的起源:理论家的分析
华尔兹曾在其极受推崇的经典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明确指出,“要阐明如何才更易于实现和平,就需要了解战争的根源。”
 美国学者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也曾在颇有影响的《战争探源》一书中论及战争逻辑与和平逻辑的相通性。他指出,“从逻辑上看,战争的根源与和平的根源必然是相互吻合的。一个不能充分解释欧洲为何享有和平的理论也必然不能充分解释欧洲为何处于战争。对战争的科学分析反过来也是对和平的科学分析。”
[8]
同理,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对和平环境的研判也就相当于分析国家安全环境。
美国学者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也曾在颇有影响的《战争探源》一书中论及战争逻辑与和平逻辑的相通性。他指出,“从逻辑上看,战争的根源与和平的根源必然是相互吻合的。一个不能充分解释欧洲为何享有和平的理论也必然不能充分解释欧洲为何处于战争。对战争的科学分析反过来也是对和平的科学分析。”
[8]
同理,对战争原因的分析、对和平环境的研判也就相当于分析国家安全环境。
从理论层面上看,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相关文献让人应接不暇。但总的来说,正如华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中的经典分析,这些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种层次的分析:一是从人性进行探讨,是为第一意象,认为战争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人性和人类行为,自私、误导性的进攻欲、愚蠢是战争的首要根源,其他原因都是次要的,因此“要消除战争就必须启发和提高人类的良知,或保证其社会心理的再调整”。二是从国家制度进行探究,是为第二意象,认为“国家内部机制是理解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好的国家热爱和平,而坏的国家热衷战争,对外战争有助于那些陷入内部矛盾和动荡的国家维护国内的团结和稳定,因此消除战争的根本方法便在于改造那些好战的坏家伙;三是从国际体系进行分析,是为第三意象,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战争的第一位原因,用卢梭的话说,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制止它。国家之间就像人之间一样,不存在利益的自动调节。由于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构,就可能经常要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 [9] 根据华尔兹的这种层次分析,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理论是经典的第一意象分析;民主和平论、独裁和平论 [10] 是典型的第二意向分析理论;华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温特的建构主义都是第三意象的分析理论。
大国战争是有大国卷入发生的国际战争,是国际关系中最具颠覆性的暴力现象。什么是大国?米尔斯海默从物质实力界定大国是比较科学的角度,他认为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相对军事能力,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必须拥有足够的军事资源以承担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展开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2)它不必拥有挫败领导大国的能力,但它必须有相当大的希望把冲突转变为一场使支配大国遭到严重削弱的消耗战,即便该支配大国最终赢得战争;(3)在核时代,必须拥有从核攻击中生存下来的核威慑力和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当然,“如果一个国家获得了超过所有对手的核优势,它就将强大到成为体系中唯一的大国。如果出现一个核霸权,则常规力量平衡大体上就无甚意义了。”但米尔斯海默拒绝承认唯一核大国和核霸权存在的现实可能性。 [11]
大国战争的根源是什么?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对大国战争的主要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偏好,历史学家们倾向于揭示不同战争的个性解释,他们怀疑政治学家们使用的“系统分析”方法,认为这是“人为地把复杂纷繁的事实简单化”;而政治学家们则更喜欢寻找不同战争背后的共性根源,质疑历史学家们“苦心研究现象性的东西是否有意义”。
 譬如,根据戴尔·科普兰的归纳,历史学家们往往认为,“汉尼拔(Hannibal)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于公元前218年攻占了罗马;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引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拿破仑(Napoleon)在欧洲恣意横行折射出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欲望;那些卷入1914年世界大战的国家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担心;而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希特勒(Hitler)的个性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譬如,根据戴尔·科普兰的归纳,历史学家们往往认为,“汉尼拔(Hannibal)的复仇心理驱使他于公元前218年攻占了罗马;新教与天主教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引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拿破仑(Napoleon)在欧洲恣意横行折射出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权力欲望;那些卷入1914年世界大战的国家是出于对竞争对手先发制人的担心;而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希特勒(Hitler)的个性则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又如,霍尔斯蒂指出,“路易十四自青年时期就把战争视为可替代打猎的取乐方式,弗里德里希大帝则把战争视同一种获取个人名誉和荣耀的工具,而内维尔·张伯伦则把战争归为一种外交失败和道德沦丧的结果。”
又如,霍尔斯蒂指出,“路易十四自青年时期就把战争视为可替代打猎的取乐方式,弗里德里希大帝则把战争视同一种获取个人名誉和荣耀的工具,而内维尔·张伯伦则把战争归为一种外交失败和道德沦丧的结果。”

政治学家们与历史学家的分析路径完全不同,他们更愿意从若干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中去发现规律,提炼共性,进而建构一种抽象的理论解释。有学者倾向于从民族主义或其他国内政治考虑等非安全和非结构因素出发去寻找战争的根源。譬如戴维·凯泽(David Kaiser)在其颇有见地的著作《政治与战争:从腓力二世到希特勒的欧洲冲突》中并不认同欧洲的大战都是为了反对某一个企图征服欧洲大陆从而建立大陆霸权甚或世界霸权的主流正统观点。凯泽提出,欧洲历次大战的根源不在于大国均势的变迁,而在于欧洲政治体制的演变。他认为,“欧洲各个时期的全面战争(general war)都源自特定的具体的政治发展:16世纪末17世纪初对贵族权势的失控;17世纪末君主制的巩固;18世纪末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新理性主义精神;20世纪孪生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权力。” [12]
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分支试图对大国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各自的回答。古典现实主义对大国战争进行解释的理论内核是基于人性的均势和平理论,强调大国实力对比的大致平衡是和平的基本保障,认为如果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压倒性的力量优势,那么国际体系就是和平的。如果要慑止进攻并维护稳定的均势,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急剧增长的实力都必须受到必要的对抗力量的反制,由于权力平衡带来了进攻后果的不确定性,使各方在发动主动攻击时会三思后行,这往往使战争最终得以避免。 [13] 相反,当体系中的一个国家试图通过扩张实现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即一个潜在霸主出现时,均势机制就会启动,导向大国战争,防止霸权追求者如愿以偿。
霸权稳定论的大国战争理论是与古典现实主义的均势和平论相反的理论,认为霸权国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是大战的根源,崛起大国往往是大国战争的发动者。罗伯特·吉尔平写道,“那些从变革社会体系中受益最大、并有实力促成这种变革的行为体会寻求变革体系,以增进自身的利益。变革之后的体系反映的是新的权力分配态势,服务于新的支配性成员的利益。”
[14]
简言之,霸权稳定论的大国战争逻辑是,“那些正在崛起而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会采取攻势,以获得为原有秩序所不容的地位和利益”。
 显然,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关系历史上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往往是某一国享有权力优势的结果。比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和平被归因于英国的霸权优势,而二战后的“长久和平”则被视为与美国拥有的支配性实力密不可分。
[15]
显然,在霸权稳定论者看来,国际关系历史上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往往是某一国享有权力优势的结果。比如,1815年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和平被归因于英国的霸权优势,而二战后的“长久和平”则被视为与美国拥有的支配性实力密不可分。
[15]
与“均势和平论”和“霸权稳定论”的理论主张不同,“权力转移论”认为,大国战争的根源主要在于崛起大国对支配性大国在权力上的逼近和超越,现状大国在与崛起大国竞争时的相对权力损失以及由此而来的二者实力地位的趋近程度是竞争是否会演变为恶性并最终升级为冲突乃至全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权力转移论”的核心观点是,“权力的转移,尤其是支配性大国的变更,是导致大国战争的深层机制。”
[16]
也有国内学者认为“权力转移论”实质上应为“实力转变论”,包括两大转变,一是“挑战国实力从弱到强的转变”,二是“挑战国和主导国相对实力的转变”。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国际社会中对既有国际秩序不满的大国,“通过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变革,逐步缩小与主导国家的实力差距乃至双方实力大体持平,从而对战争成本—收益的考量发生变化,很有可能发动战争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国战争理论继承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主张,强调试图利用权力上升优势而实现均势现状之利己改变的努力必然遭到有力的反制。结构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均势和平论的发展在于,它认为大国战争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格局的极化特征,其基本理论主张是,两极体系是稳定的,华尔兹说,“成对——两个公司、两个政党、两个配偶——的稳定性是得到充分检验的”。 [17] 多极体系相对于两极具有更大的不稳定性。 [18] 在华尔兹的理论里,国际权力分配一般表现出“两极”或“多极”的特征。华尔兹以演绎的方式论证了两极权力结构比多极权力结构稳定的结论。华尔兹认为,大国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里的不同均势行为是导致二者稳定性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两极体系里,“两个大国展开竞争,均势失衡只能通过两国的内部努力才能得到纠正。”然而,在多极体系里,“变换结盟关系提供了纠正(均势失衡)的额外手段,增加了体系的灵活性。” [19] 在华尔兹那里,“内部制衡比外部制衡更为可靠,更为准确。国家误判自身相对实力的可能性比误判对立阵营的实力和可靠性的可能性要小。不确定性和误算非但不能使国家适当地警惕并促进和平的机会,反而会导致战争。在两极世界里,不确定性减少,而计算也更容易做出。”因此,制衡的有效和不确定性的减少是两极稳定的主要要素。使两极世界稳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在军事上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深,非领导大国脱离或加入某一个阵营所带来的影响根本不足以造成权力对比关系的震动或倾斜。华尔兹举例说,在美苏对抗的体系里,法国从北约撤出军事力量、美苏先后“失去中国”都没有对当时的大国权力对比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华尔兹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与各自阵营里的其他成员国之间总体权力的巨大差距使中小国家之间的任何力量重组都“意义不大”。 [20]
相反,多极世界具有外部制衡的低效、误判误算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军事相互依赖也远较两极世界深刻等三大特征,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作用是多极体系稳定性相对较差的根本原因。华尔兹说,在多极体系里,“权力政治依赖于外交,联盟通过外交而得以构筑、维护和打破。结盟的灵活性既意味着一国存心拉拢的国家可能偏好别的追求者,也意味着一国眼下的盟友可能背叛。”于是,“结盟的灵活性限制了一国的政策选择。其战略务必讨好一个潜在的盟友,或满足一个现在的盟友。” [21] 从这个意义上说,结盟关系对多极体系中的力量对比态势影响很大,“在多极体系中,大国太多,使任何大国都难以确定清晰而固定的敌友界线;大国又太少,难以使背叛的影响无足轻重。” [22]
戴尔·科普兰在糅合古典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的大国战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动态差异理论”。他认为,国际格局的极化特征和大国的兴衰对比是大战起源的主要决定因素。科普兰指出,“无论正在衰退的国家是否采取可能导致大战的行动,极性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多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必须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才能考虑冒险发动大战。
在两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无论在军事力量上优于还是仅仅相当于正在崛起的国家,都有可能发动大战或以发动这种大战相威胁,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两次柏林危机就是如此。”

作为一名结构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也将大国战争的根源归结为国际结构的极化特征,他说,“单独专注于结构便可以告诉我们有关大国战争起源的大量知识。” [23] 在他看来,建立在大国间实力分配基础上的国际格局与全球性、区域性国际安全环境的基本特征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格局决定了各个国家的活动背景和政策空间,是国家权力战略规划和设计必须考虑的首要制约条件。尽管自由主义者往往把冷战后欧洲和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归因于地区一体化、民主化,或是和平战略文化取代了军事主义战略文化,但米尔斯海默认为,两个地区的国际权力结构处于良性平衡状态才是最主要的原因。米尔斯海默指出,“当前欧亚的和平与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有利的权力分配基础之上的,从而大大减小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24] 米尔斯海默认为,大国间相对权力的分配态势是大国考虑采取暴力权力战略还是非暴力权力战略的决定性因素。在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中,尽管国家总是持有相对实力最大化的动机,但它们并不是没头没脑的盲目进攻者,相反,按照国家具有战略理性的假定,国家总是会认真仔细地掂量进攻的风险,并考虑其竞争对手的实力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只有当其认为预期收益将会超过所付代价时,它们才会诉诸特定的权力进攻战略(如战争),以服务于权力—安全最大化的目标。倘若成本过高,则国家会静观其变,等待更为有利的出手时机。 [25] 因此,大国的进攻性意图常有,而进攻性行动却不常有,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并不拥有发动进攻性行动的实力”, [26] 陷入一种“眼高手低”的困局。
尽管米尔斯海默承认“无政府状态无疑是大国战争的一种深层原因”, [27] 但无政府状态和战争的发生之间存在实际上的不一致性,这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本身不能解释为何安全竞争有时会导致战争,但有时又不会。” [28] 因此,还必须找到其他起作用的结构变量。在米尔斯海默和许多其他结构现实主义者看来,体系中主要国家的数目及其相对权力分配态势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体系中的大国数量决定了体系的极化结构,它们之间的相对权力分配决定了这些结构的平衡程度。根据大国数目和大国间权力分配的平衡态势,米尔斯海默将国际权力结构定义为三种:两极、平衡的多极和失衡的多极。两极体系指“由两个拥有大致相等实力的大国所领导的体系,或者至少没有一个大国比另一个拥有更具决定性的强大力量”。而失衡的多极体系指“体系由三个或更多的大国所支配,其中之一是潜在的霸主”。平衡的多极体系“由三个或更多的大国所支配,但没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霸主;相反,权力在大国间相当平衡地分配,或至少是在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国间相当平衡地分配。” [29]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分析,在两极权力结构下, [30] 权力在相互竞争的两个大国之间大致平衡地分配,二者都不可能奉行霸权战略以谋求建立全球或地区霸权,任何谋取霸权的努力都将不可避免的遭到对方强有力的抵制,并最终被挫败。在这种战略态势下,双方都更可能采取更为间接的方式去削弱对手,如通过讹诈而从中小国家那里得到特权,或通过沉重的军备竞赛来拖垮对手,或千方百计使对手陷入与中小国家的长期战争而难以抽身,耗费权力资源。在平衡的多极体系中,推诿思维普遍存在,国家谋权战略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比如有可能针对中小国家或虚弱的邻近大国采取有限或代理人战争的战略。在失衡的多极体系中,巨大的权力优势给头号强国带来了进一步谋求霸权地位的冲动与信心。于是,霸权战争似乎是潜在霸主相当可行的战略选择。不过,潜在霸主谋求地区霸权的努力必然遭到其他大国的联合钳制,因此它必须与其面对的所有对手作战(最好是各个击破)方能确立霸权地位。当然,倘若一个大国具有核垄断地位,则核讹诈也是可有的霸权战略选择。
总起来看,两极结构最稳定,平衡的多极结构比较稳定,失衡的多极结构最不稳定,大国战争的风险最大。 [31] 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分析,两极世界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1)较少的大国冲突配对,两极体系中的大国战争往往不是两个对峙大国的直接冲突,而是其中之一与中小国家之间的战争;(2)大国间实力分配的平衡是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双方都清楚自己不可能在战争中彻底击败对手;(3)两极体系抑制误算,减少了大战的可能性;(4)两极体系产生的战略恐惧往往由两个超级大国承担,恐惧的扩散性不强。平衡的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可能导致战争,其基本逻辑包括四点:第一,大国数量的增加导致更多的大国冲突组合;第二,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导致大国间权力分配失衡的可能性比两极体系较大,优势大国因为其相对实力优势而对赢得战争胜利的预期较高,威慑战略不如两极体系有效,从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较大;第三,由于没有明显的反对者,大国可能结伙压制第三方、强制或征服中小国家的可能性较大;第四,因误算导致的战争可能性较大。失衡的多极体系是包括一个潜在霸主的国际格局,是最不稳定的一种实力分配结构。因为这种权力结构除了包括平衡的多极体系所具有的四大战争可能性之外,它还面临着严重的权力失衡问题,潜在霸主既拥有制造乱子的实力,也会在大国间造成严重的恐惧,这无疑会增大战争的可能,这种战争还可能卷入体系中的所有大国,导致体系层次的全面战争的爆发。 [32]
米尔斯海默将1792—1990的200年欧洲大国关系历史做如下的分期 [33] 来支撑自己的“权力结构—大国战争”理论:拿破仑时期,1793—1815(22年),失衡的多极体系,法国谋霸的拿破仑战争;19世纪,1815—1902(88年),平衡的多极体系,比较稳定;威廉德国时期,1903—1918(16年),失衡的多极体系,德国谋霸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两次大战之间,1919—1938(20年),平衡的多极体系,比较稳定;纳粹时期,1939—1945(6年),失衡的多极体系,德国谋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期,1945—1990(46年),两极体系,稳定。根据米尔斯海默的研究,在平衡的多极体系中,共发生了14次大国战争,战争时间约20年,战争的时间频度为18.3%;在失衡的多极体系中,共发生了9次大国战争,持续约35年,战争的时间频度为79.5%;而在两极体系中,只发生了一次大国针对小国的战争,即苏联1956年对匈牙利的用兵行动,战争的时间频度为2.2%。 [34] 米尔斯海默的分析似乎很好地支持了其“权力结构—大国战争”理论。当然,米尔斯海默对案例的分析和对史料的运用也不时遭到其他学者的批评,认为他“过于剪裁历史以支持其理论观点。” [35]
[1]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3 (Winter 1994/95), p.51.
[2]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 Random House, 1972, p.68.
[3]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 p.29.
[4]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6, p.5.
[5]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 p.6.
[6]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 p.7.
[7] J. William Fulbright, The Arrogance of Power , pp.7-8.
[8] Geoffre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 New York: Free Press, 3rd edition, 1988, p.3.
[9]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引文分别见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第14、69页,本段中卢梭的观点亦转引自该书第163页。
[10] 民主和平论是国际关系学界耳熟能详的理论学说,但独裁和平论则几乎没有在国际关系理论之湖中泛起引人注目的涟漪。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指出了独裁和平的理论逻辑。参见Mark Peceny, Caroline C. Beer with Shannon Sanchez-Terry, “Dictatori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96(2002), No. 1, pp.15-26.
[1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5.
[12] David Kaiser, Politics and War: European Conflict from Philip II to Hitler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reface.
[13] Edward Gulick, Europe ’ 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5.
[1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9.
[15] Indra de Soysa, John R. Oneal, Yong-Hee Park, “Testing Power-Transition Theory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National Capabilit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1,No. 4, 1997, p.511.
[16] Henk Houweling, Jan G. Siccama, “Power Transitions as a Cause of War”, The Journal of Con flict Resolutio , Vol. 32, No. 1, 1988, pp.87-88.
[17]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161.
[1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hapter 8.
[19]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163.
[2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169.
[21]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165.
[22]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p.168.
[2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335.
[2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Pacifier”, Foreign Affairs , September/October 2001,p.47.
[25]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p.37-38.
[2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415, note 14.
[2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334.
[28]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334.
[29]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p.269-270, pp.337-338.
[30] 哈理森·瓦格纳(R. Harrison Wagner )在一篇专门探讨两极问题的文章中认为,仅仅用两极理论来解释冷战中的国家行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R. Harrison Wagner, “What was B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47, No.1, 1993, pp.77-106.
[3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44.
[32] 米尔斯海默关于国际格局与大国战争的分析,请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p.334-347.
[33]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348.
[3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p.357.
[35] Sean Lynn-Jones, “Book Reviews on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8, No.2, 2002, p.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