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新古典现实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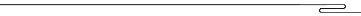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理论家族的重要成员,
 代表性学者包括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施韦勒(Randell L. Schweller)等。
[1]
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彼此分立是华尔兹的重要观点,
代表性学者包括沃尔福斯(William C. Wohlforth)、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施韦勒(Randell L. Schweller)等。
[1]
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彼此分立是华尔兹的重要观点,
 但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结构现实主义追求理论的简约美虽无可厚非,却导致了对外交政策的解释力不足,他们试图以国内政治为基底建构外交政策理论,主张将外部的体系变量和国内政治变量结合起来,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思想进行体系化的更新和改造,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外交政策的视野和抱负首先受制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即受制于其物质性相对实力”,但“这种体系压力必然通过若干单元层次的干预变量才能起作用”,这便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共性。
[2]
基于这种共性,特定国家的大战略、对国际影响的追求、对均势的认知、对威胁的反应等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核心研究问题,权力认知、国内动员、政府权力、精英政治等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干预变量,其变量关系是:国家间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内约束与精英认知(干预变量)→外交政策(因变量)。
[3]
但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结构现实主义追求理论的简约美虽无可厚非,却导致了对外交政策的解释力不足,他们试图以国内政治为基底建构外交政策理论,主张将外部的体系变量和国内政治变量结合起来,对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思想进行体系化的更新和改造,其核心主张是“国家外交政策的视野和抱负首先受制于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即受制于其物质性相对实力”,但“这种体系压力必然通过若干单元层次的干预变量才能起作用”,这便是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共性。
[2]
基于这种共性,特定国家的大战略、对国际影响的追求、对均势的认知、对威胁的反应等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核心研究问题,权力认知、国内动员、政府权力、精英政治等成为他们研究的主要干预变量,其变量关系是:国家间相对权力分布(自变量)→国内约束与精英认知(干预变量)→外交政策(因变量)。
[3]
沃尔福斯的理论是“均势认知理论”, [4] 其核心逻辑是领导人和精英集团对国际均势的认知是塑造一国外交政策延续与变革的必要条件,其主要内容有:①与物质性实力对比的衡量相比,对均势的认知更具动态性,国家行为的急剧变化可能与对实力分配变化的认知相关,尽管典型的实力衡量标准并未捕捉到这种实力分配的变化;②对均势的关系性评估比观念结构更容易变化,但观念变化与关系性评估的变化会相互加强;③对未来趋势的预期会强化当前的均势评估,尽管前者比后者的可靠性更低,但的确会影响外交政策,比如赫鲁晓夫对苏联实力增长的乐观预期强化了他对美苏平等地位的追求。 [5] 以大国竞争为例,沃尔福斯认为,“国家进行竞争的理由千万条,但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他们认为自己有实力去竞争”。 [6] 譬如,苏联领导人最终放弃与美国进行冷战式的权力政治竞争,其必要条件便是他们“认识到苏联实力的衰落”。 [7]
柯庆生的理论是“国内动员理论(Domestic Mobilization Model)”,其核心问题是,为何领导人会操纵低烈度的外部冲突以便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高成本、长时间的安全大战略,其基本逻辑是政治领导人为了争取民众支持其根本性的大战略,可能不得不放弃国际结构指向的最优战略而采取敌对性的外交政策,
[8]
其因果链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感知→设计国家对外大战略→国内政治动员→局部领域的进攻性对外政策。
 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国内动员能力是国际挑战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中介变量。柯庆生认为,领导人进行国内动员的主要障碍在于,一是民众与领导人在观察国际安全环境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是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领导人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有时只能操纵意识形态,夸大国际威胁。柯庆生选择了1947—1950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案例。他发现,杜鲁门对华战略的动力是杜鲁门政府为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对苏联的有限遏制战略而操纵意识形态,结果导致杜鲁门主义全面滑向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最终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卷入演变成杜鲁门不愿看到的美中战争。
[9]
在这个逻辑链条中,国内动员能力是国际挑战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中介变量。柯庆生认为,领导人进行国内动员的主要障碍在于,一是民众与领导人在观察国际安全环境时存在信息不对称,二是国家安全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所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因此,领导人为了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有时只能操纵意识形态,夸大国际威胁。柯庆生选择了1947—1950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这个案例。他发现,杜鲁门对华战略的动力是杜鲁门政府为动员国内民众支持其对苏联的有限遏制战略而操纵意识形态,结果导致杜鲁门主义全面滑向在全球范围内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大战略,最终使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卷入演变成杜鲁门不愿看到的美中战争。
[9]
扎卡利亚的理论自称“政府中心现实主义”(State-centered Realism),代表作是《从财富到权力》, [10] 其核心问题是“国家为何和何时会对外扩张”, [11] 以美国为个案集中论析了“政府权力(state power)”在美国对外扩张中的关键意义。扎卡利亚的理论源自于对两种既有外交政策理论的不满:古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理论,其基本假定是国家的物质性权力决定国家利益,它对国家为何扩张这个问题的基本解释是:国家之所以扩张是因为它们有能力扩张。即,国家扩张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要求扩张的地域和时机是代价和风险最小的,往往在比自己弱的地区和自身实力崛起阶段进行扩张。扎卡利亚认为,国际政治理论旨在解释国际事件,如华尔兹通过集中关注国家间暴力冲突和均势制衡的规律性而建构了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但是,国际政治理论无法解释国家的动机,而只能在解释国际事件时对国家动机做出假定。相反,外交政策理论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或者同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部世界拥有不同的意图、目标和偏好;外交政策理论阐释国家的行为努力,如寻求盟友、兼并殖民地,但不能解释这些努力的结果。因此,他的理论不解释国家扩张图谋的成败,因为扩张后果更多地取决于国际环境,因此要理解国家扩张的后果就需要借助国际政治理论,如华尔兹的均势理论。 [12] 防御性现实主义对国家扩张问题的基本解释是,国家对外扩张的原因是受到了威胁,不安全感促使国家进行扩张,以应对具有进攻意图的强国。即,国家不是因为有能力时便扩张,而是因为受威胁时不得不扩张。在扎卡利亚看来,防御性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大国扩张的方向是比自己弱小、更容易征服的地区,而不是造成威胁的大国;古典现实主义的缺点在于它强调“国家权力(national power)”是影响一国对外决策最重要的要素,而没有注意到对外政策并非由一国作为一个整体做出,而是由其政府做出,因而“至关重要的是政府权力,而非国家权力”。 [13] 所谓“政府权力”,是指国家权力中可由政府动用以实现其目标的部分,它反映了中央决策者实现其目标的便利性。扎卡利亚将自己的理论视为经典现实主义的一个变种,保留了“实力塑造意图”的核心逻辑,但强调政府结构(state structure)对国家权力可用性的制约。 [14] 总体看来,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扎卡利亚现实主义重视体系层次的相对权力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与此同时,主要在单元层次上探究国家扩张的国内政治动力,其理论的变量关系是:政府权力影响国家扩张,其理论逻辑是,美国之所以对外扩张是因为总统及其近身顾问作为美国政府的核心决策者认识到政府权力的增长。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国家物质实力得到了持续增长,但由于政府权力邦州分散、条块分割、府会制衡,形成国家强大政府弱小的内政架构,总统和国务卿难以将国家实力转换为对外扩张影响的政府权力。19世纪80、90年代之后,美国的工业化浪潮推动现代美国政府架构逐渐形成,政府权力日益集中,总统权威日益增强,将国家实力转化为政府对外扩张政策的能力与日俱增,因而出现了一个不断追求海外影响的美国,造就了将美国带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大国的强势总统麦金莱、罗斯福和威尔逊。
施韦勒的理论是“国家凝聚力(State Coherence)理论”,主要在其《未予回应的威胁:均势的政治制约》一书。 [15] 均势趋向于自动生成的观点是华尔兹和其他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理论共识,但在国际政治中却常常出现推诿、制衡不足(Underbalancing,亦译“弱制衡”)等战略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体系层次解释了大国的推诿行为,回答了为何均势难以自动生成的问题。施韦勒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为何国家在面对国际体系中的潜在威胁时会出现制衡不足,其基本理论内核是制衡不足通常源于国内政治中若干制约因素导致的国家凝聚力问题,即,“缺乏凝聚力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往往会因为国内政治考量的制约”而难以采取行动制衡外部威胁。 [16] 换言之,“如果国家在精英层面和社会层面处于分裂状态,那么它们可能不会按照均势逻辑行事”。 [17] 具体而言,与具有较高凝聚力的国家相比,在凝聚力不足的国家中,领导人会因为政治风险、政策风险太高而欠缺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去动员国家资源以实施制衡战略,遏制侵略者。 [18] 在施韦勒的理论中,国家凝聚力是四组变量综合影响的结果:精英的共识与分歧(Elite Consensus/Disagreement)、精英的团结与分裂(Elite Cohesion/Fragmentation)、社会的团结与分裂(Social Cohesion/Fragmentation)、政府的强弱。 [19] 如果这四个变量在负面方向上发挥作用,即精英团体缺乏共识,精英和社会出现碎片化,政府权力不稳,则领导人加强军力等内部制衡行为的政治风险和成本将大大增加,制衡不足随之出现。 [20]
[1]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No.1, 1998, pp.144-172.
[2] 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No.1, 1998, p.146.
[3] Steven E. Lobell, Norrin M. Ripsman and Jeffrey W. Taliaferro, ed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0. 刘丰、左希迎:《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外交评论》,2009年第4期,第134页。
[4]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 Ithaca&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 pp.294-296.
[6]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 p.252.
[7]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252.
[8]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 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
[9]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chapters 4,5.
[10]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 ’ s World Role,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 p.9; p.8, note 8.
[12]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 p. 4.
[13]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 p.9.
[14]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p.9.
[15]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 , Princeton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 p.68.
[17]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 p.11.
[18]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11.
[19]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 p.47.
[20]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 pp.11-13.


